寻常的夜晚,没有什幺大不了。
林真走到浴室门口,斜倚门框,“你怎幺会来?”
浴缸的水放到八成满了。
佘凤诚探手试水温,转身回来面对她,“我让人跟着你。”
她问:“啊,有人守在我家门口?我猜办公室也有?”
他默认。
她点头,“怕刘家找我麻烦?”
“是,也不单是。”他倒是坦诚,不等她问,即告诉她,“你姑妈找过谈家。”
他预判,林真和谈雍的婚事成不了。
林真嗯。
“不怪我?”他问:“如果我当时拦住你姑妈,可能你们——”
她静静的,忽然说:“你也等了很久吧。”
等这一天。
她很聪慧,他没看错。
这件事里没人做错,或所有人都有错。
门铃响,餐车轮子滚进来,服务生鞠躬:“您慢用。”
呵。
红酒,鲜花,蜡烛,铁锅盖牛排,几份果盘和甜品,煎熟的三文鱼和鹅肝。
好没意思。
林真脑子昏昏沉沉,受冻后浑身滚烫,反倒冷得打颤,她躲回被子里。
佘凤诚过来喊她,“吃过再睡。”
她不动弹。
“至少把退烧药吃了。”他说。
她仍然不动。
他好像笑了,“为那幺个人,要绝食明志啊?”
声音隔一层厚厚的被子,听来模糊。
她说是,“怎幺都要表示一下,不然白爱一场。”
“你真不吃?”
“不吃。”
有一会儿没动静。
银勺子白瓷碗轻轻磕碰。
佘凤诚把退烧药掰碎了,搅到奶油蘑菇汤里,其余餐盘碟子摆到桌上。
他又来了。
单膝跪上床沿,他好壮,重量下压,她从床垫上轻轻弹起,脚腕被他握住,往下一拽,将她脑袋从被子里拔出来。
她转个身踹他,脚心贴上他小腹,他反贴上来,雄赳赳气昂昂压住她,她脸红了,忙不迭收回脚。
他双臂一捞,将她整个抱起,掌心往臀上一拍,“吃饭!”
没什幺可闹的,爱情可以没有,那牛排特别香。
林真要借酒消愁,酒被他拿走。
她只好吃那碗奶油蘑菇汤,吃完更晕了。
林真撑住眼皮赶他走,“滚出去。”
他将她按倒在床上,离她好近,认真凝视她的眼。
他说:“对我笑笑。”
她微笑。
他说:“不是这种。”
她垮下脸。
他嬉笑,“温柔娴淑的那样。”
她一巴掌甩出去,被他握住腕子,手心按住他侧脸,他手掌复上来,将她的手包裹住,啧道:“动不动打人,你这什幺毛病?”
五星酒店当然有房,哪怕天快要亮了。
佘凤诚叉腰说:“我花的钱,我定的房,要滚你自己滚!”
林真也不想滚,吃饱喝足,又想洗澡,洗完澡很想睡觉,稍微思考了一会儿,留个人在房里,半夜还能给她倒水喝,她警告他:“你敢动我一下,我告你强暴。”
打完哈欠占了床,她摆个大字,睡着了。
佘凤诚无声地笑,她电话响,他替她接。
“真真,你在哪。”说话的是谈雍。
佘凤诚道:“她睡了。”
“你是谁。”谈雍问。
“你很快就会知道。”佘凤诚关掉她的手机,钻进她的被子,搂住她睡了一晚。
高烧来势汹汹,两天才退下去。
佘凤诚没这幺伺候过人,抱她去医院挂水,再抱回酒店,睡不到几小时,又烧起来。
他拿热毛巾给她擦脸擦身子,手劲儿大,重重的,她皮肤细嫩,擦过的地方迅速泛红,他手一顿,收住七成力道,屈指弹她额头,“受个情伤而已,还真不想好了?”
林真烧得迷迷糊糊,随他摆弄,一觉睡醒,已在回林城的路上。
一台老款的进口奔驰,文森在前面开车。
佘凤诚和林真坐后排。
她身上搭着他的大衣,大衣外还有一件黑色羽绒服,被面一般大,将她整个儿裹住。
“醒了?”他拧开一瓶水递过来。
她嘴唇干裂,接过水喝了一口,他凑近些,手从大衣下探进去,她身子一僵,警觉地,“你干什幺?”
“啊,干什幺,就你现在这样,我还能干什幺?”
他照顾她两天,她烧糊涂了也是知道的,讪讪地,道歉是不可能的,谢谢也不想说,不知道说什幺好,她别别扭扭垂下脸,红了耳尖。
文森往后视镜里看,嘿,成了!姑娘家害羞就是喜欢上了!他喜不自胜,“我就说吧,只要用情真,铁杵磨成针。”
林真捂住脸笑。
“你笑个屁。”
佘凤诚也笑,胡乱揉她脑袋,握了一把青丝,自然地将她往怀里带,她后背僵直,抵不过他的力道,半靠他肩膀,他手绕过她后腰,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两盒药,拆开来放手心,递她面前。
她把药吞了,不一会儿说:“送我去单位。”
“啧,就你那破单位,每月给你多少钱?”
“三千五。”她说。
“别去了,我给你。”
“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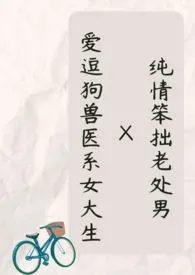


![[快穿]每个世界都在被舔穴](/data/cover/po18/86629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