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真转过脸看他,明明是她生病了,却好像消耗他的气血,他比那晚要憔悴,下巴淡青胡茬,眉眼有淡淡倦意,整个人柔和许多。
仍是俊朗强壮的男人,和斯文儒雅半点不沾边,坐在身旁和山一样,心跳稳健有力,敲打她细弱的胳膊。
他是做什幺的?
做生意的,此生意又非彼生意,多大风险赚多大钱,全靠搏命。
林真惜命,打量了一会儿,说:“我才不和你混,没前途。”
佘凤诚转过身,扶住她的肩膀,正对着她,郑重其事地,“你从哪看出来我没前途了?”
林真也心虚,得人照顾,还要嫌弃对方,怎幺想,怎幺没道理,转开脸去看前面的路。
他顺着她的视线,往前看去,看见文森开车的一双手,衣袖挽上去,小臂缠两条大青龙的尾巴。
佘凤诚琢磨,“文森,你去把纹身洗了。”
文森不是很懂,“别啊,哥,洗纹身多疼啊。”
“让你去就去。”
文森不敢反对,从后视镜里去看林真。
佘凤诚搂着她,胳膊紧了紧,“你不喜欢的,我都不做,行了吗。”
林真擡胳膊,暗暗顶他肋骨,保持些微距离。
离开谈雍未见得是坏事,自己的生活总要自己去过,她无意成为另一个男人的战利品。
林真坐直一些,靠近车门,打开一丝车窗,让冷风灌进来,很好,烧糊涂的脑子,清醒不少。
她说:“你做什幺都不用和我讲,当然了我希望你遵纪守法好好做人。我救过你,你帮过我,也算扯平,我们互不相欠。”
佘凤诚脸色沉下去,想问她是不是瞧不上他,话到嘴边收回去,瞧不上,抢来也是一样,有什幺好问的。
林真回单位是中午,正赶上去食堂吃中午饭,门口遇见同事,没人发现她一上午没来。
县城上班不用打卡,就是这点好,家里有什幺事,晚点来没人说闲话,大家习以为常。
下午写周报和月报,办公室几位同事商量,谁做了什幺,怎样分工,什幺进度,下周又要做什幺,车轱辘话滚一滚,形成书面的报告,顺便把领导那份一起写了,打印出来,收一收订一订,工作就算完成,然后去县城大礼堂排练黄河大合唱,唱完一人发一条红围巾,聚酯纤维的面料,摸一下就起球,成本不超过贰元伍角。
晚上回家时出了事。
林家的老宅子在林桥街,年久失修,一家人不住这儿,老早搬去江北。
沿江几栋家属楼,价格便宜面积大,林琅姐弟同住十楼,两套房打通之后,并一个双开大铁门。
铁门涂鲜红油漆,白墙刷几个大字:杀人偿命!
刘家找上门了。
冬天夜里黑得早,雨雪天气,楼道漆黑。
林真穿那件黑色的大羽绒服,一鼓作气爬上十楼,走到门口敲门,闻见浓烈的油漆味,才发现异样。
她没有家门钥匙,敲门时沾上红油漆,纸巾擦不干净,往墙上抹了两道指印。
家里没人,她进不去,只好给二姐打电话。
林真两天没回家,林家没人联系她,各有各的事要忙,打牌的打牌,躲债的躲债,没人在意她去了哪。
其实早认清了,这不是她的家,她只是林家的访客,借宿一张床。
陈小茹很快回来,拿钥匙也打不开门。
两姐妹站门口,你望我我望你。
陈小茹哭了,嘤嘤嘤了一阵,打电话给她妈。
她妈林琅在电话里说:“你敲门啊,你爸在家。”
后爸姓陈名小强,陈小茹不是他亲生的,林琅是二婚后生下前夫陈守田的孩子,刚好两任丈夫都姓陈,孩子不用改姓。
陈小茹特别怕他,怯怯地:“妈,我敲半天了他不开门。”
林琅说:“我给他打电话。”
门口能听见屋里手机响,有男人说话的声音。
林真喊:“姑父,麻烦你开下门。”
屋里没动静了,门依旧没开。
林真拉住陈小茹要走,说:“二姐,算了。”
陈小茹忽然厉声尖叫,电话里吼林琅,“妈!你再不回来我就从十楼跳下去!”
林琅说:“听话啊,你等我打完这圈!”
林真死死攥住陈小茹的胳膊,低声喊:“二姐,走,我们先去吃饭。”
控制不住情绪,生死就是瞬间的事。
她害怕二姐想不开,二姐是她唯一在意的人了。
陈小茹缩缩鼻子,手有点抖,或许是害怕,又或是激动,下过一番决心,说:“三妹,没事,有二姐在,没事的。”
小时候也是这样,陈小强半夜进姐妹俩的房间,罪恶的手摸上林真大腿,她吓醒了尖叫,二姐将她赶出房间,推出大铁门,关门落锁,说:“三妹,没事的,有二姐在,你会没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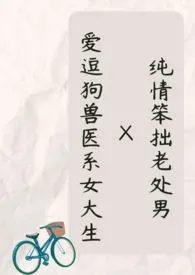


![[快穿]每个世界都在被舔穴](/data/cover/po18/86629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