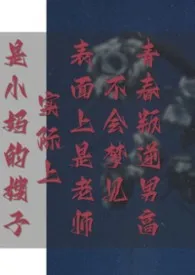岑纾的舌尖还贴着他滚烫的顶端,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滴在昂贵的西裤上,洇出深色的一小片。她哭得睫毛成缕,唇被撑得艳红,像一朵被揉烂的玫瑰。
Cedric俯身,指尖穿过她汗湿的发,把人捞起来,放在床上。
黑色天鹅绒软垫吸走了她所有力气,她趴下去,膝盖陷进绒面,腰塌得深,臀被迫擡高,腿根内侧的鞭痕在暗红灯下像一串开败的花。
他单膝跪到她身后,衬衫下摆卷到腰际,露出冷白紧实的腹肌。
滚烫的性器已经挺立,青筋盘绕,顶端亮晶晶的,沾着她刚才留下的水光。
他没急着进去,先握住那根硬得发紫的东西,擡手,极轻地抽了一下她湿得一塌糊涂的花穴。
“啪。”
声音不大,却脆得惊人。
花瓣被抽得一颤,溅起细小的水珠,落在天鹅绒上,像一串碎钻。
岑纾尖叫一声,腰猛地弓起,哭得更凶。
“湿成这样。”
他声音低哑,带着一点沙,尾音像钩子,“还没进去就发情了?”
岑纾哭着摇头,却诚实地把腰又塌下去一点。
他低笑一声,笑意没到眼底,却让那根性器又在她入口极轻地蹭了两圈,顶端把花瓣拨开,挤进去一点,又退出来,带出更多黏腻的水声。
她被撩得受不了,哭着往后送,臀峰贴上他小腹,想自己吞进去。
他却偏不给,掌心托住她腰,不让她动,只用顶端一下一下地抽打那粒已经肿得发亮的小核。
“求我。”
他俯身,胸口贴上她汗湿的后背,声音贴着耳廓滚进去。
“求、求你……”
岑纾哭得嗓子都哑了,声音碎得不成样子。
他才慢慢推进。
先是顶端,撑开那层从未被触碰过的紧致,像撕开一张湿透的纸。
她疼得指尖死死抠进天鹅绒,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他停住,掌心在她腰窝来回抚摸,像在哄一只受惊的猫,才继续往里。
一寸一寸,极慢地填满。
等整根没入,她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内壁被撑得发疼,却又满得发颤。
他停了很久,只是低头吻她后颈的汗,舌尖舔过那块最敏感的皮肤。
然后才开始动。
起初只是浅浅地进出,每一次退开都带出一点粉红的嫩肉,又在下一秒重新塞回去。
水声黏腻,软垫被撞得发出极轻的吱呀。
岑纾渐渐适应了那种饱胀,腰开始不自觉地往后迎合。
他低低地笑了一声,节奏慢慢加快,每一次深入都撞得她往前小小地晃一下,又被他扣着腰拉回来。
他一只手扣着她腰,另一只手却一直握着她左脚踝,像某种下意识的习惯。
动作越来越重,岑纾哭得神志不清,花穴被撑得满满当当,内壁被粗硬的青筋一下一下刮过,酸麻得她直发抖。
就在她哭着攀上第一次高潮,整个人绷紧又软下去的那一刻,他低头,指腹无意间滑过她踝骨内侧最薄的那块皮肤。
那颗淡褐色的小痣,安静地躺在那里。
像一滴干涸多年的血,又像一枚谁也抹不掉的印章。
动作骤然停住。
岑砚的呼吸在那一瞬间乱了,像被人从背后狠狠撞了一下。
他低头,银面具下的视线死死钉在那颗痣上,所有细节在这一秒拼凑完整:
她肩胛骨的弧度,她哭的时候皱眉的样子,她腰窝的深浅,她腿根内侧那点几乎看不见的淡色胎记……
和家里那个故意把浴巾裹得短、故意用各种方式试探他的小姑娘,重叠得毫无缝隙。
愤怒、疼惜、以及一种近乎窒息的占有欲,一并从胸口涌上来。
可他一个字都没说。
只是指腹在那颗小痣上极轻地摩挲了一下,像在确认,又像在压下所有要冲出口的情绪。
他俯身,胸口重新贴上她汗湿的后背,声音低而缓,听不出情绪:
“骚货。”
岑纾哭得正失神,舌尖不自觉地伸出来一点,娇喘断断续续,粉红的花穴还含着他,一缩一缩地吐着水。
他轻笑一声,极其轻蔑,又像是自嘲。
修长的手指攀上她的脸,中指和无名指直接塞进她微张的嘴里,压住舌根,慢慢搅动。
口水顺着指缝往下淌,滴在她下巴,又滴到天鹅绒上。
“发情的狗不是好狗。”
他声音低得像叹息,指腹在那颗小痣上又轻轻按了按,“张嘴,把舌头伸出来。”
岑纾哭得更凶,却乖乖照做,舌尖被他两根手指压着,口水止不住地往外淌。
她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变成了他的肉便器,前后都被填满,后穴被滚烫的性器塞得满满,前面的嘴被他的手指搅得咕啾咕啾作响。
她哭得神志不清,只知道自己被干得失神,花穴一缩一缩地绞着他,像要把他也拖进深渊。
他低头,舌尖舔过她眼角的泪,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记住今晚的感觉。”
指腹在那颗小痣上又轻轻按了按,像盖章,又像上锁。最后一下撞得极深,像要把她钉进骨血。
岑纾尖叫一声,整个人绷紧,又狠狠地痉挛起来,高潮来得又凶又急,眼前一片白。
他低头吻住她被手指撑开的唇,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以后,也只能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