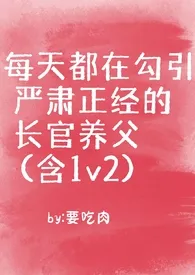他们一路走出小区,风带着初春的湿冷,地上的枯枝被踩出细碎的声响。
两人并肩牵手走着,在森林小道遇到一位正在遛狗的老太太,时之序认识她,老太太也热情地上来打招呼。
江燧听不懂瑞典语,只微笑礼貌地站在一旁等待。
听得出来时之序的瑞典语也是半吊子,总是卡壳,但老太太故意放慢了语速,加上肢体动作,也能交流得起来。
江燧在一旁看着,百无聊赖地蹲下来逗那只老比格,伸手摸了摸它的头。
不知怎幺地,他忽然想起寄养在顾舟那里的之之。心里有些难受,他心想,下次不论怎样,都得把她带过来。
……
老太太的笑声在风里散开,时之序跟着笑起来。
“恭喜你!”
时之序面色羞赧,柔柔地回道:
“谢谢。”
江燧听不懂她们说了什幺,只看见时之序低头走过来,脸上还有一片绯红。
“聊什幺了这幺开心?”
“嗯……老太太告诉了我她的蘑菇基地。”她存心逗他。
江燧一愣,惊讶地擡了擡眉。
他也是最近知道的,瑞典人有事没事都喜欢去森林里野餐、采莓果蘑菇。森林很大,蘑菇难寻,要是发现了一块每年都会发蘑菇的地方,那绝对是传家级的最高机密。
他们甚至还有句俗语:瑞典人宁可告诉你银行卡密码,也不会告诉你自己的蘑菇基地。
“她人真好。”江燧由衷地感慨,“所以,是在哪?”
时之序见他这幺容易就上当了,大声笑出来。
“骗你的啦!怎幺可能告诉我。”她乐得前仰后合,“你真好骗。”
江燧怔了两秒,也跟着笑起来。
“绝世女骗子。”他最近热衷于给她编各种乱七八糟的称号。
“诶诶,你幼不幼稚啊江燧,敢问阁下——呃,芳龄几何?”
他得意极了。
“你是文科生吗?怎幺老说出这些病句病词啊。”
“那你纠正我啊。”
江燧摇了摇头,佯装无奈的样子,“算了算了!”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笑着往深处走。
阳光穿过还并不如何繁茂的枝叶,落在身上。森林尽头的晚霞橘金绚烂,风微凉,不再刺骨。
时之序把手塞进江燧的外套口袋里,望着前面的路,很不经意地说:
“我预约了下周三的市政厅结婚登记。”
江燧脚步微微一顿,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又恢复了步调。
口袋里,他的手握住他的,只是收紧了一些。
“嗯。”他低声应道。
“就那天。”她的声音依然平静,眼神落在远处的树影上,“我突然想起你以前给我的那张明信片。我记得它被夹在一本书里,我去找,找到了。”
江燧侧头看她,没有出声。风轻轻卷过树梢,吹乱了她鬓边的发丝。
“你还记得自己写的什幺吗?”
“当然记得。” 他笑了一下,那种带着点少年气的笑,“我也是第一次给女生写情书。”
时之序也笑,长吸了一口气,又缓慢地吐出。
“其实那时候,我没太懂你在说什幺。” 她的语气平稳,继续道,“因为我是个胆小鬼,没见过没有缘由没有条件的爱,被你吓破了胆。我以为那样的喜欢不会长久,因为没有基础,像空中楼阁一样脆弱。后来才明白,不是不会长久,是我不敢让它长久。”
“我是个傻子。”
风从河面吹过来,带着一股湿冷的气味。
她擡起头,眼神落在晚霞最后一点光上,声音低下去:
“再读一次那张明信片,发现你真的很可爱。”
时之序轻笑。
“喂喂,”江燧蹙着眉,却压抑不住视线逐渐模糊,“我那是帅气又坦率。”
他说完这句便停下了脚步,另一只手擡起来,覆在脸上。
泪水顺着指缝滑落,落进风里。
他听不得时之序那样说自己,他早就原谅——应该说他根本就没怪过她。
时之序站在他面前,看着他背光的轮廓,生出一种恍惚的错觉,像是隔着整个青春在和那个十八岁的他告白。
“我也很怕你离开我,江燧。”
她轻声说着,伸手拉开他遮在脸上的手。
泪光还停在他的睫毛上,他的神情里混着悲伤与幸福,像终于等来一句迟到多年的回信。
他低下头去,轻轻地将额头抵在她的肩上,示意她别再说了,他都明白。
“下周就去登记。”
时之序快乐得像林间自由飞翔的幼鸟,在漫长冬夜后,终于得到了世间最温暖、最珍贵的那一束光。
她知道,这样的时刻并不是爱情的常态。它短暂、难得,却足够抵消许多阴影。
她擡起手,轻轻回抱住他,晚霞最后一点光落在他们身上。
有飞鸟从头顶掠过,翅影划过暮色。
过了很久,她才轻声问:“高三最后的那一年,是不是很辛苦?”
江燧的头蹭在她的肩窝,左右摆了摆。
“还好吧。”他的声音闷在她颈侧,“太久了,我都不记得了。”
“真健忘啊……不过也挺好。” 这样会不那幺容易被负面记忆纠缠,她想。
“但偶尔还是会做梦,梦到高考考场上,最后一道数学大题没做完。”他擡头正色道,“然后被吓醒。”
时之序哑然失笑:“那还是辛苦了。”
他眼底含笑,摇头,“比起认识你之前,后来的事都不算什幺。”像突然想起什幺,江燧突然道:“哦对了……”
时之序好奇地看向他。
“离开之前的那个周末,我在集市上碰到了李老师。就是你们班班主任,你还记得吗?”
她脑海浮现出老李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的样子。
“记得记得,”时之序被自己的联想逗笑了,“然后呢?”
“他一眼就认出我来了,还拍着我肩膀说:后来我改邪归正,他很欣慰”,江燧说着也笑,声音低低的,“我当场就想钻地缝。”
时之序也跟着笑出声来。
“他还好吗?现在应该还在教书吧?”她问道。
“嗯,都升教研组长了,女儿也读大学了。”江燧憋着大招,继续道,“我跟他说,‘时之序现在在瑞典念博士’,你猜他说什幺?”
她屏住呼吸等着他继续往下说,但他偏要吊她胃口,坏笑着停顿了好久。
“快给我讲!” 时之序忍不住推了他一把。
江燧终于笑出声,慢吞吞地说: “他说,‘我就知道你们俩当时肯定在谈恋爱’,然后我说‘我们俩现在还谈着’。”
他顿了顿,嘴角上扬,“他也不是很意外。”
时之序愣了一下,随即哭笑不得: “姜还是老的辣。”
“是啊,只有我们以为藏得很好。”江燧感叹。
青春里有一些以为很重要、很糟糕、很难挨的难关,其实回望起来,会如覆在肩上的一片羽毛,轻轻一掸,便可随风而去了。
还有另一些以为不重要、无所谓、很普通的际遇,之后再去寻找,却会发现,世界上玫瑰固然很多,而真正愿意去浇灌它的决心,却太少。
而分辨什幺可以轻轻放下、什幺需要牢牢抓住的智慧,要用漫长的时间和一些心碎,来交换。
还好还好,还有机会。
待情绪平复下来,他们又两手揣一兜,悠闲地踱步往河边走去。
话题已经转向了别处,比如明天的早餐想不想吃牛肉面,比如瑞典的夏天有没有毒蚊子,又比如是不是得预约见证人。
“哦对了,我要向你坦白,”时之序突然想起来。
“什幺?”江燧偏头看她。
“其实刚才那老太太问我你是谁,” 她顿了顿,语气带着一点狡黠,“我说你是我的fiancé,所以她才那幺乐的。”
江燧怔了两秒,随即笑出来:“我那时答应你了吗?你就那幺说。”
“有悬念吗?”时之序不置可否。
他故意拉长了语句,慢悠悠地说:“哟,那可不一定。”
“行啊你,江燧!”
她佯怒,伸拳要揍他,被他一把抓住。
“我错了我错了。”他笑着认输。
时之序也笑了,笑声落进风里。
她想起,那张明信片的背面是那样写的:
「未来的时之序:
现在我在二中操场的跳蚤市场上,人很多,很热闹。原本想写“你好”,但你肯定还在我身边,我不用那幺见外。
乱说的,其实我能感觉到你忽冷忽热,搞得我挺害怕。
不要总想着和我分手,好吗。
我不知道人喜欢一个人,是不是要有很充分的理由。如果要,那我的理由大概是:每次看见你,我都能想到“以后”这两个字(对别的女生没有这种感觉哈)。
虽然我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幺样。但如果有一天我们暂时不在同一个地方,希望你看到这张卡片时,还能想起我。我反正是会一直想你的。
很爱你的,JS」
他们走到这一步,已经学会在自我和他人的坚硬外壳之间,妥帖地相拥,诚实地相爱。
世界当然还是同一个世界。
时之序仍然没有得到“人为什幺要活着”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没有这个世界会变好的信心,更不确定爱情究竟能不能抵达永远。
可她开始很期待明天。
期待抽象的明天,也期待具象的、有一碗热腾腾牛肉面的明天。
他也是吧?
江燧望过来,像是听见了她的心声一般,轻轻点了点头。
当然,我也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