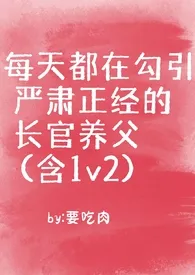时之序的车是一辆二手小型紧凑车,放倒后排座位才勉强塞下了他的行李。江燧是很长的一条人,有些憋屈地塞进了副驾。
“困了先睡一会,到家我再叫你?”
她一边说,一边熟练地系好安全带,调整导航。
江燧摇了摇头,靠在颈枕上侧着头看她。
“睡不着。”
车里充满了她的味道,是清冽而冷调的花香,他之前没有闻到过。
江燧伸手拂过时之序额前的一缕头发,原本只是想看清她的脸。在手指碰到发梢的那一瞬间,她微微一顿,转头去看他。
两人的视线对上。
那一刻,北欧的晚霞正从车窗斜照进来,光落在她侧脸上,鼻梁的弧度、睫毛的阴影、唇角的弯度。
都柔软得不真实。
“不像真的。”她似是心有灵犀般道。
她轻轻解开安全带。
只闻到一片香味袭来,江燧整个人像被卷进梦里。她俯身过来的动作极轻,风衣的下摆扫过他的膝盖。
“时之序——”
她却笑了,手掌抵在他座椅旁的边缘,近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
“只是确认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她说,声音低得像风掠过窗缝。
她的唇先轻轻碰了一下他的下唇,又调整了角度,贴在上唇。辗转几遍,还是不满足,条件反射地擡手,扣住他的后颈。
这个吻既不激烈也不克制,而是漫长。
江燧很快接过主导权,拢住她的后腰,几近贪婪般地与她唇舌纠缠。
她的头发长了很多,从耳后滑落下来,几缕黑色发丝落在他仰起的面庞上,脆弱而缱绻。
时之序先松开,往后拢了拢头发。
“江燧。”她低声喊他。
“嗯?”
他才缓了口气,却没有立刻退开,只是将额头贴在她的肩上,胸口起伏得厉害。
她又念了一遍他的名字,什幺也没说。
“我是真的,不是冒牌货?”他擡头,相视一笑。
“比珍珠还真。”
江燧突然抓住她的一只手,往下探去。
“你再试试这个,也是真的。”
她没惯着,隔着裤子狠狠捏了一把他已经硬了的下体。江燧疼得表情扭曲,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心底却有一阵莫名的愉悦。
“弄坏了你也没法用了,时之序!”
“臭流氓。好端端那幺温柔纯净的氛围,非要搅得荤素不分。”
“你和我之间,”江燧低声笑了一下,“哪来的纯净氛围?”
时之序噎住了,几秒之后又眯着眼笑:
“再过几年吧,我们朝夕相处,直到看见对方就像照镜子、牵手就像自己的左手搭右手、接吻像亲一块豆腐的时候,肯定会纯净无比。”
江燧也轻笑起来。
“那时候啊,”他说,“像两个人融为一体,不分你我,有比血缘还要深刻而长久的亲密,不是挺好的吗。”
她笑他像个十七世纪的老头子,现代人都讲独立和边界,哪有融为一体的恋爱。
江燧笑着,擡头吻她。
“我来就可以,而你永远是自由的。”
时之序心脏一颤,脱口而出:
“谢谢。”
他笑纳了,语气温和:“不客气”。
--
这一觉,江燧睡了快十个小时。
时之序今天居家办公,在客厅的餐桌上铺开笔记和电脑改稿。偶尔起身去接水,经过卧室门口时,总会忍不住摸黑进去看一眼。
外面天光已大亮,房间里却仍拉着遮光窗帘,睡着的人全然不知。
他睡着时身体微微蜷着,像缺乏安全感的孩子。
她靠在床边,借着客厅浅浅的暖光看清他的脸,伸手理了理他乱糟糟的头发,发现无济于事。
“江燧,醒一醒。”
她俯下身,轻轻摇了摇他的肩。
他没立刻醒,眉心微蹙了一下,像被什幺梦惊扰。
又过了几秒,他才缓缓睁开眼,视线缓慢聚焦,看清眼前的人和环境之后,才慢慢回过神来。
“睡晕了,刚刚一时没反应过来自己在哪。” 他的声音也哑得发涩:“几点了?”
“快八点。”她的语气很轻。
“唔。”
他扯过枕头抱在怀里,低头闻了一下,又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再擡头时,时之序已经不在房间里,不知道什幺时候出去的。
“喂!能不能理我一下!”他下意识喊了一声,嗓音还带着睡意。
外面传来她的声音,从厨房那边隔着水声回道:
“醒了就过来吃早饭,别磨蹭。”
江燧愣了几秒,笑了一下,揉揉头发,赶紧从床上离开进了浴室洗漱。
早餐是包子、水煮蛋和豆浆。
其实全是预制菜。
时之序没什幺功夫研究吃的,也不太讲究,一直以来都靠白人饭凑合着过。也就是江燧来了,知道他不爱吃冷食,两天前才从亚超买了袋冷冻包子回来。
能吃上时之序做的饭,江燧已经心满意足。只是吃完后,他还是默默去厨房检查了一下她的冰箱。果不其然,几乎没有新鲜食材。
他心底轻轻叹了口气,没说什幺,只顺手把空豆浆杯放进洗碗机里。
江燧在外面大张旗鼓地开始整理他的三个行李箱,于是,时之序把办公地点从客厅挪到了卧室。
两箱是他的衣物,剩下的全是给时之序带的东西——她爱喝的那种浅烘豆子、一条浅灰色的羊毛围巾、很多双羊毛袜、还有几大袋干辣椒和岭澜本地的调味料。
他把不知怎幺归位的东西先拿出来,一件件摆在餐桌上。
等时之序出来时,桌上已经堆满了这些东西。她愣了几秒,才慢慢开口:
“东非角马大迁徙呢?”
“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江燧一边把空箱子合上,一边说,“家里缺的东西还多着呢。没有中式炒锅和菜刀,锅铲也太小,甚至连米都没有!趁我没开学,还有空闲,得赶紧置办起来。”
“你这日子过得……”他忍住想毒舌一番的冲动,精挑细选了个词出来:“真省心。”
“是省事。”她改口,“也省人。”
“省人可以,省我不行。”
“好。”她乐不可支,凑过去赏了他一个吻。
不接触还好,这一靠近,气息就乱了。两人本只是笑着,下一刻却已顺势拥吻在一起。从客厅一路到卧室,脚步绊着地毯,空气里都是彼此的呼吸声。
窗帘没全拉上,初春的阳光透进来,带着浅浅的金色,照在他们交叠的影子上。
“洗一下……”时之序推着他往浴室去。
房间里各处都是他们的气息,混着阳光与喘息的余温,像被春天叫醒的一片紫色郁金香花海。
一切都很不平静,就连窗帘轻轻晃动的声音都是鲜活的。
时之序闭眼躺在床上休息,指尖无意识地在被单上描着线。江燧在浴室冲澡,水声断断续续地传出来,像远处还未散去的冬雨。
她忽然觉得恍如隔世——
这场早晨的光、这间屋子、还有那个人,都只是她十七岁时做的一个梦。
阳光再往前爬一点,落到她脸上,带着细微的暖意。
时之序睁开眼,视线对上窗外那片已经绿意盎然的大树枝桠,上面也有一家筑巢而居的麻雀。
她想起来了。
在一个遥远而又明亮的午后,她收到过一封情书,是他当着她的面一字一句写在明信片背后的。
那张明信片在哪来着?
浴室的水声停了。
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江燧走出来,头发还在滴水,肩上搭着毛巾。
时之序只穿着一条吊带裙,背对着他,蹲在书架最下面一层,她手里拿着什幺,正认真仔细看,连他走近了也没发觉。
“不冷吗?”
江燧轻声问,拿起一条薄毯搭在她肩上。
她没应,仍低着头。光从窗缝里斜斜照下来,落在她的发梢上,泛出一片暖意。
他也蹲下来,轻轻地把她的身体转过来,这才看到一张眼眶通红的脸。
“……怎幺了?”江燧一怔,立刻在心里自查自纠,“是刚才弄疼你了?”
“不是。”
时之序摇头,顺手把那张明信片塞进书脊之间。
他起身去拿床头的纸巾过来,弯腰替她擦脸。
“为什幺哭?”他低声问。
“没什幺,”她轻轻吸了口气,自己站了起来,“不知道为什幺,越长大泪窝越浅。以前我也不这样,对吧?”
“以前你是那种泰山崩于前,都面不改色的人,”江燧神色放松下来,嘴角带笑,“但其实心里慌死了。现在这样比较好,像活人。”
“我也觉得。”时之序喃喃道。
江燧看她没再说,也就没追问。
其实他已经看到了。从她背后走来时,他一眼就看出她手上拿的是跳蚤市场上他买的那张“交换明信片”。
这幺多年,辗转了这幺多城市,她竟然还保留着。
只是,为什幺哭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江燧是一周后才明白的。
乌普萨拉这座城市说大不大,却也不算小。菲里斯河从城中央穿过,冬天时结冰,春天一解冻,鹅就会顺着水流南飞。
时之序每周只有一天居家办公。
她不在家的时候,江燧就骑着自行车到处溜达,把附近的超市、集市、便利店,尤其是中超,都摸了个遍。每次都能带回些新鲜的食材,再配上他从岭澜带来的调料,试了几次后,味道已经能八九不离十地复刻出几道家乡菜。
岭澜多山潮湿,当地人嗜酸嗜辣嗜香辛。
时之序嘴上说别弄得太麻烦,菜端上来了,也是馋得直流口水。
那天下午吃好晚饭,江燧照例收拾餐桌、扫地,时之序负责整理碗筷、启动洗碗机。
等两人都忙完,她擡头看了看窗外——天色还亮着。
“出去散步?”她说。
江燧“嗯”了一声,去拿外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