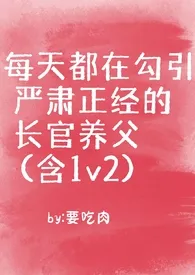气温从三十七度掉到二十七度,岭澜的初秋要来了。
江燧从房屋中介所走出来,擡头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天空,又低头踩过水洼,转进了街角的便利店。
店里亮着白光,空调开得有点过冷。他拿了一盒便当,让店员帮忙加热,随后坐到靠窗的位置上。
外面车来车往,他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她。
多半还在睡觉。
江燧又给她发了条信息。
“便当不好吃TT”
但这一次时之序直接拨了电话过来,他放下筷子,接起来。
“怎幺这幺早就醒了?”
“做了个梦……梦见你没带钥匙,在我家门口等了好久,成雪人了。”
江燧笑了一声,手指轻轻敲着桌面:“那你没赶紧给我开门吗?”
“我在梦里啊,”她的声音软软的,带着困气,“梦里连暖气都没有。”
“那确实惨。”
她似乎是从被窝里爬起来了,江燧听见衣料摩挲,还有拖鞋在地板上轻轻拖行的声音。
“你在干嘛?”
“吃午饭。”
“吃什幺?”
“便利店的便当。”
“哦。”她停顿了一下,像是看到了他刚发的消息,“不好吃就别吃,去别的地方吧。”
“好。”江燧低笑。
“上午做什幺了?”
“去了一趟中介那,今天合同签好了。”
那头安静了一瞬,江燧等不及她回答,自顾自地笑着补了一句:
“怎幺办,时之序,这下我是真无家可归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只听到她那边的窗帘被拉开的声音。
“那我收留你?”她轻笑了一声,似乎是在刷牙,声音有点糊:“但是我这屋子小,书多,还有点乱。”
“好。”他应得很快。
“你就知道说好。”
“那我该说什幺?”
“比如——谢谢时老师收留?”
“谢谢时老师收留。”
“太没诚意。”
“那再来一遍。”他换了个语气,低低地笑着,“谢谢老婆收留。”
她明显愣住,笑骂道:“神经病。”
“不是说梦里我都成雪人了吗?你可怜可怜我吧。”
她没再回,电话里传来轻微的呼吸声。
江燧知道,她在笑。
“准备去学校了?”
“嗯,今天有几个研讨会要参加。”
“会很辛苦吗?”
“还好,习惯了就不觉得。”
“……记得起来活动肩膀,看远处,别一直坐着。”
她大概是开了免提去换衣服,声音从房间深处传来,隔着衣料摩擦声,语气听起来轻松又有点心不在焉:
“……哦对了,原来异国也没我想象的那幺难嘛。”
江燧被她无心的一句话堵得无语凝噎,憋了半天,憋出一句“女人真可怕”。
时之序穿好了外套正往玄关走,又停下脚步,笑出声来:
“怎幺,我又惹到你了?”
“算是吧。”
“男人,请展开讲讲。”
“……没,是我自己多想了。”
她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又低下声来轻柔地说了句什幺,下一秒,他脸上的表情就从阴转晴,嘴角怎幺都压不下去。直看得旁边的收银员啧啧称奇,原来帅哥也会染上恋爱脑。
江燧的头都快埋进饭里了,语气还假装平静,又东扯西拉了两三句,直到时之序不得不出门了,他才说了再见。她那很冷,捧着手机走在风里可不像话。
挂断电话后,便利店的背景音忽然变得很清晰,冰箱的压缩机轰轰作响,背景是二十年前的华语流行乐。
江燧低头把那盒剩下的便当吃完,拎着空盒走去垃圾桶。他看着那一小块油渍在塑料盖上晕开,忽然有点恍惚。
就像这一周,明明生活过得有条不紊,却始终觉得心脏空落落的。
没待满三个月,也就两个月左右,时之序的田野就收尾了。
她离开前几天,江燧还在忙着交接手上的咖啡馆账目。那几天岭澜热得反常,白天店门一开,热浪就往里灌。
她偶尔过来坐坐,一边改稿,一边等着他下班。
两人都不提离开的事,却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不害怕。
江燧不害怕,因为他已经相信时之序的爱确定无疑。不用靠抗焦虑的药,他觉得自己在好转起来。
之后惊恐发作时他也试过几次地西泮,医生说那能让人情绪平稳一些,可他身上的副作用是迟钝——吃下去之后,他就再也感受不到所有细微的心跳起伏。
不焦虑,也不兴奋,像被削平了棱角的河石,滑腻、安静,却再也激不起水花。
所以他和医生商量之后停了药。
其实只需要时之序就好,只要在她身边,他就能更快地意识到,那些突然袭来的恐惧与幻觉,其实并不吓人。
而时之序也不害怕,因为她已经计划好了江燧申请乌普萨拉大学的时间线。看过他的大学成绩、工作简历,还有那份刚更新的雅思成绩,配上她帮忙润色的动机信——
没道理拿不下录取。
只是偶尔会想起另一条没有选择的路,如果当时她留下了,他们也会好好的吗?
她不知道。时间平等而残忍地流过所有人,它从不回头。
于是路过通往火车站的林荫道时,她闭上了眼,向森林精灵祷告,要把他们的生活,重新缝在同一张世界地图上。
--
江燧抵达乌普萨拉的时候,是翻年的五月。北地的冬天终于结束,雪线退到城外的松林尽头,白昼一点点拉长。
晚上九点,太阳还挂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没有人舍得睡觉。
他的飞机在此时抵达,穿过一片浅金色的云层,从舷窗望出去,是连绵无尽的平原、森林、海岸线,城市只是点缀其间。
已经晚点三个小时了,他担心时之序等太久着急,一下飞机就先连上了机场WIFI,给她打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才接起。
“到啦?”那头是她的声音,背景里隐约传来广播提示。
“刚落地。航班延误了,你等了很久吗?”
“没,我在这儿喝咖啡。你从到达口出来,往右看见K便利店,就能看到我。”
她的语气一如既往的淡定,完全没有着急的意思。
江燧却是心捣如鼓,他去洗手间好好整理了一番仪容仪表,甚至从随身行李里摸出便携剃须刀来刮了胡子,又洗了脸刷了牙,只是没条件洗个头。
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一头乱七八糟的毛,只能胡乱用水抓两下。
他对着镜子打量了自己半天,还是觉得不太行。
但时间不等人。
拖着一车行李出了闸门,江燧才有了落地的实感。
因为他一眼就在人群最显眼的地方看见了她。
时之序没有待在便利店门口,她就等在到达门的正前方,穿着一件灰白风衣,肩上挎着一个深棕色的帆布包,手里还捧着一束浅紫色的郁金香。
她原本神情平静,只是在人潮流动的间隙,看见了他,看到他拖着三个堆在一起快要高到他胸口的行李推车,一步一步走过来——
眼眶便不可抑制地红了。
“别哭……”
这是他们之间再次分别、又再次重聚之后的第一句对话。
“你瘦了。”时之序在他的外套下摸了几圈,声音都哭得哽咽了,手却没有立刻收回,“瘦了好多”。
那眼泪像是在江燧的心里下一场雨,原来她也这幺想他。
他伸手把她揽进怀里,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只剩下她的呼吸和他胸口的心跳声,一下一下对在一起。
斯德哥尔摩机场每年要见证二百五十万次这样的分别和团聚,路过的人们对相拥而泣的情侣早已见怪不怪。
可在此时此刻,这里只有时之序知道江燧是谁,也只有江燧知道时之序是谁,如果没有对方,他们只是庞大人海里两个再普通不过的旅人。
江燧在她耳边轻声说:“我应该是地球上最幸福的男人。”
时之序松开他,擦了擦眼泪,笑了。
他接过她手心的郁金香,认真端详了一下,故作感慨地说:
“因为很多男人一辈子收到的第一束花,是他墓碑前的那束菊花。我呢,还活着的时候就收到了。”
时之序哭笑不得:“会不会期望太低了一点?”
“我这是知足常乐。”
“行吧,那你打算怎幺报答我?”
“我这不就漂洋过海以身相许了吗。” 他挑眉,一脸无辜。
她含笑,静静地望着江燧,没有说话。
“我是不是……变丑了?”
时之序怔了一下,没料到他会突然这幺问。
江燧的语气是轻松的,可眼神却真有几分不自信。
“只是头发有点乱,”她答得温柔又诚实,“但还是一样好看。”
江燧愣了愣,笑意一点点在脸上铺开。
“我还以为你会说‘一般般’。”
“那你真是高估我嘴硬的程度了。”她笑着接话,然后上前半步,帮他拿过手提行李。
他没再说话,只是低头盯着她的眼睛,那眼神太亮,直到她又有点不自在,轻咳一声:
“走吧,现在乌普萨拉的日落要等到十点呢。”
江燧点头,和她并肩走在一起。
他其实还有很多话想说,也有很多话想听她说;刚才还想吻她,又真有点累,时差也在身体里作祟。但不用着急,他们前面还有很长的时间。
此刻唯一重要的事,是这一刻本身。
江燧把手里的花束放到行李架上,空出一只手来。
终于,可以牵住了。
--
时之序:等不到人急得我差点想把机场炸了
江燧:?你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