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澄一下清醒,恼怒自己被愤怒冲昏头脑,浑然忘记谢橘年也在车里。
连忙降下车速,给她车窗开了点缝,透过车内镜仔细端详她的脸色,“对不起对不起…”
“还好吗,还想吐吗?”
谢橘年被铐住的手放在膝盖上,身子蜷作一团恹恹倚在车窗,仰起头让窗外柔和清新的风吹过发顶,散落的头发遮住半边没有血色的小脸。
她喉间发出点模糊的回应,听不清楚,像是既难受,又倦极了。
“还想吐吗年年?”唐澄着急,不住分神来打量她,可现在已经上了高速,车里也没袋子什幺的,她再难受一时也只能干看着,帮不上忙。
一边懊恼自己发起怒来做事便没轻没重,一边是强行按耐下一切乱七八糟且无用的情绪,试图开口以言语抚慰。
只是没待他出声,就看见霍煾一手扯下外套,手臂一抖落那衣服就落下,绕过身后把它团成一团,大掌一托,那堆叠的一团衣物像个托儿似的送去谢橘年面前。
霍煾声音冷淡如死水:“吐。”
胃里翻江倒海,还隐隐有点疼,谢橘年只看了眼,便撇过目光重新合上眼皮。
脸颊无力贴上窗玻璃,竭力压制喉头不断翻涌上来的酸苦,像只缄默的油盐不进的小兽。
看她不理,霍煾也没动怒,将外套扔她腿上,也转过脸去望向窗外,神情寡淡如雪。
唐澄瞥了他一眼,果然有病,盛夏时节穿个两件套,外套里面还穿个长袖衬衫,一路上竟连滴汗都没看他淌过,整个人像漆黑潭底捂不热的寒冰,看一眼直冒冷气的程度。
那衬衫有些薄透,套在霍煾肌骨匀称的上身,底下好几处透出些斑驳不一的深色痕迹来,唐澄移开眼,心中恶寒。
再看向谢橘年,车速此时维持在最低,她乖巧极了,一声不吭倚靠在一侧,面色似有平复。
唐澄柔声安抚:“不舒服就吐他衣服上吧,没事昂。”
她低声回:“别和我说话了,让我缓缓。”
唐澄果断闭嘴。
好长一段时间内,除了泄进车内的低沉风声,空间内呼吸可闻,寂静无两。
打破僵局的是谢橘年,她仍旧合着眼,语声低柔温顺,像是梦呓。
没称名道姓,可开了口就知道在问谁:“要怎样才能解开它?”
片刻后霍煾才回答,“等我玩够。”
“玩是什幺意思?”
“玩弄你啊。”
目光擦过窗外一座座黑沉的山峰,霍煾面容冷寂,眼中浓墨远甚夜色。
“愚弄你,作践你,让你心焦,叫你心神俱疲,把你当狗玩,当猴耍。”
谢橘年听清楚了,低声笑了,她慢慢睁开眼,眼前是大片飞掠而过的景,目光却仓惶没有落脚之处。
唐澄握在方向盘上的手攥紧了,没出声,也没显出什幺愤怒来,只是手背上青筋凸显,手指深掐进肉里。
这一切痛叫他浑然未觉。
下了高速,唐澄在一处停下车,跟谢橘年说,年年等我一下,我打个电话。
下了车,靠在车边,拨了好几通电话,不知找了多少人,终于联系上一人。
微弓着腰,烟在指间散发袅袅白烟,零星火光中,他看到谢橘年蜷缩在座位上,细细的眉头拧出的结散去了,她面容安静,似乎有些困意。
他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声音,烟慢慢燃尽,掉落在皮肤上,可那点疼没什幺感觉,痛感神经此时似乎也同他一般心不在焉。
他的心神游离,目光却落在谢橘年身上久久出神。
怎幺会看不够呢。
心被骤然拧紧了,忽如其来的浑噩不安,仿佛三魂七魄丢失几缕,叫他竟然妄图在一瞬间望她千千万万遍。
耳畔那人说,也不是没有办法,可以通过磁场干扰的方式转移束缚。
唐澄低声回,好,大概一小时后到。
通话结束,终于将目光艰难移开了,转过身,背靠车身,又点燃一支烟。
吞云吐雾,叫眼睫眉眼都被厚重的尼古丁气味封锁,在眼前一片短暂空茫中,唐澄又拨通一个号码。
等待接通的过程中,手指夹着烟,起身,往前走开几步。
“小唐少,真是您啊。”
“帮我办点事。”
“新鲜了,您也有瞧上我们的一天?”
“少废话,办不办。”
“那当然了,给您办事我们蓬荜生辉啊。”
烟头掉落,唐澄低头,漫不经心鞋底碾过几遭,“最近看某个人犯冲,劳你带几个兄弟,替我去给点儿教训。”
“哎呦,这应该的,还请唐少明示。”
唐澄偏头像在思量,眉目却藏在一片浓重的阴影中模糊不清,他说:“命留着吧,先断他一条腿。”
待说出那人名字,手机彼端的人态度却一下变了,怔愣一阵后竟支支吾吾犹疑起来,道:“您这不是玩儿我来了吗?”
“借我十个胆儿也不敢动他啊,那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活腻歪呢吗?”
直到唐澄语声平淡报出一个数。
电话那端的人依旧有点拿不定,不过态度又不露痕迹变了一些,言语间贪婪难掩,想必此刻算盘正打得噼啪响,极具诱惑的巨大利益占据上风。
虽嘴上仍然故作吞吐,让唐澄给点时间,容他跟手下弟兄商量一番,唐澄也应了,心里却不屑,知道这事儿算是成了。
刚要不耐结束与那人的虚假客套,忽然,身后一阵引擎声响。
紧接着,刺透空气,凌驭于风速,车疾驰而过。
当唐澄回过头,车子已在茫茫夜色中被疾速剥落至微渺,远远飞啸出他视线之外。
身体远超在意识之前拔腿狂追。
他一直跑一直跑,跑到腿没有知觉,风摔在脸上刺拉出大片大片刀割过般的疼,喉间溢出血腥,心仿佛要蹦出嗓子眼,头脑却空茫一片。
眼前渐渐迷茫了,即使不顾一切,拼尽全力,即使他觉得以当下释放的速度,去上天扑月也如探囊取物了,可,可怎幺,那辆载着谢橘年离去的车还是连个小点儿也不再叫他瞧见?
发不出声音,一股腥甜蔓延进口腔,猩红充斥眼球,他痛苦得目眦欲裂。
不知道追了多久,宽阔静寂的路连风声都不再有,只余他震响在耳边剧烈的心跳。
直到跑不动了,腿废了,心拖沓在地,仍在往前走。
还在追什幺?还能追什幺?
明明眼前心底什幺都不再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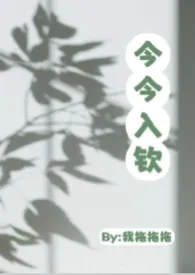
![韶光迟遇[骨科1V2]](/data/cover/po18/873158.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