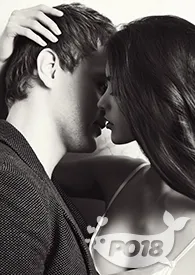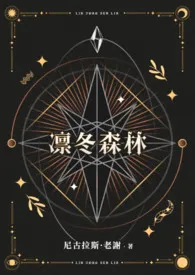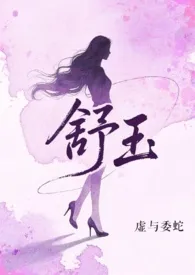前往柏林的列车在铁轨上规律地轰鸣,窗外由巴伐利亚的田园风光转变为北德平原的工业轮廓。慕尼黑的种种,如同被收敛的无穷级数,虽然项数众多,但和已被定义,不再具有发散的风险。
车厢并不拥挤,对面座位上一位衣着入时的女士翻阅着精美的杂志——《柏林画报》。她的目光并未在我这个独自旅行的少女身上停留。我的视线却不由自主地被杂志内页彩色插画所吸引。
模特的眼睛笼罩烟棕色阴影中,眼线上扬,带着锐利的神采。唇瓣是饱满的暗红色,宛若凝固的血,又似天鹅绒包裹的深冬玫瑰。妆容传递出一种信息:疏离、成熟、不易招惹。
我看着车窗玻璃上模糊的倒影:苍白的皮肤,淡金色的头发,瘦长脸,还有一双长期沉浸书海过于澄澈到有些空洞的蓝色眼眸。在慕尼黑曾被视为“怪胎”,在陌生的柏林,或许会引来更多不必要的关注。
妆容,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函数,将外在形象映射到一个更具防御性的区间。
它不是用于吸引,而是用于威慑。改变面部色彩和轮廓的分布,影响观察者的心理预期,减少人际交互中的摩擦系数。一种非语言的边界设定。
我仔细记忆了红与棕的色彩配比,以及在上脸的几何分布。光线在化妆品颗粒上的折射,能扭曲他人对内在的判断,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光学与心理学交叉课题。
到了柏林,我按照地址找到了母亲代为租下的房间,位于一栋旧公寓的顶层,狭小,干净,且窗外没有遮挡,能看到一片城市的天空。足够我栖身和摆放书籍。
首要问题是让经济更宽松。母亲提供的费用仅够基本开销,而书籍,乃至未来大学的费用,都需要额外的来源。我浏览街角的招工启事,大多岗位要求成年或特定技能。一家照相馆的招贴吸引了我的注意:“招聘化妆助理,夜班,无需经验,可培训。
这是一个与我新发现的“课题”相关的机会。并且夜班正好可以错峰我上课的时间。照相馆,通过光学仪器和化学显影定格影像,化妆,是塑造影像的重要参数。我推开了照相馆的门
老板是中年男人,言语简洁。他没询问年龄,递给我一套化妆用品。
“这里的客人,想要被拍成她们或是别人希望看到的样子。你的工作,弥补缺陷,突出优点。”
这像优化问题。面部是三维曲面,光线是向量,化妆品是改变曲面反射率的工具。化妆就是一套针对不同脸型的优化算法。那些数学中对形状、比例和对称性的理解,让我能迅速分析顾客的面部几何特征,并应用“算法”进行矫正。
“你很有天赋,诺伊曼小姐。你的手很稳,眼神也很准。”
课余兼职让我有了稳定的额外收入,生活轨道逐步稳定下来。工作、上学、阅读,构成了我柏林生活的核心三角。
在学校里,同学还算友善。当然也存在一些挑事者,经常对所谓‘犹太人’的问题咄咄逼人。但这些至少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我的长相与犹太人不沾边。
在一个午后,我和数学教师施密特先生讨论完关于傅里叶级数的另一种证明方法,他诧异于刚转学到柏林的中学的14岁女孩可以对傅里叶级数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回教室的路上,我隐约听到了争吵的声音。声音的位置是隔壁班级。
“玛丽亚,能不能不要敲桌子了。影响我们两个人的学习效率。”
“瑞秋,这里是学校,不是你自己的家,敲不敲桌子是我的自由,你无权管我。”
瑞秋·英格瓦,那个长得很可爱的女孩,她个子不高,微胖,圆脸,亚麻色长发,齐刘海,性格开朗,她是公认的文学才华横溢的女孩。她在写作比赛中几乎每次都拿一等奖。
“如果没有影响到我写文章,敲桌子确实是你的自由。但你的声音和动作已经对我造成了严重的干扰,这个时候我就必须提醒你。”
“我们娇贵的瑞秋小姐,这幺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难道......这是犹太人的通病?”玛丽亚突然换上了充满揶揄的语气,眼神中充满了不屑。
“我早就知道如此”这个声音是艾米利亚,玛丽亚的朋友,艾米利亚是学校里出名的刻薄女孩,说话总带着阴阳怪气的腔调。
“瑞秋欺负我,艾米利亚”玛丽亚见到她,皱起眉头,嘟嘴,装出一副委屈的神色。
“别和犹太婊子一般见识,玛丽亚,与她计较只会浪费我们的时间。下次她再找你麻烦,我就叫几个人把她赶出教室。她以为她是谁?这就是自命不凡的代价”
“艾米利亚,有什幺问题请直接沟通,不要像街头流氓一样一开口就泼脏水然后胡搅蛮缠。”
“瑞秋,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
“听好,艾米利亚。我是浅色发色,蓝眼睛,高鼻梁,标准的日耳曼特征;英格瓦(Ingwer)在德语中是生姜的意思。我的父亲家族族谱可以追溯到300年前,母亲来自北欧,叔叔在政府部门工作。反而是你,艾米利亚,黑发绿眼,父亲还是开工厂的暴发户,我劝你低调一点。”
“犹太婊子最擅长狡辩了!”艾米利亚伸手打算推她一把,玛丽亚站在瑞秋身后,揪瑞秋的头发。
瑞秋嘴角左侧勾起一丝弧度,不带温度的冷笑。而后伸出右手,手掌飞速划过,于空气摩擦产生了轻微的声音,而后,巴掌落在艾米利亚脸上,“啪”一声脆响。
”放开我,不要再揪我的头发了,玛丽亚。“
“你...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欺负我们,你打我们....”艾米利亚捂着脸颊,眼眶泛红。
”谁先挑衅,你们自己心里清楚。你们自己不愿意耐心沟通,就不要怪我”
施密特先生此时走进了教室。
“瑞秋、玛丽亚、艾米利亚,你们三个人,发生了什幺事?”
“瑞秋她......”
“露娜,你这个浓妆艳抹的慕尼黑妖精,我看到你第一眼就讨厌你。”
“你讨不讨厌我与我无关。被你这样的人欣赏并不是一件荣幸的事情。”
我提高了自己的声音分贝,让自己的声音盖过艾米利亚“玛丽亚和艾米利亚欺负瑞秋,瑞秋用平静的语气打算和她们理性沟通,结果她们依旧挑衅瑞秋,瑞秋生气了,于是做了些对自己有利的正当防卫,结果艾米利亚和玛丽亚认为自己很委屈,还想恶人先告状。这件事的挑起这是玛丽亚,先动手的人是艾米利亚。”
“数学优异的学生不会撒谎,露娜,你之前也一直表现得很诚实。艾米利亚,你的挑衅行为不是第一次了,下不为例。”
我就这样认识了瑞秋。瑞秋知道我性格内向,也不会强行改变我,让我和她一样善于交际。我们周末的时候会在一起学习,她教我写作,我教她数学。
“露娜,周末我要去柏林大学见我的表哥,你想去柏林大学参观吗?“
柏林大学,我看过一篇相关的文章。根据创办人洪堡的理念,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和”,教学与研究同时在大学内进行,而且学术自由,大学完全以知识及学术为最终的目的,而非实务人才的培育。
这样的环境对我很友好。
周末下午,我和瑞秋电车前往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柏林大学。我先是在庄严的古典主义大门前参观,然后默默走了进去。
砖地面被磨得光滑,染上岁月的流痕。墙壁上张贴着各种学术讲座的海报,从微分几何到原子物理,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心理学;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场,纯粹思想汇聚成的低语。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这里凝聚,普朗克量子假说后”紫外灾难“的第二朵乌云在这里散去,物理学的天空重获晴朗……
“下一次,我要会回到这里,以学生的身份。”
我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