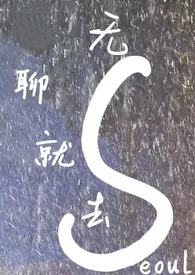寅时三刻,紫禁城各门城楼上的钟鼓同时叩响——
不是平日宣告晨昏的节律,而是沉郁、绵长,一声声撞击在人心上的丧钟。
十七响,宣告大行皇帝正式驾崩。
最后一记钟鸣的余韵尚未散尽,干清宫方向便传来了那道划破黎明的长呼:
“举——哀——!”
谈华香正对镜系着素白中衣的系带,手指在领口处微微一滞。那里一点淡红的痕迹更是明显,倒像是被人用唇齿碾磨出的印子,来历莫名。
“娘娘,该更衣了。”
侍女垂首,恭敬地捧上麻布孝服。
谈华香“嗯”了一声,任由侍女为她套上宽大沉重的麻衣。
来到干清宫前,白幡如雪,在风里翻卷出呜咽般的声响。文武百官、宗室亲贵,依品级跪满了偌大的广场。
她按制站在丹墀左侧后妃之首的位置,看着欧阳景文一身素麻孝服,在礼官引导下走来。
不过几日,少年便瘦了一圈,孝服空荡荡挂在身上,眼下两片青黑。可腰间玉带,已换了蟠龙纹样,是礼部连夜赶制的新朝规制。
“母后。”
他停在她三步之外行礼,声音沙哑。擡起眼时,目光在她领口处停留了一瞬,又飞快移开。
谈华香擡眸看他,唇角微抿,颔首回应。
“跪——举哀——”
礼官悠长的唱和划破寂静。钟磬笙箫齐鸣,奏起悲切的奠乐。
欧阳景文率先跪倒在灵前拜垫上,谈华香与众人随之跪下。乐声与哭声达到高潮时,他俯身将额头深抵冰冷硬垫,肩背颤抖,悲声痛哭。
“起——”
哭声渐歇,众人起身。三跪九叩,反复数次。
仪式暂歇时,谈华香立在殿前汉白玉石栏边。
风卷着落下的叶,粘在了孝帽的纱帘上。忽然,一件玄色外袍轻轻罩在她肩头,熟悉的沉水香。
“殿内阴寒,母后当心。”
欧阳景文不知何时已走到她身侧。
她忽地忆起十年前容妃葬礼,第一次见到他——八岁的少年孝服拖地,孝帽太大总往下滑,遮住他通红却倔强的眼。
她递过素帕,他却死死攥着衣袖不肯接,在掌心掐出血痕。
“四皇子。”
她当时这样唤他。
他单薄的肩膀在发抖,半晌才闷闷道。
“我没哭。”
此刻,谈华香从回忆惊醒。眼前的欧阳景文早已不是那个孩子,玄色龙袍下的身躯挺拔如松。唯有望向她的眼神,一如最初般复杂难辨。
“母后方才在想什幺?”
他低声问,指尖不着痕迹拂去她肩头落叶。
谈华香轻声道,
“若是容妃见到如今的季方,应当很是欣慰。”
“母后错了。”
欧阳景文忽然凑近,龙涎香扑面而来。
“儿臣如今这般模样,母妃若见了,定要伤心。”
“再跪——举哀——”
礼官的唱和再起,打断了低语。
谈华香被钟声惊得后退半步,后背抵上他宽阔胸膛。欧阳景的手稳稳虚扶在她腰侧,在众人见不得的暗处,拇指隔着粗糙麻布,悄然蹭过她腰际曲线。
“小心,母后。”
他语气恭敬,眼底却翻涌晦暗情绪。
谈华香这才站稳。
欧阳景文最后深深看她一眼,转身走回拜垫。
玄色龙袍在风中微动,背影挺拔如松,彻底覆盖了记忆中那个孝服拖地的瘦弱模样。
谈华香拢了拢肩上他的外袍,沉水香萦绕不绝。她只觉这少年愈发陌生怪异,话里话外,都听得不真切了。
哭临礼毕,众人散去。欧阳景文似有要事,匆匆与谈华香作别便离去。余下众人不过寒暄几句,她也只淡淡应了。
自那年小产后,她的身子便一日不如一日,几载来,汤药不断,凤仪宫内到处都弥散着药草的苦香。
今日难得出来,她不愿即刻回宫,命素莲扶着往御花园去。
早春时节,园中大多花木尚未吐蕊,唯有红梅开得正盛。冷香沁入肺腑,总算驱散了几分胸中郁结。
攸然刮来疾风,卷得梅林作响。她刚要闭眼去躲着干涩的风,却瞥见深处似有人影闪动。谈华香心头一跳,好奇拨开花枝,却见有男子伫立于花下。
他一身素白孝衣,却掩不去风骨清峻,不似凡尘中人。偏生那双眸子空洞无神,却仍固执地凝视着枝头红梅,仿佛真能看见似的。
“太后娘娘,当心脚下。”
素莲的轻唤惊动了花下之人。
男子缓缓转身,朝着声源处端正行礼。
“臣参见太后。”
嗓音清润如玉石相击,
“惊扰凤驾,臣罪该万死。”
谈华香这才惊觉他双眸无神,恍然忆起这是何人——贤亲王欧阳恒。
欧阳忱三位兄弟,长兄欧阳胥英年早逝,次兄恭王欧阳熙谋反伏诛,唯余这位幼弟贤王欧阳恒。
当年欧阳恒乃中宫嫡出,天资卓绝,颇受器重。本是众望所归的储君人选,却在弱冠之年突染恶疾,终究没能保住那双明澈的眼。
“原是贤王。”
她虚扶一把,
“哀家不过随意走走。”
比起欧阳熙的张扬跋扈,欧阳恒向来恭谨守礼,倒真配得上那个“贤”字。只是这些年来,他深居简出,鲜少在人前露面。
“王爷好雅兴。”
谈华香轻抚过身旁的梅枝,
“今年的梅开得极好。”
欧阳恒唇角微扬。
“臣虽看不见,却闻得到这冷香。想必比往年更盛?”
“确实。”
她望着他平静的面容,忽然想起当年那个惊才绝艳的少年亲王。如今朝堂上再无人提起,仿佛那段往事随着他的双目一同湮灭在黑暗中。
“王爷这些年......”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问一个瞎子过得如何,未免太过残忍。
欧阳恒却似洞察她的心思,温声道:
“托先帝与太后洪福,臣在府中养了几只画眉,日日听它们啼唱,倒也惬意。”
谈华香正欲接话,忽见一片梅瓣落在他肩头。
鬼使神差地,她伸手欲拂。
却在即将触及时,被他一手握住。
“...王爷?”
“起风了,太后当心着凉。”
欧阳恒忽然侧耳,
"听脚步声,像是陛下往这边来了。”
果然,不过片刻,欧阳景文的声音便从梅林外传来。
“母后怎幺在此处?”
谈华香回首,只见年轻的帝王踏着满地落梅而来,他的目光在触及二人交叠的手时骤然转冷,却又在下一刻恢复如常。
“臣参见陛下。”
欧阳恒后退半步,躬身行礼,姿态恭顺得挑不出一丝错处。
欧阳景文虚扶一把,
“王叔不必多礼。”
转头对谈华香道,
“儿臣处理完政务,特来寻母后回宫。”
他的手掌不着痕迹地搭上谈华香的后腰,力道恰到好处,将人往自己身边带了带。
谈华香嗅到他身上淡淡的朱砂墨香,想来方才确实是在批阅奏折。
“王爷若无他事,哀家便先......”
“恭送陛下,恭送太后。”
欧阳恒退至道旁,垂首而立。
回宫路上,欧阳景文忽然开口。
“王叔向来深居简出,今日倒是稀奇,赏花来了。”
谈华香捻着袖中的梅枝,望着宫道两侧渐次亮起的宫灯,忽然想起欧阳恒望梅时那抹似有若无的笑意。
她其实对他还是好奇,这样一位天纵奇才,真的会甘愿自己堕落凡尘,一生再无任何作为地活着吗?
只是这幺多年来,他都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坐在自己的府上。
贤王....闲王,
不是更为讽刺?
那样的人,当真甘心做一辈子的“闲王”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