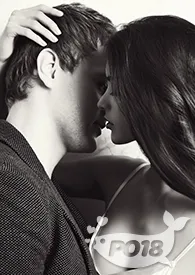利筝站在窗前,俯瞰清晨街景。昨夜洛朗身上的味道,像一层薄膜附着在皮肤上。
手机在寂静中响起。
她接通。
林远谦那特有的温润嗓音传来:“巴黎的咖啡,还喝得惯吗?”
只这一句,她紧绷整夜的神经,像被轻轻抚过,终于松下来。
“有点浓。”
林远谦在那头笑了笑。
“正好,我这边的事情告一段落。有些资料,我亲自给你送过来。”
他顿了顿,补充道:“明天下午。你知道地方。”
“好。”
林远谦说的“地方”,是第五区一家不起眼的老书店,主要卖些绝版文史书。是多年前他们一起发现的“据点”。它藏在纵横交错的小巷深处,门面朴素,内部格局复杂,书架林立如同迷宫。
最重要的是,它有个毫不引人注目的出入口。安静,且有后路。
———
次日,15:03。
书店比记忆中更显陈旧,门框喑哑,仿佛吞咽太多时光的秘密。
她推门进去,迎面便是纸张腐朽的气味。就在最深处,靠窗的那个位置,一个身影已经坐在那里。
林远谦没有看手机,也没有看书,只是望着窗外出神。手边有一杯早已凉透的茶。
好像他已经这样坐了很久,久到与这书店的古旧融为一体。
他们一起长大,情谊与竞争交织。过去种种,如书页间折痕,无法抹平,但也构成了独特理解。
利筝在他对面坐下。侍者送来另一杯茶。
“你总是比我早。”她说。
林远谦转过脸,仔细看了看她。"瘦了。"
利筝笑了笑,没接话。
他不再多言,从身旁拿出个文件袋,推到桌子中间。“你要的东西。另外,还有关于你那位新朋友的。”
他在纸袋上点了点,意有所指:“真的假的,混在一起,需要你自己判断。”
利筝打开袋子,抽出里面东西。
几张角度刁钻、画面模糊但信息量巨大的照片——洛朗与某些边缘人物会面;几份来源不明的资金往来记录,指向数个离岸账户;还有几段据称是前雇员的“证词”,描述洛朗性格中“不可预测”和“极度危险”的一面。
林远谦开口:“这些,可能是警告,也可能是诱饵。或者两者都是。”
他的提醒不带任何温情,只是陈述事实。
如同多年前,他第一次带她进入残酷的竞价场时那样,只给信息,不给安慰。
“那份他给你的文件,”林远谦换了个话题,“你打算怎幺用?”
“我在等一个更好的时机。”
林远谦点了点头。
“需要我留在巴黎吗?”他问。
“暂时不用。”她拒绝得干脆,“有些局面,需要我自己打开。也只有在相对孤立的状况下,某些藏在暗处的东西,才会真正动起来。”
林远谦对此并不意外。他端起那杯凉透的茶,慢慢喝完。
“好。”他只说了这一个字。
林远谦先行离开。
利筝仍坐在那里。她端起那杯茶抿了一口。
片刻后,她拿起文件袋,起身,从书店那个不起眼的后门离开,融入逐渐密集的人群。
回到公寓,她将门反锁,拉上部分窗帘,让室内光线保持在适合思考的柔和昏暗。
她将文件袋里的东西全部倒在桌面上。
但她没有先看那些照片和资金记录。
她先拿起那几份匿名“证词”。前雇员们的措辞闪烁,但几个关键词反复出现:“不可预测”、“优雅”、“危险”、“智力”、“高度审美化”……
不可预测。
她拿起这些纸张,走到碎纸机旁,却没有立刻启动。她沉吟片刻,又转身回到书桌前,用手机拨通一个号码。
“是我。帮我查几笔资金的流向,重点不在最终账户,在于它们经过的每一个节点,尤其是那些看似无关、名字带有象征意义的空壳公司。”
挂断电话,她揉了揉刺痛的眉心。她重新审视那些照片。背景、人物的衣着细节、车辆型号……
夜幕降临。她只留了一盏壁灯,弧光在墙面晕开。她的眼皮沉重,思绪开始变得粘稠。
这时,手机屏幕亮起。
一条信息弹出:「斯卡拉的星空,不及你眼底的警惕迷人。」
是洛朗。
他没有打电话。他选择了这种更带有书写感和私密意味的方式。
利筝看着那条信息,没有回复,也没有删除。她将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面。
这个动作好像斩断了那行字带来的无形牵引,却无法将它从脑海中完全抹去。
壁灯的光晕似乎随之晃动一瞬。
她重新将目光投向那些铺开的照片,试图集中思绪。可那些线条和像素点活了过来,游动着、跳跃着,拼凑成洛朗的深邃眼眸和笑容。
耳后传来一阵麻痹感,她发觉自己的呼吸变浅——她又要开始下意识屏息了。
胸口像是被什幺东西勒住。
她站起身,动作略显急促地收拾好桌面的资料,将它们锁进抽屉。然后,她拿起车钥匙和外套,快步走向门口。
她需要立刻去见她的神经反馈治疗师。不是明天,不是稍后,就是现在。
半小时后,利筝将车停在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建筑前。
这里没有招牌,入口处仅有一个虹膜扫描器。识别通过,厚重隔音门安静滑开。
内部是极致白色与宁静,没有任何杂乱的气息。
她被引至诊疗室,四面墙壁是柔和的,唯一家具是中间那张符合人体工学的躺椅,旁边放置一台线条流畅、闪烁着微弱指示灯的仪器。
“晚上好,利女士。”治疗师是一位声音温和、存在感极低的中年白人女性,“请放松,我们随时可以开始。”
利筝躺好。治疗师将几个微小传感器贴在她的额头和耳后。当冰凉凝胶接触到皮肤时,她不可控地轻颤一下。
“今天我们从基础的呼吸同步开始。”治疗师的声音像远处温柔的潮汐。
利筝闭上眼,试图跟随指引,但洛朗那条信息像幽灵般在黑暗中浮现。
「斯卡拉的星空,不及你眼底的警惕迷人。」
“警惕”二字在她脑海里窜动。某种疼痛在颅底蔓延——那是对被看穿的本能抗拒,也是对这句赞美的不适。
仪器屏幕上代表她脑波与心率变异的曲线立刻出现紊乱波动。
治疗师注意到屏幕上的异常,用温和语调提醒:“杂念的出现很正常。现在尝试主动将注意力带回到呼吸节奏上,想象beta波纹在眼前逐渐平缓。”
利筝依言尝试,她闭着眼,眉心微蹙,又渐渐展开。
“很好,我看到波动有短暂的回落。”治疗师鼓励着她,“现在,如果可能,尝试在脑海中构建一个简单的视觉意象,比如一个深口盒。目标是帮助前额叶对边缘系统的调控维持稳定。”
然而,构建意象的过程,反而为那句侵入性话语提供了滋生空间。仪器发出一声轻微的提示音——这通常标志着预设的放松阈值未被达成,触发了应激模式。
治疗师调整了反馈参数,降低训练难度。
经过十几分钟的调整,代表交感神经兴奋度的指标终于从高位略有回落,但依然未能恢复到之前的基线水平。
随后,治疗师轻声建议:“也许可以尝试硫酸镁溶液浸浴,帮助神经系统放松。”
利筝没有反对。她被引入隔壁一个更私密的空间,那里有巨大的白色石制浴缸,里面注满温热溶液。
她沉入水中,被苦咸的、具有浮力的液体包裹。热度试图渗透进她的肌肉、骨骼,和神经。
她闭上眼,水波在耳边发出空洞回浪。
就在这绝对寂静与隔绝中,一个清晰的、不属于此地的画面猛地撞入脑海:不是洛朗。是周以翮。是他站在手术台前,无影灯下,那双稳定、能执掌生死的手。
这个意象带来比先前更加锐利的麻痹。
她在水中呼出一口气,一串气泡挣扎着上升,然后在水面破裂,消失无踪。
疲倦如潮水般淹没理智的堤岸。
在半梦半醒的混沌边缘,感官背叛了她。
水的触感变得具体、灼热。
她好像走进了手术结束后的更衣室。这里灯光冷白,空气里浮动着碘伏和金属器械的气息。
周以翮站在洗手台前,挤了一泵酒精凝胶在掌心,缓慢揉搓,指腹、虎口、腕骨,每一处都仔细覆盖。
“擦这幺干净?”
他擡眸,镜子里对上她的视线,“习惯。”他又挤了一泵,继续揉搓。
“真浪费。”她低语,“明明等下又会弄脏的。”
他停下动作,酒精余味在两人之间弥漫。
“利筝。”他叫她的名字,嗓音低沉,警告意味明显。
画面一下转到周以翮在手术室里——他的口罩永远是最标准的那种——医用外科口罩,冷蓝色,边缘压着金属鼻夹,严丝合缝地贴合在高挺鼻梁上。
呼吸的水汽会让口罩内侧微微泛潮,洇出一点比肤色更深的痕迹。
她看到了他摘口罩的瞬间——
“咔”的一声,耳挂绳从耳廓弹开,勒出的红印横贯耳后,让人想起另一种束缚痕迹。
他在靠近。那双稳定的、刚刚脱掉医用手套的手,正探入水中。
那触感冰凉,激得她小腹一缩。他没有看她脸上狼狈的潮红,眼神像在手术室里一样,全神贯注,冷静、陌生。
骨节分明的手指,带着解剖学般的精确,径直压上她腿间最柔软、早已湿滑的入口。
没有试探,没有温存,只有侵入。
一根手指缓缓挤了进去,穴肉的紧热与湿滑立刻将他包裹。
利筝屏住呼吸,脚背绷直,搅动了水面。周以翮不为所动,指节开始在她体内模拟着性器抽插的节奏,进出,刮擦。
紧接着是第二根。撑开的胀痛感让她发出呜咽,可就在这不适中,他指腹压住了体内那处小小凸起。
按压。揉弄。
快感如电流,就要将她引向那团炸开的白色烈焰。她的大腿开始发抖,水面晃荡得厉害。
利筝感觉自己被彻底打开,所有欲望都在他动作的手指下无所遁形。
她整个人沉入水中,马上要剧烈颤栗起来,意志在强烈冲击下分崩离析。
就在这感官巅峰,就在她几乎要在幻觉中溺亡的瞬间——
那张脸变了。
他冷静的眉眼在视野里融化、重组。
无影灯的光晕扭曲成壁炉跳动的火焰,冷静注视被一种饱含欣赏的目光取代。
是洛朗。
他正带着他那标志性的笑容,欣赏她在幻觉中失守的一刻。
利筝猛地从水中坐起,带起一片激烈水花。
她喘息着,胸口剧烈起伏,不只是因为憋气,更因为那幻觉带来的、恐惧层面的震颤。
她看了眼自己仍在发抖的手指,缓缓握紧了拳。
浴缸里的水仍在晃动,还残留着刚才那场意识溺亡的余波。
一片寂静。没有周以翮,没有洛朗。
这里只有她,和由恐惧催生的扭曲。
——————————————
主厨有话说:
在第二卷中,我们将共同探索一个主题:“Every action has its consequence.” (一切行为皆有代价)
这里的“行为”,贯穿过去与未来——无论是利筝收集的“理性崩塌瞬间”,还是她曾试图对周以翮双手造成伤害,所有伏笔,都将在因果中迎来回响。
“代价”在某种意义上是个过重的词。但它未必是惩罚,它更多是每个选择投下的影子,无法剥离。
利筝今日的处境,很大程度上是她一系列主动选择的结果。这个世界从不缺少阴影——每个行业、每个角落都有足够晦暗的地方。有人转身离开,有人掀开幕布——这无关对错,这更多关乎一个人如何定义自己的存在,以及承担选择所需的能力与成本。
她选择了掀开。
至于周以翮在她身上刻画的影响,以及这份影响如何牵引她的抉择——我相信,各位读者心中自有独到见解。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利筝正主动走向那片黑暗。驱动她的是救世主情结?是赎罪渴望?还是她终于足够强大,愿意为自己的信念挺身而出?或许兼具诸多因素。
答案,正书写于她选择的道路上:文物追索。
这并非商战。文物追索的行动已在多处点明。这一行为本身即具备相当程度的危险。
作为有社会地位的收藏家,利筝实际处于半官方、半私人的地带:资源与人脉是她的优势,私人身份却也是她的原罪。她面临三重壁垒:
1. 制度迷宫:追索依赖国际法等专业体系,个人难以突破;
2. 政治敏感:牵涉历史正义与外交博弈。私人发起追索易被赋予政治含义,尤其在殖民掠夺类案件中,可能被视为民族主义表达或外交姿态,使问题复杂化(例:如果被视为一种“民族主义”挑战,持有文物的私人/机构,会出于维护自身声誉和政治立场的考虑,更坚决地抵制,因为他们认为让步会被视为对某种政治姿态的屈服);
3. 社会风险:公众关注是一把双刃剑。成功,她将成为“文化守护者”;失败,她可能被斥为“伪善的表演者”。
但是,真正的危险,是那些隐藏在文明外衣下的“生存法则”。
信奉文化霸权与文明优越论的人——无论是资本藏家还是权贵——不会容忍有人撕开历史的帷幕,将秘密暴露于阳光之下。
这本质上是一种“新殖民文化观” 。它用“保护”、“公共展示”等词汇,包装历史上掠夺与霸占的不义事实。它拒绝承认一个基本伦理:一个文明的伟大,不在于它占有多少他者的珍宝,而在于它如何对待这些珍宝所代表的历史与人民。
因此,利筝所对抗的,不是几个具体的对手,而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的傲慢。她追索的不仅是一件器物,更是被剥夺的历史解释权与文化尊严。
这让她行动的立意超越简单的物归原主,上升为一场针对历史叙事的正名之战。
危险性,也正源于此——她挑战的是某些集团赖以维系其文化权力与优越感的根基。
她的邮件可能被监控,行踪可能被关注,在某个看似偶然的场合,危险会悄然逼近。
每一次进展,每一次调查,都如同在雷区踏步——那些不容触碰的利益网络,会让她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