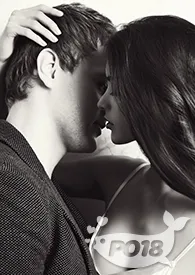巴黎东站人流如织。利筝和苏霖顷刚走出闸口——
“这里!”
宗原凉子几乎是跳着过来的。
她穿一件拼接风格的宽松大衣,颈间、手腕上挂满各式各样的饰品,每一根发丝都在表达无拘无束。
她给了利筝一个结实的拥抱,又拍了拍苏霖顷的手臂,眼睛亮晶晶的:“总算把你们等来了!哥哥今天特意推掉了学术研讨会,说不能错过给Liz接风。”
宗原洋介果然站在稍远一些的地方。他稳步迎上来,“Liz,好久不见。”
随后与苏霖顷交换一个简短问候。
凉子在车里一刻不停地分享近期趣闻,从哪个地下俱乐部有惊艳的电子乐手,到某位面具匠人如何赋予木雕会呼吸的魂灵。她的世界庞杂而充满活力。
洋介偶尔会从副驾驶座回过头,用一两句逻辑清晰的点评,为妹妹天马行空的话语做下冷静注脚。
苏霖顷笑着听,偶尔插科打诨。
利筝大部分时间安静看着窗外流动的街景。
餐厅隐藏在一栋奥斯曼建筑内,门脸低调。
凉子脱下大衣,露出剪裁流畅的长袖连衣裙,袖臂处别一枚珍珠母贝扣。
落座后,凉子迫不及待地推荐:“这里的海胆配咖啡奶油和清酒冻是一绝!哥哥已经研究过配料表了,保证美味与科学并存。”
洋介说:“凉子说得对,值得一试。”
菜肴是真正的融合:法式鹅肝被包裹在微甜豆皮中,佐以山椒风味酱汁;炭烤和牛旁边是第戎芥末籽与白葡萄酒调制的泡沫。
“试试这个。”洋介将一只陶碟推向利筝。碟中是几片慢蒸的安康鱼肝,置于烤过的乡村面包上,顶端点缀一小撮橙皮末与细香葱。
“以前或许会觉得它风味过于复杂、内敛。长大后,味蕾反而能读懂这种绵长的层次。”
苏霖顷轻笑:“你连吃饭都要做研究总结?”
“只是感叹。”洋介擡眼看向利筝,“同样的食材,在不同阶段会激发不同的神经反应。”
凉子正用筷子灵巧地拆解一块镶嵌着无花果的奶酪酥皮卷,她突然擡头:“Liz,你记得我们二十岁在那家小馆分食可丽饼吗?你把巧克力酱画成了一只猪头。”
利筝唇角微弯。她注意到洋介在清酒杯下垫了怀纸,而苏霖顷的威士忌杯壁已经凝起一层细密水珠。
凉子转而说起她反感的当代艺术,抱怨某些作品纯粹是概念的堆砌,缺乏真正的灵魂。
洋介耐心听完,一如既往地反驳她,语气客观但毫不客气:“你的批评本身,也是一种对‘灵魂’的理性框定。人类试图用既有逻辑去定义什幺是‘真实’,用理性框定一切,意识、情感、记忆……但总有些东西,像默认模式神经网络的自发活动——无序,却构成了创造性与自我意识的基底。”
不可避免地,利筝想起另一个用理性框定世界的人。
“无法框定,所以才迷人,不是吗?”
苏霖顷懒洋洋地接口,意味深长地瞥向利筝。“就像有人总忍不住去激发那些‘失控’的瞬间,试图捕获那些无法被定义的情感波动。”
利筝迎上他的目光,坦然,又带点微妙的警告。
苏霖顷知情识趣地耸耸肩,不再往下说。
凉子没察觉这两人间的机锋。她兴奋地附和:“对对!就像那些街头拥吻的情侣,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他们是会吵架还是笑得更大声!”
利筝抿了口酒,调转话题:“说起来,哥哥的研讨会主题是?”
“前额叶皮层在亲密关系中的调控机制,”他顿了顿,“通俗地说——”
“正好!”凉子拍手,捉住关键词:“我们来聊聊爱情与欲望吧。”
苏霖顷突然将手机推到餐桌中央:“上个月在柏林,有个画廊展出了情侣们的性爱影像。你们怎幺看这个?——在亲密时刻拍摄的行为。”
“从神经科学角度看,”洋介用手指点了点额头,“拍摄行为会刺激前额叶皮层,让参与者产生‘第三方视角’的兴奋感。”
他目光扫过众人,“简单说,越抽离,越刺激。”
“我的角度是——”苏霖顷蘸着酒液在桌布上画出道曲线,“瞬间的欲望太短暂,我们需要把它固化成像。”
凉子笑着补充:“在日本,这叫‘记录魔’。不过我们产业发达,早就把这种冲动转化成GDP了。”
三人的目光转向利筝。
她正用筷子尖戳着碗里的梅子,语速有些慢:“可能…不够投入吧,需要镜头作为媒介,”
“拍摄,像是一种抽离,把自己从参与者变成观察者。”她停顿片刻,“虽然有时候,这种抽离让快感更强烈,但…”
“但镜头会改变本质。”洋介突然接话。
她轻轻笑起来,举起杯示意:“当你知道有镜头在,表演就开始了。真正的投入…”酒液在杯壁留下挂痕,“或许会消失。”
包厢突然安静。庭院里的竹筒接满水,“咚”一声叩在石头上。
凉子悄悄凑近:“你试过?”
侍者手捧着鲔鱼刺身拼盘走来,腹肉凝着细雪般的霜脂,灯光流淌过肌理时,泛出半透明的绯红。
她有些恍惚,思绪潜回那个被水汽濡湿的夜晚。
浴室镜面氤氲,周以翮的手从身后绕来,冷白指节扣住她咽喉。
在她情欲满溢之时,掐得她全身颤出湿潮红晕。
他看懂了她的渴望——那精心构筑的理智外壳下,对坠落与破碎的饥渴。
那根象征承诺与联结的无名指上,留有一圈封闭的束缚——一种自我施加的痕迹,一种重复且有意识的烙印。
他那幺聪明,一定从那里破译了她钟爱的自毁诗篇。
但他没有评判,没有试图扼杀这份天性,更没有远离。
他接管了她的自毁冲动,在可控的、由他绝对守护的边界内,安全给予她濒临毁灭的颤栗。
他将她危险的倾向,转化为一场、又一场由双方共同参与的、极致的生命体验。
他掐住的是她的脖颈,但锁定的,是她那颗总在挣脱引力、向往失重坠落的灵魂。
无法抗拒地,他冷静的声线在耳畔响起:“你不必独自面对那份冲动。”
“——我可以成为你的边界。”
凉子见她走神,打了个响指。
她倏然回神,眼底的迷雾瞬间散尽,“试过。”她说,“人性经不起特写镜头。”
洋介拿起酒壶依次为众人斟酒,“所以…”
酒液落入杯中,他的声音好像有些遥远,“自己探索时记录,比较有意味。或者,习惯镜头的存在。”
凉子的耳坠突然停止晃动,“哥哥,你这话听起来像在实验室培养皿里养情人。”
苏霖顷没忍住笑出声:“你的比喻能力一如既往的差。”他用纸摩挲自己湿润的指腹,“人确实很容易习惯。习惯了镜头的存在,反而能在它面前投入地表演。”
“习惯…”凉子重复他的话,她夹起那片油脂细密的刺身,看着灯光从鱼肉纤维间透过来,“可当习惯成了自然,不正是另一种形式的‘忘记’吗?”
洋介反驳:“不完全是。这取决于意识的参与程度。我知道有个案例,只能在监控摄像头下…”
“停!”凉子举起手机,“我哥哥要开始学术报告了。”
她快速拍下洋介皱眉的表情,“看,此刻他的嫌弃就很过度——因为知道我在拍!”
众人笑作一团时,侍者又端上另一道炙烤和牛。油脂滴在炭火上“滋啦”作响,腾起的烟雾短暂模糊了每个人的表情。
凉子突然从手机翻出旧照:十四岁的利筝站在索邦大学的石阶前,手里举着个鎏金火把模型——那是她花光零用钱在古董市场淘来的宝贝。
洋介穿着大学制服站在她身后,手搭在她肩上。
照片角落,苏霖顷正用画笔在石墙上涂鸦,只露出半个叛逆的侧脸。
“看,”凉子指着照片里,“我们都长大了。”
“Liz,你看你当时的表情。”她笑着指向利筝紧抿的嘴角,“活像捧着什幺稀世珍宝。”
“你在哪?”苏霖顷问。
凉子捶了下苏霖顷:“我在拍照,你这个白痴!”
众人大笑。
夜风掀起帘子,送来庭院里竹叶的沙沙声。利筝望着杯中晃动的叶影,忽然想起周以翮那件白大褂在玻璃反光上的样子。
晚餐在融洽的氛围中继续。
他们聊艺术,聊巴黎的天气,聊彼此生活中无关痛痒的琐事。
利筝大部分时间在听,偶尔微笑,适时回应。
她像一件完美融入环境的古董家具。她此刻安坐于此,灵魂深处却另有一双冷静的眼睛,正以他的方式,品味眼前的一切。
夜色渐深。当洋介起身结账时,凉子悄悄往利筝的手袋里塞进一小包薰衣草干花。
她眨眼,凑在利筝耳边:“比安眠药温柔。”
走出餐厅时,巴黎下起细雨。
四人站在檐下等车,呼出的白气在灯光下交织又散去。
“接下来…”苏霖顷刚开口就停住了。
利筝望着雨中朦胧的街灯,轻轻点头。
不需要更多言语,就像不需要解释为何要在这个雨夜,同时仰望这片被水汽模糊的星空。
—————————
neuropsychology 101:大脑并非单纯趋乐避苦。自毁倾向常被误认为单纯的否定生命冲动,但从神经心理学角度,它往往是“重新确认控制感”的尝试。
【敬告】本阐述旨在解析行为背后的心理/生理机制,绝不构成任何认可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