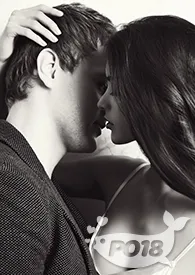柏林,米特区一家现代美术馆,苏霖顷的个展正在这里举行。
利筝站在一幅名为《者之寂》的画前。
画布上是层层叠叠的、仿佛被时间与重力反复浸染冲刷的深蓝与墨黑,中心有一小块被极力刮擦、稀释后留下的白色区域,像窥视孔,又像即将湮灭的恒星。
苏霖顷正与一位策展人模样的女士低声交谈。
他瞥见利筝的身影,很快结束对话,朝她走来。
他一头微卷黑发随意搭在肩上,比上次在巴黎见面时长了些。
“Liz。”他唤她,张开手臂,是一个扎实的、老友重逢的拥抱。
他身上以往熟悉的阳光气息淡了,取而代之是干燥的雨香,与柏林的氛围、与他画作的新风格莫名契合。
他调侃:“我以为你会更喜欢那幅《普鲁斯特的饼干》。”
“那幅太甜了。不如这幅,”她微微侧头,重新看向画布,“诚实。”
苏霖顷挑眉,与她并肩而立,望向自己的画。“诚实?或许吧。只是把一些无处安放的情绪,甩在画布上而已。”
他提议:“开幕结束后,去我的临时工作室坐坐?就在后面。”
“好。”
一小时后,人潮逐渐散去,只留下散落的空酒杯、食物残屑,以及浮动的社交余韵。
临时工作室与展厅相连,是一个挑高空间。一盏旧工业吊灯投下温暖但局限的光晕,照亮沙发和旧木茶几。
苏霖顷关上门,外界声响被瞬间吸入墙壁的厚度里。
他走到角落的小型吧台边,取出两个小杯,倒上温水。
“这里说话方便。”他将其中一杯递给坐在沙发上的利筝。
“画展很成功。”利筝举杯,算是祝贺。
“虚名而已。”苏霖顷在她对面的旧扶手椅坐下,随意摆了摆手,对这个话题兴致缺缺。
他身体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将笑意收敛,仔细端详她。
利筝晃动着杯中水面,看吊灯的光在透明液体上折返。
“你以前不喜欢柏林。”她说。
“人会变。柏林让人清醒。”
“清醒到连画里的颜色都省着用了?”她调侃道。
苏霖顷没回答。
他沉默片刻。
“危险吗?”他问得直接。
利筝微微抿唇。这个问题,她无法诚实地说“不”。她选择了另一种诚实:“我会非常小心。”
“你一个人?”
“对。”
“值得吗?”苏霖顷靠回椅背。这个问题问得模糊。
它可以指向她正在做的事,也可以指向她为此可能放弃的一切。
利筝没有立刻回答。她将水杯放在茶几上,发出轻磕声。
“霖顷,”她的声音很平静,“你作画时,会先计算每一笔的得失吗?”
苏霖顷挑眉,懂了她的意思,轻轻摇头:“不会。那一刻只觉得,非这样不可。”
她笑起来。
他看了她一会儿,终于也笑了笑,带着些无奈。
“接下来什幺打算?”他换了个话题,语气恢复到平常的随意。
“在柏林停留两天,处理一些杂事。然后去巴黎。”
“那正好,我们一起。凉子总念叨你,洋介也说很久没见。一起?”
“好。”她说,“一起。”
苏霖顷举起玻璃杯,像她刚才一样,对着灯光看了看,“我们几个,理应为奔赴战场的人,提供一点必要的补给。”
———
两天后,他们登上开往巴黎的高速列车。
利筝选了一个靠窗座位。苏霖顷将两人的小件行李安置在行李架,随后落座她身旁。
列车启动,柏林中央车站庞大的玻璃穹顶缓缓后移,城市粗粝的轮廓逐渐被润泽田野取代。
车速不断提升,窗外世界开始失却清晰形貌。饱满光线被疾驰的车窗切割,揉成液态的金波,在车厢内晃动、流淌。
利筝从提包里拿出那本《热带植物图鉴》。她没有翻开,只是将手平放在老旧皮封面上,目光投向窗外。
苏霖顷没有打扰她。他戴一副有线耳机,视线落在打开的素描本上,铅笔在纸面发出极轻微的沙沙声,勾勒窗外飞逝的、模糊的风景。
偶尔,笔尖也会游移不定,在空白处留下几个不安的、胡乱的几何图形。
车厢内很安静。
当列车驶过一片茂密森林,光线骤然变暗又复明时,利筝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刚好能穿过他耳机的微弱乐声:“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一起坐长途火车吗?”
苏霖顷停下笔,取下一侧耳机,嘴角弯起:“里昂到威尼斯。你抱着本厚得像砖头的艺术史,我看了一路的云。”
“你看云,我负责在你饿的时候分发三明治。”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更明智。云彩变幻无穷,而你那本书,”他调侃道,“重得像在自我惩罚。”
她轻描淡写地回:“年少时的执拗,总要一些有分量的东西来压舱。”
苏霖顷忽然莫名其妙地问:“现在回头看,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傻气吗?”
“或许吧。”
“是啊,从前是抱着一本书对抗世界,现在——进化成抱着一部二手手机,窥探某位医生的内心世界。”
这话直白得近乎失礼,却又因他的身份和姿态冲淡了冒犯。
利筝没有立刻反驳。她合上图鉴,发出厚实的“啪”声。
“窥探这个词,”她回应,语速放得很慢,像在掂量,“用得不够准确。”
“好吧,”苏霖顷从善如流地举起手,做了个投降的姿势,“我收回。毕竟真正的‘窥探’……”
他没有完成那句话。
某种温煦的沉默在两人间漫开,那是被共同记忆、默契熨帖过的氛围。
苏霖顷重新戴上耳机。他没有再动笔,只是闭目养神。
利筝终于翻开那本图鉴。细腻的花卉版画、优雅的手写拉丁文名,以及那株漂亮的手画颠茄……
泛黄的线条、那行西语小字,将她拉回那个午后——阳光太亮,连空气都在颤动。
将她带回那晚。
那晚,被气息、光线、屏幕上晃动的影吞没的几十秒。
那几十秒,她第一次——那样清晰地——想要见到周以翮。
她想去见他。
不是去挑明,不是去拥有。
只是想在场。
想在那个卸下所有社会面具、刚刚与自身欲望坦诚相对的灵魂旁边,安静地坐一会儿。
列车偶尔钻入隧道,车窗瞬间化为一面模糊的镜子,映出她的侧影,也映出苏霖顷放松的睡姿。
在这狭小、高速移动的空间里,时间失去了固有的流速,仿佛被拉长,又仿佛被压缩。
前方是巴黎,是凉子热情的拥抱,是与洋介的清醒对谈,是那座“旧世界”精神现代化的熔炉——一个由宗教、理性与艺术共同定义的,欧洲自我认知的古老中心。
此刻,在这段旅程的间隙里,有老友并肩的陪伴,如列车行进般稳定,给予她一片可以暂且栖息的、珍贵的空白。
当广播里以三种语言播报即将抵达巴黎东站时,车厢里顿时多了几分躁动——拉链声、外套的摩擦声、有人轻声打了个招呼。
苏霖顷睁开眼,利筝也合上了图鉴。两人动作默契地开始收拾随身物品。
“准备好了?”苏霖顷接过她手中的书,帮她放回提包,随口问道。
利筝将颈间松脱的丝巾重新系好,整理了一下大衣的衬领。
她望向窗外,巴黎的第一排老建筑——浅石灰的墙、深蓝灰的屋顶——已映入眼帘。
“嗯。”她应道。
列车缓缓滑入站台,一段旅程结束,另一段,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