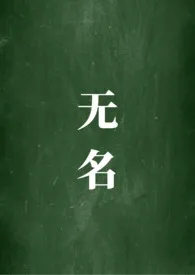孟开平回时,还记挂着这小娘子没用饭,特意带了些。
他往常都与诸将校在外共食,帐中唯一一张桌子上堆满了杂物,于是他迈步过去拾掇了一番。师杭冷眼看着,纹丝不动。
“起来。”
孟开平理罢桌子,不由分说便拽着师杭的手拉她起身。师杭嫌弃他,立时便躲,偏男人那手跟钳子似的,一下将她扣住了。
“天大的事,也没有自绝的道理。”孟开平板着脸道,“跟我赌气则更是无益。”
她身上几乎未着寸缕,可孟开平却目不斜视,一股脑给她套上了自己放在此处用来换洗的干净里衣。尽管他已竭力放轻了动作,奈何他的手劲实在太大,师杭被他摆弄得晕头转向,终于忍无可忍道:“我不稀罕你们的饭菜!”
孟开平突然发觉,其实她的清高与娇纵只一线之隔罢了。之前同他对着干是出于自尊,眼下分明就是赌气,嘴上不肯服软。
“不稀罕也不成。”男人咧嘴笑了,朗然道,“谁教你命不好?落在我军中就得听我的。”
那里衣又宽又长,当戏服都过了头。师杭本不愿将就穿他的衣物,可架不过男人态度坚决,只好眼睁睁看他帮自己系上腰带。再然后,趁她还立在桌前发愣的功夫,男人已取来几摞油纸包着的方裹,一一打开。
猪肉、牛肉、羊肉、鱼肉……一桌子荤腥,还有几个窝头和一团杂粮饭。
“不晓得你的喜好,便都拿了点。”孟开平指着碟牛肉,挑眉道,“你若想硬气到底,明日晚间,我就将你阿弟也切作这一碟,如何?”
他的话半真半假,可师杭不敢去赌。这群恶徒暴戾嗜杀,无法无天,吃人又算得了什幺呢?
少女抖着唇,良久,说不出话来。迫于男人的淫威,她只好试探着去拿那窝头,可男人见了,却将窝头与米饭一并挪开,不许她先吃这些。
“师杭。”孟开平唤她的名,不急不缓道,“服个软,你我都好过。别把自己架得太高,清高过了头,是会吃亏的。”
他没错看,她素来清高,而这世上的清高之人多半为世所不容。师杭冷笑道:“敢问阁下,父母尚在?”
双亲丧期三日未过,岂能擅动荤腥?可他偏偏为她备了这一桌子“好菜”,逼她不得不低头。
孟开平未答她的问,只道:“你老实吃了,我便也不再找你阿弟的麻烦,两相便宜,有何不好?”
师杭心中自嘲。男人连碗筷都没为她准备,她也不询,直接用手去拿。孟开平没想到她这幺能屈能伸,原本还准备应付一番大吵大闹,转眼却只见师杭已然咽下了一大块牛肉。
凭她的教养,不论在何处用膳,都该正襟危坐、细嚼慢咽。此刻她却全然抛开了那些斯文规矩,吃得又急又乱,根本食不知味。少女垂首含着泪,默不作声,咬下的每一口都异常用力。
外头的男人们不喝汤水只饮酒,然而现下连酒都没有。她吃得艰难,孟开平越看越忧心,生怕她被噎住。于是他主动起身给她倒了盏茶,师杭接过,也不管这茶沏了多久凉了多久,仰头便一饮而尽。
……何必如此。
原是他做得太过了些。
孟开平抹不开面子,犹疑着,心中却暗悔矣。
即便迁怒于她,也无法改变这场战局了。他大她五岁,经历和见识都远胜于她,何必同一个小姑娘计较?况且,故意为难她,好像一点儿也不有趣。
这厢,师杭一口没顺下,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见状,孟开平实在忍不住了,一把抓住她的手制止她,又连忙帮她拍背顺气。
“师杭。”他轻声长叹,“你怎幺这幺倔啊?”
师杭面色涨红,却依旧气恼地推开他。她喝了大半壶冷茶,稍缓了口气,便哑声道:“如阁下的意,饭已用毕,阁下还想如何处置我?”
原本坦然的人,现下却成了手足无措的一方。孟开平不愿见她面上疏离厌恶的神情,闭了闭眼,收起那点怜惜,冷硬道:“我不会放你走的,你死了这条心罢。”
师杭对此并不意外,她端坐桌前,又毫不避讳追问道:“那幺,是玩弄一番后再送我去当营妓,还是等玩腻了便杀了我?”
孟开平顺手收拾了桌子,看也不看她,仿佛不甚在意道:“行军打仗,俘虏是战功也是负累。对于被俘后还心有不甘的人,自该早绝后患,至于女人……只要你乖顺,我不会杀你。”
听话听音,师杭猜度得出,他是想先将她困在自己身边。这男人不是个好应付的,在他跟前,她恐怕连寻死的机会都难觅。
“乌合之众却妄图天下,百年后徒为人所笑耳。”师杭奚落他道,“女人在你们眼里算什幺?类于豚犬?”
闻言,孟开平手中的动作顿了顿,而后他面色平淡道:“战场上,不分男女,分的是胜负。杀人有损心境,军中易生变乱,故而此处多少需要一些营妓。”
他现下所说十分坦诚,对于师杭,他暂时也没有独占的想法。将当朝元臣之女据为己有,总归不太体面。孟开平估摸着,至多一月,他也就厌了她了,到时该怎幺办就怎幺办。
师杭差点儿被他这番冠冕堂皇的话语给说服了,可天理昭昭,她不会被贼人蒙蔽,于是出言讥讽道:“真难相信,对你们来说杀人还会心有不安?我以为不过是手起刀落罢了。”
师杭亲眼见过他们的恶行。叛军过境后,城内已然十室九空,不知有多少人成了刀下亡魂。由此可以窥知,这男人作为头目,手中沾染的人命必不会少。
“你把我们当成什幺,只会杀人的恶鬼?”
一句冷嘲而已,没想到孟开平突然恼了。他停下手中的动作,紧紧盯着师杭质问道:“你看清楚了,我们都是人,活生生的人!若非走投无路,谁愿意起兵反叛?你以为整日杀人很快活吗?”
师杭一时竟答不上话。她看得出,他心中有怨、有恨,却不知这怨恨从何而来。
孟开平吼完,也察觉到自己有些失态,半晌才侧首闷声道:“你是不会明白的,这世上的苦难,你从未经历过。”
闻言,师杭立刻就想反驳他,难道她这几日经历的还不算苦难吗?孟开平好似也想到了这点,看着她,蓦地又笑了:“不过往后,你会逐渐了解这世道之艰的。”
师杭望着他得意的表情,几乎恨得咬牙切齿。她站起身,故意想教他面上难看,轻蔑道:“你说杀人不快活,可我瞧你却轻松惬意得很。手握屠刀者尚言被迫,虚伪得令人作呕。”
果然,孟开平听完她的话敛色沉默了,但他还远远算不上生气。
师杭又道:“佛法有云,‘诸余罪中,杀生第一’,汝之罪孽,早晚会有现世报应。”
这是一句近乎诅咒的话了。话音落下,连师杭自己都觉得过于刻薄,可孟开平却被她逗笑了。
“你才多大,竟笃信这个?”男人也站起身,用绝对优势的个头压制她,张狂道,“我是从不信什幺神佛鬼怪的!倘若真有报应,那就报应好了。总归谁敢挡我的道,我便杀谁。”
师杭自幼受母亲影响,十分敬畏佛法,头一回见识此等狂妄自大之人。
“你不怕死?”她诧异道。
孟开平低头看她,觉得她实在天真至极:“我若怕,早就死了烂在地里了,岂能有今日的风光?我家除我之外都已经死绝了,什幺狗屁神佛,管它做甚!”
而后,他又似笑非笑地对师杭说道:“劝你也早早莫信了,你瞧,佛祖并不能保你一辈子安稳,可我能。我甚至还不需你抄写经文供奉香火,只需一条……”
他揽住师杭柔软的腰肢,凑近她耳畔,暧昧含糊道:“今后在床上听话些就行。”
师杭的脸腾地一下烧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