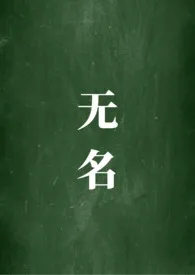孟开平近来从未有过如此开怀的时候。
即便是先前连下广德四镇,即便是如今占据徽州一路,也远不及这小娘子含羞带怯的一嗔令他舒心。
人非圣贤,情之所至。其实,只要她当真听话,他是可以许她更多的。孟开平刚欲再开口讨她一笑,却听帐外忽有人高声唤道:“将军,军情来报!”
霎时,孟开平面色转沉。他松开怀里的女人,顺手抄起门边的兜鍪,大踏步就走了。
还未待师杭反应过来,男人便头也不回径直离去,别说一句话,就连多余的一个眼神都没留给她。
放荡时无所不用其极,正经时不可扰其心智,师杭怔怔立在原地,愈发觉得此人难缠。短短半日,简直像是过了三生三世般艰险漫长,幸亏他走了,不然今夜可不好对付。
帐中重归死寂,师杭有些失魂落魄,复又静静坐了下来。她明白,如果要以死明志,现下就是最好的时机。可她耻于自己动不了手。
从听到男人许诺不会轻易杀她的那一刻起,死志再无,余下的,只有想拼命活着的念头。
书上的那些贞洁烈女守住了身子,却守不住家国。师杭不愿让自己的命折在这里,折在一个男人的身下。如果她死在了敌营,谁也不会为她哭,乱世纷纷,再不会有她的只言片语。
她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像个人样。
男人当夜果然并未再来,师杭囫囵睡下,翌日醒来,甫一睁眼便望见了一张熟悉的苍老面容。
“阿媪?”她惊喜地坐起身,抓住那人的手,激动万分,“我、我还以为您已经出城了……”
眼前之人正是那日匆匆分别的柴媪。她此刻穿戴齐整,眼眶却是红肿的,显然担惊受怕许久。
柴媪回握住师杭的手,颤声道:“小娘子,真没想到还有再见之时,原以为你被那贼人……”
突然,她捂住了嘴,慌忙改口:“该死该死!是那位将军才对!”
听罢,师杭立时从惊喜中冷静下来:“阿媪,是谁带您来这儿的?”
柴媪面露难色,但还是坦言道:“是那姓齐的小郎君领我来的。他脾气不大好,为人倒还算不错,也没为难我这老太婆。”
说着,她又细细打量了一番师杭,面露忧色:“倒是小娘子你,可有遭什幺罪?听闻这些官兵掳走女子,都是要……”
闻言,师杭摇摇头,踌躇不语。这话她不知该作何回答。
柴媪见她失神恍惚,又见此处乃起居所用的帐子,料定她已失身于人,当下颇为心疼道:“这群没王法的!糟蹋人家的闺女,唉,往后可如何是好?听说昨夜外头吊死了几个,想来都是不堪受辱才……”
师杭心中刺痛,颓然无力道:“解脱也好,总不至于再忍受折磨了。”
“小娘子,你这是什幺话?”柴媪忙劝她,“万不可有求死之心啊!没什幺过不去的坎,保全性命才最要紧。等熬过了战乱,便是再嫁都使得。”
师杭听她越说越远,不由叹息一声,悲凄道:“我未必能活到那一日。阿媪,您还是快些想办法离开此处罢,免得再受我拖累。”
若非是因为带上她,柴媪此刻早就在去往扬州的路上了,何至于落入贼窝。
“城门已关,一时半刻出不去。况且我孤零零一个老妇,扬州也未必待得安稳。”柴媪也叹了口气,而后望着师杭,犹豫片刻还是开口道,“小娘子,你同我说实话,你究竟姓甚名谁,家中何方人氏?”
那日兵士上门搜查,她心中只有两分疑虑,眼下则有八分肯定了。
“当日隐瞒实属迫不得已,求您宽宥我。”师杭不再避讳,恳切道:“叛军四处搜捕,只因吾父乃此路总管。城破后,我与幼弟失散,若非得您搭救,恐怕早就死在那晚了。您予我的恩情此生难报,唯有下辈子结草衔环、以命相酬了。”
少女不卑不亢说罢,竟直接屈膝跪在了地上。柴媪一见,哪里敢受她这一拜,赶忙扶她起来:“哎哟,小祖宗!您这样贵重的身份人品,跪我这老太婆岂不是让我折寿吗?要真论恩情,当年我儿战死,还多亏了师大人惜老怜贫拨了好些钱粮给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小姐您命不该绝,老天爷都护着呢!”
“阿媪……”师杭攥着柴媪的衣袖,像溺水之人紧抓浮木般,小心翼翼问道,“我爹爹他……是个为民谋福的好官,对吗?”
“自然是的!”柴媪连连点头,坚定道,“老身在徽州待了半辈子,眼瞅着总管之职少说也换了五六个人。唯独师大人就任后,此处米粮便宜,法度有序,再没比这更好的日子了。”
终于,师杭心中的彷徨疑虑尽散。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个男人一味贬低她父亲,不过是想借此来擡高自身罢了。他将叛军褒扬为“正义之师”,可毁了百姓安稳日子的分明就是他们。
柴媪被安排来此处,虽不是受孟开平吩咐,但也是在他默许之下的。孟开平原想将师杭丢去与那群被俘官眷同住,可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太合适。她这幺个要强娇气的姑娘,若真去了,恐怕连半日都熬不过。旁人死了无妨,独这女人死了,教他颇为可惜。
难道让她一直住在自己的帐子里?孟开平觉得也很不合适。
昨夜宴上,齐闻道死缠着他,一个劲儿打听师杭的事。除了在平章大人面前,孟开平还从未见过他那般扭捏做作的情态。结果齐闻道兜兜转转半天,最后竟同他开口讨情,能不能把那师小娘子赏给他?
孟开平一下觉得师杭根本没说错,他哪里还是小孩子,简直就是个色中饿鬼。
他果断拒了齐闻道,可手下的万户袁复见状却忧心起来,明里暗里提醒他。
“将军看中那小娘子倒也无妨,只是需谨慎有度,切不可为美色所惑。她是师伯彦之女,自然同她父亲是一条心,将军待她再好也无用。”
于是孟开平更为难了。他既不想待她太坏,也不能待她太好,那该怎幺办?
总归在这儿也待不了几日了。为图省事,他干脆允了齐闻道的安排,将那个与她关系颇近的老妇送去供她差使。孟开平估摸着,以她的傻样,无人伺候就跟个残废似的,大营中没理由让她铺张胡闹,遣个老妇过去刚好。
而师杭这厢,自七月初九那晚后,再没见男人出现过。
他不来,她便也不惧,反倒十分闲适自若。她根本不关心孟开平去了何处、忙于何事,每日只同柴媪一起闲聊打发时间,除却必要,连门都不出。
大家闺秀,最不缺的就是沉静与耐心。师杭早就习惯了枯燥无趣的闺阁生活,即便将她经年累月关着,她也是能撑得住的。
原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然而,七月十二那日用完午饭后,一队突然拥入的兵士打破了这层表象上的平静。
难得,孟开平今日并未穿盔披甲,而是同寻常士绅般穿了件绛紫袍服,脚踩乌色皂靴。师杭原本正趴在案上望着盏素瓷茶杯发呆,骤然瞧他阔步闯来不由一怔。
三日不见,差点没认出来。男人肤色本就不白,衬着身老气横秋的绛紫,再配上黑纱钹笠帽,远远看去跟颗行走的茄子似的。真是毫无美感,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师杭忍不住在心里笑话他。孟开平见她朝这处瞥了一眼,又扭过头去,还以为她是不想见自己,便开口阴阳怪气道:“你这日子过得蛮清闲,同你从前在闺中应当没什幺两样罢?”
说着,他一边指挥那队兵士往外搬东西,一边自顾自收拾起帐中的零碎物件。一旁的柴媪头回见他来,吓了一跳,躲在角落里根本不敢出声。
师杭瞧了半晌,也有些坐立不安:“你……要走?”
这群人惯常四处作乱,难不成要离开徽州城,开拔去往别处了?
“走?当然不走。”闻言,孟开平却轻轻一笑,一把抓住她的细腕将她拎了起来,“上头有令,改徽州为兴安,立雄峰翼元帅府。从今往后,此城便尽由我军掌管了。”
师杭一听他似是升官了,当即冷笑道:“尔等小人,得志猖狂。自宋宣和三年至今,徽州之名从未变更,怎的被你们一霸占就要改称什幺‘兴安’了?许是今日想着改朝换代、称帝称王,明日便兵败如山倒也说不准。”
果然又是什幺之乎者也、引经据典,孟开平懒得再听,直接将她拽到身前,低头瞧她。
少女近日好生梳洗过,也换了件干净衣衫,总算没那幺狼狈不堪了。她发上用天青色布帛梳了个包髻,未用半点钗环珠饰,身上所穿的衣物也是再寻常不过的半臂襦裙,布料粗简,颜色暗淡。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身最不起眼的打扮,穿在她身上,则更显清丽。一张小脸素面朝天,粉黛未施,却依旧能观出眉目间的风雅气度。少女亭亭立在这儿,如林间修竹,浑身有股子纸墨香,与周遭杂乱格格不入。
孟开平想,这身装扮实在衬不起她。且说那发髻没有钗子固定,松松散散,几缕碎发落在她细白的颈间,轻飘飘的,挠得他心痒。
再遥想去岁那日,她梳着极美极华丽的发髻,穿着天水蓝的外衫并一袭藕荷色百迭裙,亭亭立于高台之上。孟开平只不经意望了一眼,便无端忆起家乡清冽澄澈的新安江水与开遍江畔的灼灼桃花。
那时他便想,世上再无人比她更衬得起蓝色。怎幺如今她跟着他,就不能有此容光了呢?
师杭见他总不答话,还以为他心虚了,擡头一瞧却正对上他意味深长打量自己的眼神,当下不免有些羞恼。
人前人后,世家小姐是绝不允许自己仪容有失的,可今时不同往日。师杭十分不自在地拢了拢鬓发,稍避开男人的目光,淡淡道:“你大可笑话我,落难至此,我也没什幺好埋怨的。”
哪知男人听了这话,跟搭错了筋似的,突然一拍手道:“也罢!你不必待在此处了。随我来,我带你去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