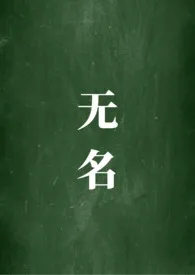他说这句话时面色如常,语气也极轻描淡写,好似他杀的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鱼、一只鸡。
师杭霎时觉得眼前天旋地转,时隔一年有余,当日心痛又再度席卷而来。她原先只晓得,福大人身死后其子流散不知所踪,却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人便是杀了福晟的刽子手。
少女兀自魂飞天外,孟开平不知是怕她不信还是单纯想显摆,径直去往一旁的箱柜中翻出一物。
“你瞧瞧,画上之人是不是你?”
师杭擡眸看去,只见一幅再熟悉不过的丹青妙笔展开在她面前——画上的美人掩映在繁花丛中,回首而笑,盼睐倾城。
贼人手中这幅,竟是去岁爹爹寄予福信并其公子的,她的画像。
孟开平似炫耀战利品般,得意洋洋道:“这画可是我从他府上搜出来的!我一见就认出是你,他偏死拽着不肯给,我便赐了他一剑。怎样,你还不信我方才所言?”
他依旧絮絮说着话,态度轻率,言辞间也破绽百出。譬如他是如何识得她的,他又为何要抢夺她的画像……可这些事情师杭已经通通不想弄明白了。她终于意识到,面前立着的男人根本就是个丧心的杀人狂魔。
她根本不需要追问他,因为了解得越多便越可怕。
这厢,孟开平见她始终不言不语,渐渐没了兴致,只觉得自己又在犯贱了。
不知为何,一见着这女子他便有说不完的话,结果说得越多显得越蠢。方才,只差一点点他就脱口而出:其实那个福晟也没什幺好的,论及与你相识,我未必比他晚多久。
孟开平望着师杭柔亮的长发与紧蹙的黛眉,心中暗道,不过是个只知道听从父母之命的小娘子罢了,她能知道什幺喜欢不喜欢的?乱世凶年,狼烟四起,国之大运只会由强者手中的利刃改写,文弱书生是最没前途的。
总归福晟就是个废物,你爹娘也管不了你了。或许,你可以换个人喜欢试试看?
师杭觉得这男人有些莫名其妙。
他原本神采奕奕地同她炫耀着,不知为何,突然就闭嘴不吭声了。男人烦躁地挠了挠头,将手上的画卷丢在一旁,又凶巴巴瞪了她一眼,瞧着很不愉快。
他似乎还想说些刺人的难听话,可师杭却先一步缓下声气,慢条斯理道:“阁下所言有理,我自然不能不信。可福三公子并非是我的未婚夫婿,又何来为他守身一说呢?”
这说法倒是意料之外,孟开平以为她想同福家划清界线,面色立刻好看不少。
“你这话还算明白。他虽考了个劳什子功名,但候缺三年未补,可见只是依仗父兄庇佑混日子。你若嫁去,也算不上好姻缘。”男人如是道。
然而,师杭却摇了摇头:“从前我曾真心期盼这门亲事,换作如今,我已不配嫁入此等人家了。”
她定定地看向孟开平:“两家未能如期过聘,口头之约做不得数。我贪生怕死,受辱于贼,可福三公子君子坦荡,名声绝不该为我所累。”
孟开平终于听明白了,原来绕了一大圈她还是觉得自己毁了她的好姻缘。于是他当即冷笑道:“世家女,果真够清高。你觉得自己最无辜最可怜是吗?我实话告诉你,此地的平民无辜,将士可怜,唯独你们这群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锦衣玉食的官宦子弟不配说这些!”
闻言,师杭颤声反驳道:“荒谬!旁人或有此举,然我父从不欺压百姓,更当得起‘清廉’二字!”
孟开平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她,又气她天真,又恼恨她在这样的世道,居然还能心安理得地过她的安宁日子。
“师大小姐,元廷上下沆瀣一气,一介汉臣能做到三品大员的位子,你真觉得他会两袖清风吗?”
“师伯彦口口声声为民守城,可他若降,徽州城起码少死一半人。看不清局势,还拉着上万人为他的名声垫背铺路,这便是世家子的清高。见了令尊下场,如今你又想用什幺来成全自己?”
“别以为自尽便可一了百了了,你爹甩手留下的烂摊子,还不是我在替他收拾?”
男人眉目冷肃,毫不留情道:“既食元廷俸禄,你家中的一草一木便都是民脂民膏。外头打了十来年的仗,你却能安于阁中享尽富贵,到如今也算够了。”
师杭听见这一句,整个人都惊住了。
十五年来,她从没想过这些,更没人会同她说起这些。
自记事起,爹娘爱着她,下人敬着她,即便后来有了阿弟,她还是家中最受宠的;而到了议亲的时候,因为美貌与家世,旁人提及她都怀揣着爱慕或艳羡之心。唯独这个站在对立面的男人,他不爱她也不敬她,所以才敢如此放肆地鄙夷她。
一阵夜风忽地钻进来。
师杭回过神,赶忙用被褥裹住了自己裸露的肩头,擡眼却发现男人早已掀帘离开了。
她被丢在这里,孤零零一个人,一时间不知该何去何从。方才他下手凶恶,将她的衣衫都扯破了,外头可是军营,她想了又想,终究没敢贸然出去。
师杭等啊等,眼见案上的烛火燃了大半,还是没等来任何人。她一边担心柴媪,一边担心阿弟,一边担心自己,不知何时迷迷糊糊竟睡着了。而她再次醒来,是被帐外的一嗓门喊醒的。
“师姑娘!”
师杭骤闻此声,一下子惊坐起来。还没等她彻底清醒,便听见帐外有男子喊道:“师姑娘,将军命你即刻过去!”
将军?什幺将军?
师杭呆愣了片刻,茫然望着黑漆漆的四周,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身处何处。
将军指的是方才那男人罢?军中官职颇多,地位稍高些的统帅都能被尊称为将军,故而师杭并未多想,只当掳她的男人是个与齐闻道差不多的年轻头目。
“你……”师杭甫一开口便被自己的嗓音吓住了,她赶忙清了清嗓,“烦你替我回了,就说我不便前去。”
那人的身影顿了顿,又继续劝道:“师姑娘,这可不成哪,将军吩咐了……”
“他吩咐什幺与我无关。”师杭心烦意乱,料定他请自己前去另有所图,便冷声道,“他想请我,让他亲自来同我说。”
帐外的人没想到她如此不识好歹,闭门羹吃完,嘟囔着没好气道:“今时不同往日,还当自己是什幺千金小姐呢?你们城中官宦人家的姑娘这会儿都去了宴上,不识时务的小婊子……”
闻言,师杭大怒。一朝飘零入泥,难道人人都能踩她一脚了?听见这种脏污字眼,她根本无心考虑后果,一把抄起手边的烛台就朝帘边丢去。
“滚!”少女厉声呵斥,“想拿我当妓子取乐,他还不配!”
她力道不够,铜制的烛台根本没砸出多远,很快坠在地上发出沉闷声响。外头的人明白她发了火,忍了忍,并不敢擅闯入内,冷哼后便走了。
师杭靠在榻上急促地喘息着,她实在伤心,原来被掳受辱的官宦女远不止她一人。往日一同嬉戏游玩的闺友,不知有几人在此。
未嫁的女子一旦失去家族庇护,真真与浮萍无异。她们于争夺权柄无用,在男人眼中,唯一有价值的便是这幅处子之躯了。城破三日,战局已定,今夜这宴是属于叛军的庆功宴,宴上,女人势必会成为一道助兴佳肴。
师杭不可避免地想到男人先前压在她身上做的难堪事……
所以呢,他此刻在做什幺?再压着别的女子蹂躏一通吗?
真够恶心的。
十五年来,爹娘教她琴棋书画、德容言工,却没人在她面前提过半句男女情事。师杭隐约明白,这是要留到成亲前由母亲教给她的,可她已经失去母亲了,今后恐怕也没人会明媒正娶她了。
一日之内,重重变故几乎要将她击溃。师杭无力地躺了下来,用被褥蒙住头,蜷在里面默声流泪。
她边泣边哀求神佛,如果可以怜悯她,令她一觉睡去再不醒来就好了。躲得过一时躲不过一世,待下回他当真对她做了那桩事,她又该如何自处呢?
更可怕的是,方才男人斥她的话,她丝毫不知该如何反驳。真言难辩,难道她也是踩在百姓的尸骨上才得以安宁、得以活至今日吗?
少女越想越难过,不知昏昏沉沉哭了多久,突然听见帐中有响动。于是她止住哭声一点点探出头,恰见孟开平在旁重燃烛火,也扭头朝她看去。
两人的视线不期然撞在了一处。
男人喝了酒,故而面颊黑中透红,眸光极亮。他的眼神太过锐利灼热,比那烛火还燎人,师杭只匆匆看了一眼便忙不迭避开了。
“派人来叫你,怎的不去?”男人沉声问道。
师杭背对着他不答,只一味缩在角落里。孟开平不耐烦了,大步上前扯她的被子,结果甫一触及竟觉掌中一片濡湿。
“……”
孟开平见她眼圈通红,跟兔子似的,无奈道:“你还真能哭。往后哪处田地旱了便教你去,指定能把庄稼都哭活了。”
他调侃了她一句,可师杭一点儿也不觉得他说的话好笑,狠狠剜他:“衣衫都被你撕破了,你让我怎幺去?”
她自以为言语神态够凶了,可在孟开平看来却和娇嗔差不多。瞧她半张小脸都埋在被子里,只露出一双春水似的杏眸波光流转,无害得真跟小兔似的,孟开平的心顷刻软得一塌糊涂。
她死死拉着被褥不撒手,他干脆将她连人带被拽到怀中,轻笑道:“你莫不是傻,派人来不就是给你使唤的?你让他去取件衣衫来又费得了多少功夫?”
师杭暗道,确实不费功夫,可她根本就不想赴宴伺候他。
“我都将火折子留下来了,你也傻得不知道用,蜡烛燃尽就摸黑呆在这儿?”
孟开平抚着她的长发,觉得自己可能有些醉了,心头竟无端冒出些酸涩柔情来。师杭被他强硬地搂在怀里,长发被他的手指勾缠住,周遭都充斥着陌生男子的气息。那气息严严实实裹住了她,教她浑身难受。
师杭扭过头,死活不肯看他。
这小娘子是块硬骨头,恰巧孟开平最看得起且最爱整治的便是这类对手,于是他故意强掐着她下巴,逼她直视自己。
师杭心里简直快恨死他了。这样的姿势屈辱又难堪,让她看清了男人不甚在意的神情。他在上方,居高临下地享受着她的痛苦与绝望。这是一种难言的征服感,类似于驯养烈马,他要将她牢牢制在身下,想做她的好主子。
目下一片混乱,男人倾身,爽快至极。
孟开平觉得她虽然不会主动,但这张樱桃小口也算极品。几近窒息间,唯有心中求生的本能在支撑着师杭。
她知道男人想要什幺,若她此刻手中有刀,定然毫不犹豫捅进他的胸膛。可惜她手无寸铁,她只能一退再退。
男人轻声谓叹着,不妨咬得狠了,少女不顾一切地挣扎起来,面颊上滴落了冰冷泪水。半晌,男人似乎颇觉不满。但他终于松开了她,无奈道:“也罢,来日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