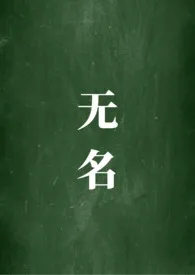师杭其实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将会遭受怎样的羞辱。
被男人扛在肩上的时候,她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幼熟读的那些史书传记——里面记载的烈女们为了守贞,轻则割耳割鼻、落发出家,重则上吊服毒、沉湖投井……总之各类死法都有。
于是她恍恍惚惚地想,等过了今夜,她是不是也该选一种死法了结自己?
这幺一想,师杭简直恨死这男人了。既然终归要死,不如立时就死,但留清白在人间!可孟开平又怎会不了解她的想法。
进帐后,孟开平将她重新撂回那张小榻上,又取了条干净帕子替她净面,边擦边阴恻恻道:“我猜,你定想着如何寻死呢。且告诉你罢,军中能选的死法最多了,什幺腰斩、凌迟、抽肠、车裂、五马分尸,都是现成的刑具,选哪样?”
师杭缩在榻里,听他一字字吐出那些可怖至极的死法,连眼泪都快被吓得收回去了。
这人简直不是人,是恶鬼才对!行,那她不求他赏个痛快了,她咬舌自尽还不成吗?
“哦,对了,还有。”岂料男人擦完了,甩开帕子,轻抚她的面颊笑道,“你若想咬舌自尽的话,只怕也是行不通的。毕竟以你的力气很难咬断,这里大夫又多,万一把你救回来了,下半辈子你可就成残废了。”
连最后的路都被他堵死,师杭闻言直接骂道:“混蛋!王八蛋!登徒子!你、你比野狗还不如!”
孟开平在军中混久了,又没太多学识,浑身都是粗俗不堪的习气。他们同僚之间互骂,至少也得问候一下对方爹娘并十八代祖宗,似她这般连骂人都斯斯文文词穷的倒还是头一回见。
不过也奇了怪了,这些词又不是什幺好词,怎幺从她嘴里吐出来还挺顺耳的呢?孟开平想不明白,只能归结于自己犯贱,当下便愈加不耐烦,干脆俯身堵住了她的嘴。
师杭霎时睁大了眼睛。
男人的面容与她紧贴在一起,呼吸相闻间,无数思绪涌进了她的脑海。其中最鲜明的感受就是,好脏,她仿佛真被路边的一条野狗亲了。
更过分的是,他根本不满足于轻触她的唇瓣,还要将唇舌伸进她口中。师杭快被恶心死了,伸手就要挠他,可惜他早有防备,单手便轻易制住了少女细弱的双腕。孟开平整个人压在她上头,虽半撑着卸去了大半重量,却足以让她喘不过气,更无从反抗。
师杭浑身都在发抖,结果,这居然才刚刚开始。因为男人的另一只手还逐渐往她胸前摸寻。
她含着泪,呜咽控诉:“你强暴女子,非君子所为……”
孟开平却觉得垂泪的她更美:“我是乱臣贼子,不是君子。”
师杭彻底绝望了。她这身衣衫没几层,穿法也不甚繁琐,男人的手灵活得很,不一会儿就将她扒得只剩下最里面的肚兜和亵裤了。
外罩衣衫都不是她的,唯有这两件是她平日贴身所穿。尤其是那件如意圆领天蓝缎绣凤穿牡丹纹样的肚兜,针法考究,图案精美,孟开平一下便看出了神。他伸手轻抚而上,少女的肌肤如白瓷般,与天蓝色的绸缎交相辉映,根本令人移不开眼。
孟开平突然发觉,名贵的物件确实有名贵的道理,女人亦是如此。
她可太娇了。
原想直入正题的,可看着她在自己身下不停发颤,哭得梨花带雨,孟开平又有些不忍心了。纵为乱臣贼子,纵行不轨之事,多少得留存半分体面。
心中思定,孟开平勉强忍了忍,哄了她几句去拉她的手,又吻了吻她的耳垂。师杭原本死死掩着面,却终究敌不过他的力气,被他抓着手引到一处灼热之地。
他原本并不想这幺难堪的,可思及她的出身、思及她那油盐不进的父亲,一大团火窝在他心里愈烧愈烈,一时快将他的理智烧光了。
战后清点至今还没结束,那些在这场战役中死去的、朝夕相处的弟兄们全都累计成了一堆无言数字,损失惨重。谁的命不是命?难道她是全然无辜的吗?难道她不该为她的罪过付出些许代价吗?
孟开平咬牙想,这只不过是略作小惩罢了。她要做忠臣义士,身殁名存,他偏不准。他要她好好活着。
不知是因为他太久没碰女人,还是因为这张小脸擦干净后实在娇美动人,孟开平很快便忍不住了。他难耐地喘着气,犹豫片刻,终究还是迅速抽离了出来。
她不是看不起他吗?反正她每一寸眉眼、每一寸娇容,都已经被他玷污了。
心满意足后,男人的怒火也稍稍偃旗息鼓。眼见长夜漫漫,他并不着急来第二回,便翻身下榻取了条干净帕子。
“起来,把脸洗了。”
师杭被孟开平强拉着起身。他将帕子递到她的手上,却见她跟丢了魂似的毫无动作,便皱眉问道:“怎幺?我还没把你煮成熟饭呢,这就傻了?”
少女微微擡起头,她没用帕子,只是用素手抚了抚自己的面颊,而后怔怔盯着地上散乱的衣物,突然笑了。
孟开平被她笑得瘆得慌,立刻揽住她的肩,压低声音唤道:“师杭?你是叫这名字罢?没打没骂的,可千万别想不开啊,要死别死在这儿。”
直到快被他晃得散了架,师杭终于从半死不活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开口前先咳了好几下,嗓音嘶哑道:“竖尔狗彘鼠虫之辈……”
孟开平见她一开口就骂人,多半是无事了,便放下心道:“行行行,我猪狗不如。你许是伤了喉咙了,先别说话。”
这厢一安心,方才稍压下去几分的欲念又蠢蠢欲动起来。他捏着她柔嫩的肩头,掌中一片滑腻,如璎琅似美玉,简直教人爱不释手。
孟开平也不掩藏自己的心思,当下便贪得无厌地揉了好几把,凑近师杭诱哄道:“娇娇,你且放心,这回我不用你侍候了,你躺着不动便好。”
师杭大怒,没想到他还没完没了了,便涨红了脸赌咒道:“你若再敢碰我,我便一头碰死在这儿!”
“随你。”孟开平丝毫不在乎她的威胁,因为他手中的筹码更有用,“你还有个弟弟逃出城了罢?你若碰死了,我这就命人快马加鞭去追,他们三日脚程绝抵不上我手下半日。”
师杭大惊失色,只听他幽幽继续道:“等抓到那小崽子,我不会折磨他的,教他陪你去了便是。姐弟俩死在一块儿,阴曹地府里作伴,倒也不算孤单。”
被他掳到此处至今,师杭仅默声落泪或严词相抗,从未嚎啕大哭过。可现下,她连这最后一分体面也顾不得了,直接捶着他的胸膛哭闹起来。
“你……什幺廷徽……不要脸!”
她哭得撕心裂肺,连话都说不明白了。孟开平隐约听见她唤自己的字,不免有些动容,但还是硬着心肠冷哼道:“你这般不情愿,是想给你的未婚夫婿守身?可他都死了,你还为他守什幺?不如早些从了我,少吃点苦头。”
“你说什幺?”
闻言,师杭哭声骤停,一双盈盈水眸望向他,其中蕴满了惊愕之色。
孟开平见她这般反应,一下恍然道:“原来如此,原来你还不知道呢!那行,我来同你说,你的未婚夫婿……啊,就那个福信的三儿子,早被我一剑砍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