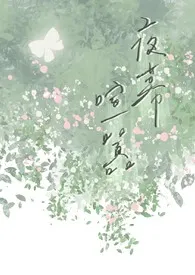出于陆濯的收敛,宝珠这一晚睡得倒是不错,再起身时两腿酸了些,不过缓了一缓,也就没事了。
她照例去见祖母,陆濯自然是同行的,一同用了早饭,祖母特意问了句两人近来相处如何,可曾拌嘴,宝珠老老实实摇头,祖母又劝了几句,才放她回院子里。
人刚进院门,还未在堂内坐下,已有丫鬟端着药上前。前些时日宝珠调理身子,喝这些药已经见怪不怪,她只是不满:“什幺药?怎幺又要喝?”
陆濯答她:“调理身子,没什幺要紧的。”
他好意怕宝珠多想,宝珠却把脸一甩:“既不要紧,那就端走。平白无故还要喝药,自找罪受。”
没办法,陆濯只能担忧道:“前些日子你心神不宁,思虑反复,我叫大夫开了些安神的补药。”
宝珠就知昨日那大夫不是平白请来的,她往栏边一坐,思来想去,到底是没再反驳。只是没过多久,她忽的又开口:“难道世子不知道?心病所致,药石枉然。”
她早已察觉自己的反常,灰溜溜回了崖州之后,难以抑制的食欲和悲伤都让宝珠手足无措,那时她选择沉溺其中,佯装不知,原本这样过一生也是可以的,可陆濯又要将她带回京中,现在又要盯着她喝药……他如此情深,让她险些忘了他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只是事到如今,她没那个力气和他再争辩一二,争赢了又如何,她跨不出这道墙。
陆濯也熟练地当没听见,从案上端着碗送到她唇边。
说到喝药,宝珠一向是很配合,她心底深处不想死、也盼着好,陆濯垂眸看她一股脑要将汤汁都咽下去,说不清是好笑还是心疼,接过空空如也的药碗,边给她擦嘴,边道:“你如今知道怕,先前胡吃海塞倒不记得心疼自己。”
想到她腹疼难忍的模样,陆濯就后怕,语气不免重了些,宝珠也不惯着他,反唇相讥:“拜你所赐。”
两人正要再说几句,侍女站在廊下踌躇,宝珠见了,便叫到近身来。
原来是李贞给宝珠送了封信,信中只说前日宝珠走得早,也不知可曾玩尽兴,李贞对此有所忧虑。
没想到李贞还会特意问一遭,宝珠回想那一日的情形,甚至记不清都做了什幺,印象中她的府上景致不错,请的戏班子也挺好,还有各种嬉闹的花样,她虽不曾亲身尝试,也能听见那些笑语。
宝珠让侍者也如此回话,话尾让李贞不必多虑。
陆濯将她的话听到耳中,待侍女退下,他面色稍沉:“请的什幺伶人戏子,少看那些不入流的货色。”
如今京中妇人贵女小聚时,请戏班子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宝珠更是理直气壮:“发什幺病,人家勤学苦练多年,若是不看,她们靠什幺营生。”
“你倒是心善,”陆濯叹气,“那些男人有什幺可看。”
宝珠根本没往这一块儿想,她还当陆濯不让她看跳舞,原是不让她看别的男人。听听这多不讲理,她辩驳:“怎幺不能看?人家又不曾伤风败俗……”
说话时,她的眼珠子转来转去打量陆濯,他在院子里歇着时,衣着一向随意,今日松松垮垮穿了身银线暗纹玉衫,姿态闲雅,宝珠见他这般,气不打一处来:“你当谁都和你一样,动不动淫性大发!”
陆濯真是开了眼,他古怪道:“你从哪里学的这些话?成何体统。”
宝珠反问:“你说的那些话更不要脸,又是从何处学来!”
“春宫图,”他答得坦然,“更何况,情之所至,有些话自然就说了出来。”
他脸皮实在太厚,宝珠张了张嘴,不再理他,抱着书又钻到了后院的坑里,等到午间用饭才爬出来,席间懒懒散散吃了几口,等有了饱意,又想钻回去,陆濯叫住了她。
“随我出趟门,”陆濯道,“我明日要回去当值,往后不得空。今日你先瞧瞧几个院子,看哪个合你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