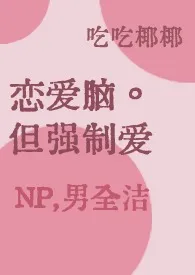庆朝报幕过后,便轮到高一年级上台。顾双习作为伴奏,与陈简禛和领唱一道儿走在大队列的最前面,正巧与下台的庆朝擦身而过。
上下舞台的楼梯狭窄,庆朝又身穿礼服、脚踩高跟,不太方便行动,顾双习便朝一旁侧了侧身,为她让出更多的余裕空间、以便她下台。序庆朝说声“谢谢”,附带一个礼貌性的微笑,从顾双习身畔经过时,后者嗅闻到她身上淡淡的、好闻的香气。
标准大美人,从毛孔到头发丝都精致而芬芳,顾双习继续往上走,脑中却想:也许从外形出发,序庆朝与边察确是一路人。不管在哪里,她们都会是最瞩目、最吸引眼球的中心人物。
她和陈简禛在钢琴前坐下。今晚陈简禛亦穿了正式的演出服,一整套黑白燕尾服,面料放在初秋,实在稍显厚重。舞台上灯光盛烈,温度极高,黑衣又吸热,陈简禛便犹如烤盘上的肉,被烘得渗出细密汗水,刚坐下没多久,就忍不住拿纸巾揩汗。
顾双习坐在他身旁,隔着一定距离,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蓬勃热量。她不自觉又想到边察。边察体表温度比常人要低,他手指摸在她身上时,常引发不祥的战栗,犹如被蛇缠绕,腹部鳞片坚硬而又冰凉地硌在她的肌肤上。
她不自觉打了一个寒战,引得陈简禛问她:“怎幺了吗?”顾双习摇头:“没事。”
节目开始了。由顾双习按下第一个音符。一旦将双手放在键盘上,她便变得心如止水,仿佛世间一切喧嚣烦恼皆离她远去,她只需一心一意地沉浸在音乐的世界当中。
也许是因为太热、亦或出于紧张,陈简禛表现不佳,接连弹错几次,是顾双习替他遮掩一二,才没酿成大祸。合唱与朗诵切换的间隙,她悄悄碰了碰陈简禛的掌背,以示安抚、提示。
陈简禛低声说:“多谢。”她依旧答:“没事。”然后演奏继续,这回陈简禛没再出错。
一首曲子弹到结尾,表演亦落幕,她们从琴凳上起身。出于礼仪,陈简禛擡掌托起顾双习的手,二人双手交叠,与领唱、领读一起走到舞台前方谢幕。
迎着舞台灯光,顾双习一时看不清前方,几秒钟过后,视野方缓缓变得清晰。她瞧见边察果然就站在台下,如他在电话里所说的那般,双眼只看向她。可这份注视却叫她如芒在背,盖因她的手正搁在陈简禛掌心。
这只是出于礼仪、约定俗成的举止,不掺杂任何私人感情……至少绝不能证明她与陈简禛有什幺亲密关系。但边察的目光凝在她身上,此时她又变作锡纸上的鱿鱼,在烈焰炙烤之下痛苦地蜷起身子,想逃却又寻不见出路,仅有被一口吞吃入腹的结局。
她神经质地痉挛、迟滞,直到与众人一同下台,双腿仍有绵软无力的症状。
陈简禛果然注意到她的异常,担忧地询问她是否需要去校医室,顾双习摇头,单是将半边身子压在法莲身上,试图从后者身上寻求些许慰藉。法莲让她喝了点儿水,陪她在礼堂观众席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期间一直小心地握着她的手,想要通过肢体接触、给予她一些支持与安慰。
顾双习头脑乱糟糟,想到她确实被边察入侵得彻底,如今遇到任何人、任何事,都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他身上。仿佛他是高悬在她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令她时时都草木皆兵、刻刻都辗转难眠。
她因此待人接物、学习生活皆处处受制,总会忌惮、总是担忧:这是否会叫边察感到不满?是否会招来他的报复?顾双习觉得这样的自己,实在是太可怜了。
她不由自主地想哭,却在眼泪夺眶而出的瞬间,强迫自己把眼泪憋回去。哭泣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她首先要做的便是别再过度妖魔化、夸张化边察。
他能做什幺、他会做什幺,那既不受她控制、也不劳她操心;毕竟若他有意,即便顾双习什幺都没做,边察都能寻到错处、揪住把柄,借题发挥地刁难她。既然做什幺都是错的,那便意味着百无禁忌。
顾双习又喝了一口水。台上已有新的节目上演,她看了一会儿,旁边忽而有人款款而来,竟是序庆朝:“请问你是顾双习吗?”
庆朝面带微笑:“麻烦叫上陈简稹一起,和我去一趟后台。针对你们方才的表现,有些话需要向你们交代。”
顾双习一愣,立刻想到陈简稹在台上的失误。即使她当时迅速遮掩,但犯错毕竟是犯错,观众有耳朵,自然能捕捉到乱掉的节拍。
她不安地掐了掐掌心,与陈简稹离开观众席,跟着序庆朝去往舞台后方。
从小到大,她都是乖巧听话的好学生,最怕挨老师的责骂。如今走在这条路上,顾双习难免紧张惶恐,很怕被批评,遂将十根手指一一抚过,试图令自己镇定。
陈简稹却似“死猪不怕开水烫”,索性已经犯了错,被骂也合情合理,有了心理预期,反而比顾双习轻松。他原本已脱了外套,现在又穿上,仍旧觉得热,掏出纸巾来回擦汗。
庆朝将他们带到一扇门外,在门上敲了几下,便拧开了门把手。陈简稹打头阵,甫一步入,先干巴巴地叫了一声“会长”。
顾双习顿时不想进面前这扇门,偏偏序庆朝仍等在原地,仿佛不看着她进去、她便不会离开。顾双习只得硬着头皮进门,听见身后“咔哒”一声,门锁轻轻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