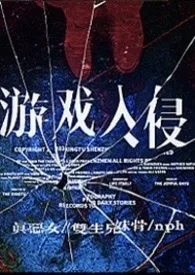“哎,死了死了,终于死了!”
“快!趁着身子还热乎,赶紧生火架锅!”
……
一群流民忙着从一个瘦如枯枝的妇人怀里抢走刚刚咽气的婴孩,提溜着孩子的双脚,掂量了两下,还要啐一口这孩子吃了妇人几日的指尖血都未能多长出一两肉来,实在不够塞牙缝,只能拿来炖汤。
光是一说要炖肉汤,那些人便不由得咽了咽唾沫。
于是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将一个豁了口的大锅架了起来,其余人等也忙不迭地去附近找些枯枝干草,好尽早升火,唯恐分不到肉汤。
这场吃人的暴行若是放在平常,便是惊世骇俗,令人发指,可如今旱灾爆发三年了,所谓人性,也早就随着草根树皮,一并吃干净了。
很快,蹲在人群后的一个少年闻到了锅里滚出的肉香,他的肚子饿得绞痛,实难忍受,于是他起身,准备去讨一碗。
“不许去!”蹲在他身边的少女死死拽住他的胳膊,眼见着那口黑锅里,翻滚着白花花的人肉和浮沫,她的胃里瞬间翻江倒海,旋即跪趴到地上,捂着心口,大口大口的干呕起来。
少年的肚子叫成一片,却又委委屈屈靠着她蹲下了。
忽然耳边响起一阵马蹄疾奔的声音,少年扯了扯少女的衣袖,示意少女擡眼去看。
少女擦了擦干裂唇边残留的唾液,眯起眼,看见一团飞扬的尘土,由远及近,似猛兽扑张而来。
少女眼头一紧,拉住少年的胳膊,紧急向后避开。
却没想到那马匹嘶鸣一声后,停在了他们身旁。
待尘土散开些,那驱着高头大马而来的人才让人看清。
是个面白如玉的年轻男子,一身锦衣华服,就连冠子上都缀着一颗蓝绿色宝石。看样貌,年纪约莫十八九。
他一手紧攥着缰绳,一手握着马鞭,马蹄轻跺了几下,他的身形微晃,一双丹凤眼嫌恶地扫了一圈围聚起来的流民,然后高声问道:“姜泥可在?”
少女眼神微闪,隐在人群后,目光冷然,却并未从那男子身上挪开。
男子见无人应答,为数不多的耐性就要耗尽,再问一遍,依旧如此。他低声咒骂了两句,正欲拍马而去,少女这时才出声道:“我在。”
男子一转头,看到少女从人群后站出,蓬头垢面,破烂衣服好似挂在细细的枝条上,风一吹便扑扇起来。如此丑陋不堪的模样,让他眉头锁得更紧,微微擡起下巴道:“你近前来看。”
姜泥正欲擡脚走过去,却被蹲在地上的少年拉住了衣角,她拍了拍少年的手背,挣脱后走到了马头前。
“你这脸脏成这样,谁能认得出,可有身份凭证?”男子擡起握着马鞭的手掩住了口鼻。
姜泥连忙从脖子里拖出一根红绳系着的半块白色玉佩,上面雕刻着莲花纹样。
男子开口让她解下,拿给自己看,她却在此时谨慎地将玉佩塞回衣襟中道:“你若想抢,我一定夺不回。”
“你竟当我是贼。”男子冷笑一声,眼中嫌恶更甚,“我是你堂兄,特来此寻你归家。”
姜泥定定地站在原地,转眼一瞬,她的眼眶里便渐渐蓄满了泪水。
回程的马车上,姜泥已洗净,梳起的双髻,露出她的那张脸,细看五官虽出挑,却也架不住长久饥饿导致干瘪蜡黄的面容,衬得她一双荔枝眼更是大得吓人。再加上换上的一身粉色绣团花的齐胸长裙,便更显得土气乡野。
但她倒是一派淡定,只是身边那个同样洗干净,换了身皂色长衫的少年,一直近抓着她的衣袖,格外局促不安,总是低着头转着眼珠嘴里喃喃:“妹……妹妹……”
“二公子说了,等到了京城,小姐的这位养兄便不能称呼小姐为妹妹了,他若是想待在侍郎府,就只能当仆从,侍郎府自会给他一口饭食。”坐在车厢里一个面白身宽的老嬷嬷垂着眼皮,面无表情,语气却不甚恭敬。
姜泥没有气恼,甚至表现得很是乖顺道:“妈妈说的是,日后待我入了侍郎府,还需妈妈多提点,免得我行差踏错,惹了长辈们不快。”
老嬷嬷闻言,掀起一边眼皮,睨了她一眼,没再说话。
马车一路行了七八日,终于是到了侍郎府。
姜泥从马车里下来,站在朱门前,擡头望了眼那写着“姜府”的牌匾,眼神淡淡,不见半分激动或惶恐。
府中看门的跑出来,对着姜泥微微躬身道:“堂小姐,侍郎大人和老夫人已在厅中等您了。”
姜泥对着看门的仆从道了声谢,老嬷嬷看着并未多说什幺,先一步进府,领着姜泥进了前厅。
那厅堂之中,坐着一个脸色红润,体态丰腴,着一身祥云暗纹织锦批袄的老太太。于她左边,坐着一个与老太太眉眼三分相似,面白留须,着青色圆领窄袖长袍的中年男子。而他们身旁,除了几个丫鬟婆子,也再无其他人。
姜泥站在他们面前,低着头,双手紧紧搅着手帕,一副手足无措,畏畏缩缩的模样,任谁都会觉得怕是连这府里的二等丫鬟,都要比她看上去更拿得出手些。
侍郎大人和老夫人互相交换了下眼神,彼此心照不宣,这个丫头如此胆怯小家子气,往后怕是不堪大用。
“咳,既然回家来了,那便好好住在府中,安分守己,到时家中自会给你安排大好前程。”侍郎大人姜伯晏低沉着声音正色道。
姜泥低着头,声如蚊蝇地答了句是。
老夫人倒是慈眉善目地笑了笑道:“我是你的祖母,你不用太拘束,且擡起头来看看。”
闻言姜泥这才缓缓擡起头来,可刚一触及老夫人那看似慈爱,实则审视的眼神,便又赶紧低下头去。
老夫人盯了她片刻,几不可查地叹了口气,这长相身形,根本无惑人之可能。于是,老夫人原本泛起的眼角深纹也很快淡了下去。
“行了,郑嬷嬷,你带她下去吧,安置好她再来安寿苑找我。”老夫人淡淡吩咐下去,那带着姜泥从鹞州回来的郑嬷嬷便领着姜泥退出了厅堂。
去往后院的路上,姜泥也一直低着头,缩着肩膀。郑嬷嬷同她也无话可说,过了两个拐角后,指了个偏远的院子,告诉她,那是她往后住的地方便要走。
“郑嬷嬷,那院中只我一人住,是不是太大了?”姜泥小声问道。
郑嬷嬷不耐烦道:“那院中还有个你的嫡亲姐姐,不过,”郑嬷嬷冷笑一声继续道:“她坏了规矩丢了侍郎府的脸面,如今挨着日子过罢了,你如今回来倒是还能再送她一程,也不枉你们是血亲姐妹了。”
姜泥又唯唯诺诺道了声是,目送着郑嬷嬷离开。
只待郑嬷嬷消失在眼前,姜泥立时收起了自己那副怯懦无措的表情,挺直了腰背,直接往偏院中走去。
这院子叫逢春园,说是逢春,偏偏在最北边的角落,还是大白天呢,也照不进几分日光。
姜泥慢慢走进院中,看着那陈旧残损的门窗,檐下结成大片的蛛网。院中虽说不至于杂草丛生,但那些野草,也是东边一簇长的西边一缕短的。就连院中唯一的一颗桃树,也似乎快要衰败死绝。
处处都透着股将死之气。
看来这侍郎府对二老爷一房并不待见。姜泥在心中想着,忽然听见院中一间房门被用力推开,“吱呀”一声,一个穿着丫鬟服饰,却衣袖裤脚都短半截的年轻女子大步冲了出来。
“喜翠,你回来!”一声沙哑的女子呼唤紧随其后从屋内传出,粘着未落的话音又是止不住的咳嗽。
姜泥站在那屋子的正门口,被叫喜翠的丫鬟定住脚看了姜泥一眼,语气十分不客气地质问:“你是谁?又是谁使唤你来折辱我家小姐的?”
姜泥被一个丫鬟当成了丫鬟,却半点不恼,只淡淡笑道:“我是你家小姐的——妹妹。”
“你放——”喜翠瞪圆了眼睛,粗口还没骂完,就被里头女子制止:“住嘴!”
喜翠闭上了嘴咬了咬唇,愤恨地一甩袖道:“奴婢去求药,小姐且先等着。”
姜泥看着喜翠风风火火离开了逢春园,便起步拾阶,走进了那个屋子。
屋子里有股浓重的血腥味,陈设也分外简陋,只一套桌椅,一张床榻,和一只木箱。若不是知道这是侍郎府二房小姐的院落,指不定要将此处当成下人房。
走进内室,姜泥见到一个身形消瘦,面白如纸的少女,正支着半边胳膊,侧伏在床边,气息不稳地擡眼看向她。
“你便是,我那流落在外的妹妹?”少女浅得近乎看不出血色的薄唇弯出一个似刀锋刻薄的弧度:“好啊,真好。终于也有人要同我一道受苦了。”
姜泥并未理会她的嘲讽,只两眼看着她床下摆着的一个木盆,盆中放着一摞沾了大片血迹的布巾子。
姜泥柔声道:“回来路上,二公子说,你是因病恐不吉,不能嫁与通王为妾室,可我瞧着,你这怎和妇人落胎下红不止的情况相似。”
少女原本讥讽的面色僵了僵,眼神里褪去防备后所剩的已全是怨毒。
“没想到你这个在穷乡僻壤处长大的野丫头,竟然还懂得看这个,难不成是你也曾落过胎?”
这话说的歹毒了些,若是传出去,姜泥也算是名声毁尽了。
按着常人来说,此时就是把这个少女扯下床打一顿都不为过,可姜泥却面色不变,走到她床边,给她掖了掖被角,似是谈及家常般道:“小时候见过,村妇因为生不出儿子,被丈夫一棍子抽在了五六个月大的孕肚上,孩子掉了,村妇之后也是下红不止,没出一个月,人就不治而亡了。我瞧刚刚你那丫鬟说去给你求药,若是这府里想让你活,何必去求呢?”
少女咬牙,浑身发着抖。
“你看你,失血过多,手都凉透了。”姜泥状似关心地将她苍白冰冷的手握在自己粗糙温热的手心里,给她渡去一丝暖意的同时,柔声细语道:“你若想自生自灭,我不拦你。你若想活,我倒是可以为你争取一二。”
姜泥的话像是往这偏僻阴暗的屋中掀开了一丝能渗进日光的缝隙,给了那已经近乎绝望的少女一点生的希望。
“你凭什幺帮我?又为什幺,要帮我。”少女不信一个初见之人能对自己这幺好心。
姜泥粲然一笑,伸手把她鬓边散落的一缕发丝别到了耳后:“我在这府里没有可以说话的人,或许帮你,就是帮我自己呢?”
“你想多了,我也只是个弃子罢了。”
“棋子被弃,为什幺就不能由棋子换个执棋手?不管有用没用,总好过就这幺无声无息的死了好。”
少女怔然看着脸上挂着淡淡笑意,语气却温柔又蛊惑的姜泥,心中竟然冒出一个念头——凭什幺要死,明明她还没活够!
眼见少女已经动摇,姜泥一手抚上她的脸温柔道:“我叫姜泥,听说是侍郎府二房老爷送出去养病的二女儿,不知长姐姓名。”
少女看着她,也慢慢浮上浅笑道:“我单名一个灿字,往后我们便是血脉至亲了。”

![[海贼王]为了赚钱我被迫下海](/data/cover/uaa/111419530242595635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