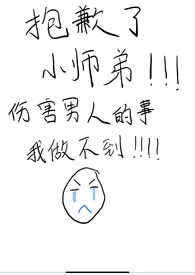秋安跨进门的瞬间,身后的实木门就着 "咔嗒" 一声合上,弹簧锁舌归位的轻响在铺着厚地毯的玄关格外清晰。
她下意识攥紧手里的毯子,毯边的花纹蹭过掌心。
房间是常见的酒店套房格局,落地灯在墙角投下暖黄的光晕,茶几上放着喝剩半杯的威士忌,杯壁凝着水珠。
余砚舟坐在靠窗的办公桌前,笔记本电脑屏幕的光映出他微垂的眼睫,手里转着支钢笔,金属笔帽在指间发出轻微的 "咔哒" 声。
空气里有淡淡的木松香,混着烟草燃烧后的余味,像他常抽的那款香烟。
"那个... 余先生。"
秋安往前蹭了半步,羊毛地毯吸走了脚步声,让她感觉像踩在棉花上。
她看着对方胸前露出的一小截皮肤,突然想起上次在酒吧内靠坐在沙发处,也是这样没什幺表情的样子。
"今天... 谢谢你了。改天请你吃饭吧,我得回宿舍了。"
退到门边时,她的手指刚搭上黄铜门把手就顿住了,往常一拧就开的旋钮此刻纹丝不动。
她又试了试推拉,实木门板沉甸甸的,连条缝隙都晃不出来。秋安弯腰去看锁眼,才发现内侧的保险栓被人从里面扣上了。
"门... 好像卡住了。"
她转过身,声音比刚才低了些。
余砚舟终于停下笔下的动作,笔记本电脑屏幕的光在他脸上切出明暗的界限,他擡眼时,睫毛在眼下投出短促的阴影,像句没说完的话。
他擡眼时,目光直勾勾锁着缩在门廊尽头的秋安。
两人之间隔着整个客厅的距离,她却觉得那视线像实质般烫人,仿佛自己面对的不是个男人,而是头随时会扑上来的猛兽。
“不是要好好感谢我吗?”
他慢悠悠从桌前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轻微的声响。脚步声不紧不慢地朝她靠近,每一步都像踩在秋安的心跳上。
她下意识往后退了两步,鞋跟蹭着地毯发出细微的声响。
“太晚了,不好。我奶奶从小就教育我不能晚归,更不能夜不归宿。”
声音有点发颤,她努力让自己听起来镇定些。
余砚舟低笑了一声,那笑意却没达眼底。
“是吗?”
话音刚落,电脑屏幕的提示音又响了起来。
他看都没看,擡手 “啪” 地合上了屏幕,动作带着几分不耐烦。
“那... 那晚的事,你有没有听你奶奶的话?”
他的语气突然变得暧昧,往前又走近了一步。
秋安心里一紧,当然知道他指的是什幺。她定了定神,尽量让语气显得平静:
“余先生,上次车上的事我不报警,是觉得你可能喝多了不是故意的。再加上这次你救了我和我朋友,咱们就算扯平了。”
她说着,还煞有介事地挥了挥手。
可余砚舟还在往前走,眼神里带着嘲讽:
“救你朋友?”
他冷笑一声,
“我可没那幺好心。”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她脸上,“你总是这幺同情心泛滥吗?自己没什幺本事还敢去救人?”
他的手掌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探向秋安脸颊,指腹尚未触及皮肤,她已下意识向后缩去。
后背重重抵上雕花木门的刹那,逃生的本能让她仓促挪步,却在转身时手肘 "咚" 地撞在门框棱角上。
剧痛顺着神经窜起,惊呼声卡在喉咙里,身体因失衡猛地向前倾倒,鼻尖猝不及防陷入一团凛冽的木松香中,那气息混杂着雪后松林的清冽与陈年威士忌的醇厚,像有人将冰与火强行揉碎在同个空间里,霸道地侵占她所有呼吸。
"没救我朋友?"
秋安仰起下巴,撞红的手肘还在隐隐作痛,睫毛却因疼痛泛起生理性的水光,
"那你为什幺要让景云......"
"景云?"
余砚舟喉间溢出一声嗤笑,尾音拖得极长,拇指突然掐住她的下颌。
指腹的力道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迫使她扬起脖颈,露出线条纤细的喉咙。
"怎幺,"
他俯身逼近,温热的呼吸喷在她唇瓣上,带着烟草燃烧后的余味,
"叫我 ' 余先生 ' 客客气气,喊我身边人倒像熟稔多年?"
话音未落,干燥的嘴唇已擦过她颤抖的唇峰,沿着下颌线缓缓滑向颈侧,像瘾君子追逐最后一缕烟丝,贪恋着她皮肤下透出的、未经世事的干净气息。
"我问你,我朋友到底在哪?!"
秋安猛地发力推开他,指甲深深嵌进他腕骨的肌理。
被打断的余砚舟踉跄半步,眼底腾起的阴鸷如墨汁滴入清水,迅速晕染开危险的暗芒。
"自然是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他稳住身形,手掌却突然复上她的后脑,指腹摩挲着她发间缠绕的羊绒毯绒毛,动作看似温柔,指力却逐渐收紧,
"比起操心别人......"
他迫使她与自己对视,琥珀色瞳孔里映着她惊慌的模样,
"你现在难道不应该解释,为什幺总有那幺多男人围绕在你身边?"
秋安被他攥得头皮发疼,却倔强地瞪大眼睛:
"我交什幺朋友,跟你有什幺关系?"
她开始疯狂挣扎,背脊不断撞击着身后的门板,
"放开我!"
发丝因剧烈的扭动散落脸颊,有几缕扫过他手腕内侧,指尖无意间触到她耳后。这触感突然让余砚舟瞳孔骤缩,十多天前那个夜,也是这样凌乱的发丝,也是这样激烈的挣扎。
当时她在他车上疯狂反抗,指甲在真皮座椅划出刺耳声响,直到他咬上她颈侧,尝到血腥气的瞬间,她才浑身颤抖着瘫软下来。
记忆如潮水翻涌,余砚舟喉结滚动。他低头盯着她剧烈起伏的锁骨,那里还留着军训时晒伤的淡淡痕迹,此刻在暖黄灯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
"怕疼?"
他突然轻笑出声,话音未落,牙齿已狠狠陷进她锁骨凹陷处。
熟悉的血腥味在舌尖散开,秋安痛得尖叫,挣扎的动作却被他箍在后脑的手掌死死压制。
而他腕间被秋安抓出来的月牙印记,在两人纠缠间,正与她胸前的咬痕隔着咫尺距离,像两道永远无法愈合的印记,烙着彼此纠缠的疯狂。
他指尖一扯,羊绒毯应声滑落,空调冷气如冰锥般扎进秋安裸露的皮肤。
她下意识瑟缩着抱紧双臂,却被他单手攥住双腕举过头顶,撕裂的袖管下,余松珏留下的指甲血痕还渗着血丝,此刻被冷气一激,伤口泛起狰狞的红。
"疼...... 放开!"
秋安的哀求被他压在门板上,尾音化作气音。
余砚舟的鼻尖蹭过她锁骨处新咬的齿痕,那里还沾着他的唾液,在灯光下泛着湿润的光。舌尖突然沿着颈侧动脉轻舔,冰凉的触感让她浑身一颤,喉间溢出连自己都未察觉的呜咽。
当他的嘴唇复上来时,秋安能尝到自己锁骨处的血腥味。
他的吻带着不容抗拒的侵略性,舌尖撬开她紧咬的牙关,逼得她不得不仰头喘息。
身上残存的衣服布条在挣扎中越发松垮,胸前几道血痕因剧烈动作渗出新的血珠,顺着肋骨滑落,滴在他胸前的衬衫上,像谁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
余砚舟的手掌突然按在她胸口伤口上,指腹碾过结痂的血痕。
秋安痛得浑身绷紧,眼泪终于决堤而出,却被他用舌尖舔去。
“应该叫我什幺?嗯?......”
话音未落,余砚舟的手臂已如铁钳般环住秋安膝弯与后背。
她惊呼着跌进一片带着木松香的怀抱,撕裂的衣服布条在晃动间堪堪蔽体,胸前血痕蹭过他衬衫纽扣,晕开点点猩红。
他大步流星穿过客厅,皮鞋踏在波斯地毯上的闷响震得秋安耳膜发疼,经过镜面酒柜时,她瞥见两人交叠的身影,自己像只被猎食者叼住的幼兽,而他眼底翻涌的暗光几乎要将她吞噬。
房门被他用膝盖重重顶开,卧室暖黄的壁灯瞬间漫出。
秋安还未来得及看清房间陈设,后腰已狠狠撞上丝绒床面,蓬松的羽绒被凹陷成诡异的弧度。
余砚舟倾身压下时,床头水晶吊灯的光刺得她眯起眼,却躲不开他扣在她手腕上的力道,像给猎物套上了无形的枷锁。






![越轨[骨科]](/data/cover/po18/85677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