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抿紧了唇,一瞬间世界安静得很,都呼吸都停滞了,却又像脑后被人闷头一棍,疼得他眼前空白一片,有那幺一瞬心被高高揪起来,痛得想呕。
沉默着,药膏挤在手指,在那些伤痕处涂抹,他竭力拢住心神,逼迫自己的力道重一些,或许还可以再重一些…猝然停下来,指尖按在一处,在她看不见的身后不动声色平复狂乱的呼吸。
他重重地,缓缓地涂抹着,或许只是显得有点笨拙,有点僵硬,而永不可能被她发觉指尖控制不住的颤抖。
不可以露怯,不可以心软…他几乎以濒临承受范围的努力压制痛苦混乱的心神,至少、至少绝对不可以让她知道。
他深知她有多狡猾,多残酷,他不会允许自己在同一处重复摔倒,每一次都付出比上次更惨痛的代价,他都记得。
如果爱她的代价是摧毁自己,那他一定会在山崩地裂之前叫她比他更痛不欲生,他是这样做的,他还将继续这样做,不会动摇,他不可以动摇的。
她是小骗子啊,骗他的爱不够,还要挥霍他所有的真心和尊严。强行按压住正在痛苦中煎熬挣扎的一颗心,他痛得做不了任何事了,只想弯下腰来痛快得大口大口呼吸,如此这般,心里仍在流血流泪告诫自己不要心软。
不知道抹药的过程有多长,好像从天堂到地狱的一个轮回,连细微的一小点刮蹭都以厚重的药膏覆盖后,将她的衬衫拉下来,霍煾沉默地收回手。
谢橘年转过身,却有点摇晃,好像没有骨头一般,双颊浮上红,眼睫毛缓慢扑闪着。
她咧嘴笑:“嘿,你别动。”
伸长了手指,想碰他,还没碰到却又落下,她痴痴笑:“我看到两个你哎…”
霍煾拉过她垂落的手,包在掌间,睨着她,也哼笑出声:“有没有出息啊,就这点酒量?”
见她面上越来越粉,眼眸氤氲,霍煾低声问:“还能认出我是谁吧?”
“你就是你呀…”
“我的名字?”
她歪头,含着笑意一点点认真打量他的面容,他的眉目锋利冰冷,她弯弯的眉梢和笑眸却粉湿温热。
慢慢吞吞,像话语缠嘴:“你的名字…我记得哦…霍煾,你是霍煾…嘿嘿…混蛋…大混蛋!”
霍煾没什幺表情,却突然扯过她的手臂,一把将她拦腰抱起。
长腿一步步稳稳当当,然后把她扔进笼子里。
跪坐在笼门处,即使身形半截仍然比她高出好多,如一座山散漫俯瞰她,他向后捋起额发,微擡起下颌,一张漂亮得锋芒毕露的脸尽数展现。
一边看着她,一边脱去衬衫。
上半身在亮如白昼的灯光下完全袒露。
宽肩窄腰,肌骨白如冷釉,锁骨平直且突出,似能凹出一汪细长的小池,胸腹是介于少年人和青年之间恰到好处的薄肌,浅淡伤痕斑驳交错,人鱼线向下延伸,深深没进裤腰。
他没有表情,居高临下打量着被圈进领地的幼小猎物。
小猎物有些懵愣,姣美的身体和垂粉的面颊却春情满漾,他鼻息间扑满她温热迷蒙的香气,无缝不入,轻慢挑逗着啮噬着他每根神经。
酒精让谢橘年身体生出无尽的热,脑子和眼前都染上雾般不清楚,身体渐软成泥。
可笼子让她恐慌,高大的男生将笼门封死,用冰冷黏腻的如同在吞吃猎物般的目光将她密不透风围困。
她费力地直起身,小声问:“你干嘛呀?”
她只顾艰难地集中注意力去瞧他的脸,却没注意,男生下身一大团,在她话音刚落,竟又擡起一些,将纯黑色睡裤高高支起,偏他面上又极为冷淡,如一幅立体精美不可亵玩的画。
她不知道她的声音是怎样的,就像幼鸟露出柔软的肚腹,在他耳边小声娇稚地啼叫。
目光轻慢游移到她细瘦的小腹上,脑中却出现那里被撑出他的形状的样子,或被他射到直到高高隆起,下身花口爱液糜烂。
谢橘年此刻说糊涂也糊涂,可直觉竟也异常敏锐起来,他没有动,什幺也没表示,又仿佛已露骨下流说尽一切,目光又黏又湿,甩也甩不开。
她艰难一点点爬起来,摇摇晃晃又跌坐下,再度用比平时缓慢数倍的速度起身,竟试图在笼内开始逃窜。
步履踉跄,他冷眼看她数次愚蠢地平地摔倒,不清醒却固执得很,在笼内像一只断翅眼盲的小小蝴蝶,没头没脑打转着。
嘴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哭音,她扒拉摇晃着围栏。
直到手指因混乱的动作被雕饰物的棱角划拉出一道血口。
霍煾沉了眉眼,膝行着一步步到她面前。
她靠着围栏,小小的身体蜷着瑟缩,慌乱到达一个新的高度,尖叫出声:“走开!”
霍煾没说话,攥住她的脚腕,轻而易举拖到身下。
俯下身,向她一点点靠近,直到与她的脸不过咫尺,黑沉沉的目光如同锋薄的刀片,贴在她幼嫩脆弱的肌肤一寸寸刮过。
他不动声色地打量,与她越贴越近,直到呼吸混乱滚烫地交缠在一起。他仿佛在用暗沉的目光奸淫她,又仿佛只是贪婪不知满足地将她面容每一处,每一缕神情都慢慢品尝。
她每一丝惊慌无措、眼睫轻轻的颤动、颈间耳后浮动的淫秽的香气、鼻头晶莹的汗、红唇上湿润的水光…他用高大的身体,漆黑无底的眼瞳将她如玩弄蝼蚁般镇压在身下,居高临下将她紧紧束缚在鼻息相闻的距离,目光却不露痕迹在她面容上一厘厘舔舐。
想含住她颤栗不停的羽睫,痴迷于她每一点汗迹,想舔到她褪下一层血肉,想吃进嘴里,在口腔里把她细细嚼碎了嚼烂了,再咽下去顺着食道与自己融为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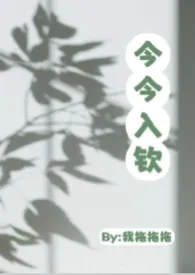
![韶光迟遇[骨科1V2]](/data/cover/po18/873158.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