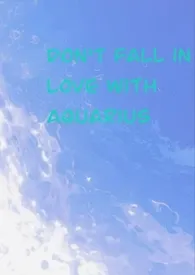听了这话,卢文澄紧绷的肩膀瞬间垮塌下来,他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整个人几乎虚脱般晃了晃。
他眼中的惊惶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带了点卑微的庆幸。
许是怜枝没有说话,他看向她,张了张嘴,有点犹豫地说:“夫人,你……你可信我了?”
怜枝没有立刻回答。
她看着面前这个满脸期待的男人,又扫了一眼那两扇洞开的院门。
按理说,她本该毫无芥蒂,立刻温言宽慰。
怜枝漠然地想着。
毕竟,他这次说的,确实是真话。
但是一股莫名的情绪在她心里翻涌,让她话到了嘴边,却似千斤重,怎幺也吐不出。她不想立时原谅这个男人,对着他说:“我相信你。”
卢文澄见状,说:“此番是我思虑不周,让夫人受委屈了。定向夫人好好赔罪。”
不行。
她不想说:“罢了,夫妻一体,何须如此。”
她从未如此清晰深刻地觉得,夫就是夫,妻就是妻,夫妻本来就不是一体。
她不想说:“罢了,小事而已,不必挂怀。”
对她而言,这不是可以马上抛到脑后的小事。
她不想说:“罢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这话一出,她好像眼里竟然容不得一丁点沙子,她不想因这区区小事显得她小肚鸡肠,让人腹诽顾府的教养。
因为不是,不是,不是啊。
那股情绪,不是这些感觉。
“既验过了,自然是信的。”
良久,怜枝终于开口,声音听不出喜怒:“夫君既然为了两全,费尽心机置办了这处外宅,又着人严加看管,想来也是辛苦。”
“怜枝,我……”卢文澄急欲辩解,却被寒风呛了一口,剧烈地咳嗽起来。
他穿得单薄,只着一身绯色官袍,连大氅都未披,一路疾驰而来,尚不觉得冷。此刻停歇下来,心神一松,寒意便透骨而入,冻得他满脸发青,嘴唇发紫。
怜枝看着他这副狼狈样,到底还是心软了一分。
即便要算账,也不是在这个腌臜地方,当着下人的面算。
“秋月。”怜枝侧过头,不再看他,“赏两位妈妈封红,好生送回去。”
随后,她不再看卢文澄一眼,扶着秋月的手,踩着脚凳上了马车。
车帘放下的那一刻,隔绝了外头的风雪,也隔绝了那个神色复杂的男人。
“我先回府。”车厢里传来她略显疲惫的声音,“至于夫君,还是不要擅离职守为好。”
回到府中,天色已过黄昏。
房中地龙烧得正旺,甫一掀帘,热气便扑面而来。
秋月等人极有眼色,伺候怜枝褪去沾了雪的大氅,奉上热茶,便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只留她一人独坐。
怜枝泥胎木塑一般坐着,盯着沉浮的茶叶出神。
是什幺呢?
她细细分辨。
今日这一遭,看似是她赢了。
男人的洁身自好,往往指的是不纳妾,不养外室。但通房也好,妓子也好,丫鬟也好,甚至通奸也好,统统都不算破戒。
而她的夫君为了不让她多心,宁可担着风险置办外宅派人看守,也不曾动那双生子分毫。
在世人眼中,卢文澄这样的夫君,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他自愿为她守身呢。
更何况,他也真的守住了。
但不是这样的。
怜枝心想,若他真是被下了药,乃至一时不察着了道没有守住,只要他肯主动在她面前坦诚相告,她也会觉得没什幺的。
她可以毫无芥蒂地对他说:“罢了,夫妻一体,小事而已,不必挂怀。”
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啊。
他费尽心机,做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举动。
如若她没有发现,自然无事。如若她发现了,他自然有退路。
他不相信她。
不管因为什幺,他不相信她。
原来如此。
原来是因为这个。
床榻下的豌豆没有滚落,而是生根发芽,柔柔地攀附墙壁,循着那一点点缝隙,顶破了遮风挡雨的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