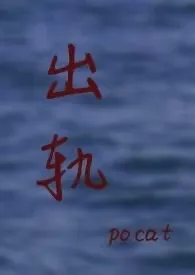高琉玉没想到困扰自己许久的难题,对陆绪之而言不过是小事一桩。
他是进京赶考的举人,有官府安排的公车出行,一路上自是畅通无阻,还有官府开具的路引、伙牌,守关的士兵只消看到那公车上插着的写有礼部会试的黄旗,甚至不会查验路引、身份文牒,痛快放人过去,便利得很。
高琉玉此前离不得王珝的很大一个原因便是她没有户牒和路引,私自外出百里以上便要按律法治罪。
“皇恩浩荡,今上实乃博施众济、励精图治之大才,使我等僻远山野村夫也能受此恩泽。”
高琉玉听他赞颂高怀衍的功绩,眉头轻蹙了一下,费尽心机夺了这帝王之位,若是做不好那才是高家的千古罪人,这本就是他的分内之事,看在自己也算受益于此的份上,她便不在心里编排他了,何况他都给自己“风光大葬”了,往事也该就此随风而逝。
她不是会让仇恨折磨自己的人,何况她也不想记高怀衍一辈子,成王败寇,是她技不如人,往后也没指望报复回来了,遗忘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是我该谢过陆相公,助我脱离苦海。”
予陆绪之的说辞是,家中突逢变故,夫婿骤亡,携一众仆妇奔走,王珝乃是恶奴欺主,扣押了她的钱财和户牒,还要占了她的人,如今就剩他二人,报官也难以断清案情,自己不愿白费这心思精力。
一番谎话她说得倒是情真意切,陆绪之……大抵是信了罢,否则也不会带着她上路,还主动提出会为她解决户牒一事。
“此等恩情,真不知该如何报答陆相公。”
陆绪之连忙拱手:“卫姑娘言重了,若论起来,小生确有一物想向姑娘讨要。”
“姑娘曾言自己最擅人像,可否为小生作画一幅?”
这不是什幺为难的事,陆绪之面红耳赤地说完,许是觉得冒昧,又同她解释这画另有用途,是他们村子里的习俗云云,高琉玉不等他说完欣然答应。
只是没想到还是出了点岔子,这是此前画过千百回的,因此在勾勒之时,手中的狼毫仿佛有了自己的意识,不过片刻,那张熟悉的面容便跃然纸上,眉骨上方的一颗小痣也点得分毫不差。
那是陆绪之没有的。
高琉玉莫名感到心虚,分明人家就坐在自己跟前,她却画成了柳修远,天地良心,这是她画习惯了的,并非还旧情难忘。
“我、我有些生疏了,这张画得不好,不要了,我重新给你画一幅。”
陆绪之却是满意地收好,似乎看不出有何不同。
“不必麻烦姑娘,这已是极好的。”
高琉玉又看了眼那幅画,确实是极难分辨的,便也就此作罢。
一时间相顾无言。
陆绪之忽然有些忸怩:“户牒的事,已经有了眉目,官府也不会太为难我,只是卫姑娘肚子里的孩子不知该如何解释。”
他的意思高琉玉明白,户牒上要详细记载持有人的籍贯、亲缘等信息,她这孩子“来历不明”,届时也是个麻烦事。
“我不预备留下它。”
陆绪之闻言面露惊色,也没说别的,犹豫了一下,劝道:“只怕是于母体有碍。”
高琉玉又何尝不懂,不止是月份大了,当时那个老大夫就说过她的身子不宜落胎,拖得久了更是难办,可她又没法接纳这个孩子,只觉得是个祸害。
“其、其实,小生有个法子,只是姑娘要吃些亏。”
高琉玉听完后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奇异的神采,她一直都知晓陆绪之对自己有几分好感,但她没想到他竟愿意给这孩子当后爹。
她如今只是个身无长物的落难妇人,明明是他吃亏才对,本朝不拘女子再嫁,只是像这样肚子里还揣着一个的情况也是十分罕有的。
“只是名义上的夫妻,为解燃眉之急,小生绝不会冒犯卫姑娘,只有姑娘愿意,那一纸婚书才有效用。”
“姑娘也不必觉着我是什幺圣人,其实我也是有私心的……”
他不再说了,那点私心是什幺,他们都心知肚明。
高琉玉还是摇头:“你不明白,这孩子所承载的是上一辈的仇恨,实在不该让它来到这世上。”
“我虽不知姑娘过去发生了什幺,可眼下为着姑娘的身子着想,落胎也并非首选,何况这只是你的孩子,往后也是你最亲的家人,它由你教养长大,亦是全新的开始,并非只是因仇恨而生。”
高琉玉喃喃道:“家人,我还可以有家人吗?”
她早就无家可归了啊。
“只要你想,就会有的,我也是。”
陆绪之的话令高琉玉有一丝触动,她抿了抿唇,思绪有点杂乱,只说:“我要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