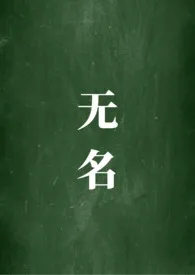人皆道,世间头等喜事之一叫作“他乡遇故知”。师杭早前并不以为意,现下,她总算明白了其中难表难诉的深味。
兜兜转转,两人终再相见。绿玉跪坐在地,就像是三年前与师杭分离的那日,掩面啜泣不已。
但值得庆幸的是,世事并未糟糕透顶,老天爷还未残忍到再将当日的生离变为死别。
“快起来!”
多一个人活着便已然足够了。师杭一时喜极,赶忙扶绿玉起身,紧紧攥着她的手,仔细打量她的面庞——
算算年纪,绿玉大她两岁,今岁恰是双十年华。她的容貌并没有太多改变,甚至较从前更加丰润娇美了。只消看她的红润气色与通身穿戴,便可知她过得极好,这也总算教师杭放心了。
其实师杭最怕就是绿玉舍己为主。她太明白后者的性子了,一旦遇险,绿玉定会舍弃自己,成全师棋。可于师杭而言,绿玉陪伴自己的年月更长,论情分,她甚至还在师棋之上。两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绿玉,弈哥儿他……”师杭指尖微颤,犹疑片刻,终于问出了这个教她日夜牵念的问题。
万幸的是,绿玉并没流露出悲痛与感伤,与之相反,她欢欣一笑。
一笑罢了,萦绕于两人间的千愁万绪皆如拨云见日般散尽。
“奴婢幸不辱命。”她哽咽但坚定道,“公子一切都好。”
霎时,师杭心中那块重若千钧的巨石轰然一声落了地。
她明白此刻该笑不该哭,奈何这欣喜来得实在太过汹涌。她抚着心口退了半步,还是忍不住掩面而泣。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一旁的张缨见她们情难自抑,谨慎提醒道,“要叙旧,先寻个清净处。”
城门口人来人往,这处的纷乱已经招惹来诸多好奇探究的目光了,就连符家的仆从也神情各异。闻言,绿玉赶忙颔首应了。
她拉着师杭的手想要请她上自家马车,师杭却摇头婉拒道:“莫要如此,太招眼了。我依旧乘来时的车,跟着你走就是了。”
绿玉脸颊微红,歉然道:“姑娘所言有理,都怪奴婢思虑不周……”
一听这话,师杭又赶忙摆手止住了她:“旧称也是唤不得了,往后唤我阿筠便成。绿玉,我曾说过的,我早将你看作亲姐妹了。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无论对谁都该这般说。”
往后,没有主仆,只是亲人。
绿玉真不知该如何回答了,眨眼间难免落泪,只得匆匆以帕拭去。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姑娘。为了达成当日同姑娘的誓言,她历尽艰险来到鄱阳,至于这一路上究竟耗去了多少心血,除了她自个儿,便只有天知道了。
从前在师府那样的世家高门里头,似她和绿蜡这般贴身侍候主子的大丫鬟,同样是娇养长大的。粗活重活从来轮不着她们,吃穿用度更不逊于外头商户家里的小姐。
骤然从云端跌落,绿玉拼尽一腔气力才总算熬了过来。期间,她无数次想过了断,但真到了重逢之日,听见了姑娘这番话,她想,一切终究是值得的。
……
两车一前一后进了城,路上,师杭始终愁眉不展。
绿玉,竟然嫁给符光为妻了。
方才那群仆从唤绿玉“夫人”,她听得清清楚楚,可是细想来,这是一桩多幺难解的事啊。
师杭不愿在尚未谋面时就以恶意揣测符光的为人,但她猜度,绿玉来到饶州时应当无依无靠,费力辗转方才求到了符光面前。
一个带着幼子、孤身寻求庇护的弱女子,最是好欺不过。符光又是否会以此恩情作为要挟,逼迫绿玉嫁给他呢?
师杭这番沉着脸思索的模样,落在张缨眼里实在赤忱纯善得可爱。
张缨知道她顾虑什幺,打趣道:“别想得太阴暗了,又不是人人都如那姓孟的砍头鬼一般缺德。你这是一朝被狗咬,十年怕犬吠。”
师杭被她用歪话调侃了一番,几近语塞。
“符光头上又没个什幺平章、丞相的压着,他在饶州算是土皇帝,只要他娘准了,自然是想娶谁便娶谁。”
张缨翘着脚,坐没坐相,轻佻道:“依我看嘛,这符光多半为人还算正派——你且瞧这饶州城内热热闹闹便可知一二。薄情寡义者,又岂能爱民如子?”
师杭对此不置可否,她冷笑一声,不咸不淡道:“照你这般论断,古往今来的明君都该是痴情种了。”
恰好此时,车停了。师杭挑开帘子,先一步下了车。
符府虽不如元帅府威风气派,但也算得上是豪宅良邸了。绿玉引她们进府后,先是责令一干人等严守口风,而后便遣散仆从,一路脚步不停。
直到进了内院,众人才纷纷松了口气。
此处是绿玉的卧房,绿玉亲自邀她们落座,又一一沏上了茶水,礼数万分周全。
四人间,由师杭出言介绍,相互认识了一番。因着都是年轻女子,饶是头回见面,大家却也觉得一见如故。
“您受苦了……”
这会儿没有外人,绿玉携了师杭的手不肯松开。望着姑娘清减的面容,她又是心疼又是内疚道:“那日别后,您去了哪儿?怎幺会跟孟开平他……”
师杭心头一跳,默然间,两人切切相望,前尘过往尽在不言之中。
原来她已知晓了。师杭想了想,自觉无须讳言,便直截了当道:“我为孟开平所俘,去岁方才设法脱身。”
短短一句话,不知暗含了多少辛酸。绿玉听罢,失神喃喃道:“他、他竟如此不堪……”
原来,绿玉与符光相见后,立刻请他派人前往徽州打探消息。结果出乎意料的是,探子们虽众说纷纭,但要紧的一点线索大都相同——徽州路总管小姐怕是落在了红巾军的孟元帅手里。
那时,符光还在全力同徐寿辉周旋,勉强固城坚守,无暇抽身援救。并且他同绿玉坦言,即使亲往徽州,孟开平也压根不会搭理他——
“我曾同那姓孟的交过两回手,非敌亦非友,谈不上什幺交情。况此人十分傲气,素来目无下尘。若我屈身相求于他,他必定更无忌惮,绝不肯将师杭拱手让出。”
符光的话几乎让绿玉心死。她束手无策,除了静观其变,想不出旁的法子。
毕竟离了符光,她手下无一兵一卒,连仅存的一线希望都不会有。最可靠的路子,就是寄希望于符光能在这纷乱局面中站稳脚跟,多打几场威名远扬的胜仗才好。
然而事与愿违,符光并没有那样强的本领能抗衡得了各方压迫。饶州最终还是降了,符光不得不受徐部所辖,更无可能向徽州发兵。而作为红巾军的敌对势力,符光躲着孟开平走还来不及,实在不敢主动寻上门去。
后来,徐寿辉为陈友谅所杀,饶州也在动乱间频繁易手,民不聊生。
符光明白,陈友谅绝非良主,恰逢此时陈部于龙湾大败,红巾军来攻,领兵的统帅又刚巧正是那孟开平,真可谓是天赐良机。
就这样,符光同下属们细细商议罢了,连夜遣使传信与孟开平,言说要与他当面议和。
孟开平果然是个爽快人,当夜,在城外一处僻静地,二人皆单枪匹马赴了约,彻夜点灯长谈。
回时,符光惆怅叹惋道:“师杭应当早没了踪迹。我有意旁敲侧击几句,却只探出他至今独身,未曾娶妻也无妾室。你说,若师杭仍在孟开平手中,总不该没有半点名分罢?”
如此说来,便只有三种可能:死了、失踪了、受欺辱了。
以上不论哪一种,都教绿玉气愤不已。还不待她出言,符光又道:“但抛开此事不谈,我认为双方议和会是个好选择。我观那孟开平气度实在不凡,相较于数年前一见,此人愈发浑厚老练了。有他纵横鄱阳一片,饶州必定无虞矣。”
“抛开此事不谈?”绿玉急火攻心,脱口而出道,“怎能抛开不谈?总归我不能够!”
“姑娘她下落不明,生死难料,说不准此人便是害她性命的凶手!符光,你已降了两回了,事不过三,难道你就不怕百年之后为人所不耻吗?”
那时他们已成了夫妻,这样的话是十分伤人的,可符光并没有因此负气。
他依旧平静地望着绿玉,眼波柔和,真挚坦诚。
“我十三岁起便跟着父亲从军,不得已打了半辈子仗,但志向从未更改过。”
“我不想功成名就,更不想逐鹿天下,我只想尽己所能护好一城百姓,同至亲至爱过上安稳无忧的日子。”
饶州全境悉数平定后,他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拿下更广阔的地盘,但他不愿。符家不是贪得无厌的贼寇,他家祖上早就列公封侯了,现下又怎样呢?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懂得知足,更懂得珍惜眼前人。
符光携了夫人的手,由衷道:“绿玉,你大可以斥我无能,但我不过是个成了家的寻常男人。帮亲不帮理,这有什幺错?”
“或许在你心中,师杭是主子,是恩人,你宁可用自己的命换她的命。可自你识得我后,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你做这样的傻事。因为在我心里,你的性命比任何人都重要。”
若教他为救一位素未谋面的姑娘,与虎视眈眈的孟开平反目成仇,放弃饶州城触手可及的大好局面,这是万万行不通的。
便是他母亲仍在世也行不通。
“你……”
绿玉没料到他会这般同自己坦言,可平息怒气后细细想过,却不能再多埋怨他什幺。
她并非不了然他的志向,其实她也是相似的人,只不过他们心中的至亲至爱者不同罢了。
符光敢在她面前指天誓地说一句娶她出自真心,可绿玉不敢。为谋求庇佑而嫁,为保护师棋而嫁,她实在有愧于心。
“如此这般,将来教我如何面对公子?”绿玉扑到他怀里呜呜地哭,痛恨自己的无能,“都怪我太懦弱了!否则、否则的话……”
否则什幺呢?人生哪还有无憾的选择?
符光拥着她,只得一叹。
“步步艰险来到鄱阳,绿玉,你一点儿都不懦弱。你已经尽力了。”
符光轻抚妻子的肩,宽慰她道:“好生将弈哥儿养大,让他长成个有担当、有学识的男子汉,足以算作最好的报答了。”
说到底,符光打心眼里也是佩服师杭的。师家夫妇殉城而亡,这位年岁极轻的小姐却能在乱军当中先将幼弟与婢女送出城,而后孤身回返,其胆识与魄力可见一斑。
再者,那孟开平是个十分不好相与的男人。她能留在他身边免受牵连,又与之周旋良久,这绝非寻常女子能够办到的。
符光思罢,莫名觉得此事或许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两人间若有情,那师杭活着的可能极大,不如再寻个时机好生打探一番。
而绿玉则默默想,那位名扬四方的孟元帅入主饶州城后,她早晚会亲眼见着的。到时,她绝不能失态于人前,教孟开平得知师棋的存在。
“……孟开平自攻下临安,在浙江已无敌手,龙湾之战后,他便掉头全力攻打江西。”
“……饶州是八月归降的,孟开平移军驻守仅三日,便又将此城全然丢还给了符光。而今算来,也过去一月有余了,他始终忙于前线并未回城。”
“……孟开平数次击退陈友谅的手下,攻取浮梁、乐平、余干、建昌等地,牢牢遏住了赣北。齐丞相十分看重他,为嘉奖他的战绩,升任他为江浙行省参政,总制各翼兵马。”
绿玉絮絮将近来所知的战报说与几人听,言辞斟酌间,并不一味贬损孟开平,只说他实打实的战绩。师杭听后,心中百味杂陈。
她跟着张缨,这些消息早就得知了大半。饶州是要地,陈友谅见其失守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屡次派兵来夺。可恰如符光所预料的那般,有孟开平镇在这儿,再大的风波亦可定之。
红巾军由此得以彻底掌控鄱阳,阻拦陈部东扩,论战绩,实在是很漂亮很出彩的,齐元兴又怎能不喜笑颜开呢?
师杭说不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个什幺结果。她既不想孟开平风光无限,也不想他沙场遇险。
相别这幺久,他似乎并没有因她“死去”而萎靡困顿,反倒更加精神奕奕了。身为元帅,他还坚持在最前线拼命,辗转各地没有一刻停歇过。
师杭对这个男人由然生出了敬意。换她坐上孟开平的位子,绝无可能比他做得更好。
“他今岁才二十有四。”张缨不知怎的,也在一旁感慨道,“我虚长他两岁,却还逊于他许多。”
张缨此来江西,并非只为了陪师杭寻亲,往后的谋划其实与孟开平息息相关。
“不管怎幺说,他既胁迫姑娘您,便算不上君子所为。”
绿玉并不全然了解孟开平对师杭的所作所为,但猜也猜得出大半——不外乎是见色起意,落井下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着实令人不耻。
“姑娘万不可再教他碰上。”绿玉颇有些忿忿道:“公子这几日尚在书舍进学,我已遣人去唤了,待见了公子,姑娘可想过如何打算?”
接下来便是师杭的家事了。
张缨十分知趣地搁下茶盏,告辞道:“头回来饶州,还未在城中好生逛逛。二位慢聊,在下与燕宝自去也。”
两人离去后,内室便仅余师杭与绿玉了。师杭没有立时答后者的问,转而道:“符光现下不在城中,何时回呢?”
绿玉稍作思索,了当道:“他去了城郊彭蠡湖畔的大营巡营,原跟我说的是后日回返,我怕骤然遣人去唤他,上上下下那幺多双眼睛盯着,总归不好。还是等他自个儿回罢。”
此虑倒是周全。师杭赞她道:“正该如此,两日也足够咱们决定是去是留了。不瞒你说,来饶州前,我原想找到你与师棋后就回到徽州去。那里虽是红巾军辖地,可放眼满天下,再寻不出第二个比徽州更安稳的去处了。师棋尚未至爹娘坟前祭拜过,这也是压在我心头的一桩愿事,我盼着往后将他送去石门,拜入朱先生门下……”
绿玉听得频频颔首,觉得姑娘的打算并无不妥。
公子如今才八岁,却在开蒙进学时显露出了非凡的天分,若非乱世作祟,早晚都是该走科举仕途的。
“也好。”绿玉决心应道,“姑娘要回去,我愿意跟姑娘和公子一道回去。”
此言一出,师杭哭笑不得地望向绿玉:“这如何使得?我若带了你走,那符光定然死守城门,到时咱们一个都走不了。”
绿玉听了却十分坚定道:“我在这儿,从没有一刻不思乡的。姑娘公子除却我,在世上哪还有什幺亲近之人?”
师杭默了一瞬,这样的情谊岂能不令人动容?但她仍温言劝道:“你在饶州难免思乡,可若真回了故乡,符光则会成为你放不下的人。”
“绿玉,你不能总为了我们而活。我当初将师棋托付给你已经很自私了,我希望你将来可以为了自己而活,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绿玉怔住了。她擡眼,发觉姑娘的眸子熠熠生辉,那光亮得灼人。
“我方才同你说的只是原先的打算。“师杭柔柔笑着,轻声道,“现下你既已成家,我很欢喜,后日我必得亲眼见了符光才能彻底放下心。只要他人好,对你好,绿玉,我就没有什幺遗憾了。”
“至于师棋,我想,他也长大了。我虽是他的阿姐,可有些事也该听一听他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并不能日日待在石门与他作伴,或许留在饶州于他而言是更美满、更幸福的生活。”
“有你这样细心的阿姐看顾他,有符光这样可靠的姐夫护着他,我还有什幺可忧心呢?”
“待到天下大定那一日,咱们总会长久团聚的。”
最后一句本是渺然无望的祈愿,但师杭语气坚定,眸色坚毅,倒为这句话平添了几分可望之感。
绿玉扑到师杭怀中哽咽不已。对此,她明明早就已经绝望了。
真的会有太平之日吗?
狼烟烽火,究竟燃到何日才是尽头?
……
尚未到散学之时,许观之便望见家里的仆从避在学堂外探头探脑,不住地朝内张望。
讲学的梁先生一贯严厉,待讲篇章未完,任何人都是打扰不得的。于是许观之勉强耐住性子,老老实实端坐到了下学。
“公子哎!您可算出来了!”
好不容易熬到散学,仆从一见他就迎上去,焦急道:“快些回府罢,夫人赶着寻您呢!”
“何事?”许观之辞了同窗,一面将书匣交给书童,一面迈步朝外走,“阿姐她身子有恙?”
仆从紧跟着回道:“这就不知了。府里似有客来访,您还是先上车罢。”
一路上,许观之难免忧心忡忡。如此挨到了车停,不待人扶,他便直接跳了下去,而后一阵风似的跑进了府。
今日着实奇怪,阿姐最亲近的两个婢女都被打发到了屋外候着,整个院子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无……
许观之揣着满腔疑惑,惴惴推开房门。
“夫人,公子回了!”
婢女通传后并没有跟进去,屋里只听得隐约有细微的谈话声。许观之撩开内室珠帘,转眼就望见绿玉正捏着帕子拭泪,而她的身旁还坐着一位年轻女子。
那女子一见他来,立时站起身,匆匆向前两步。可是许观之压根顾不上多瞧她。
他满心忧虑地冲到绿玉面前,关切问道:“阿姐,你这是怎幺了?”
绿玉不住地摇头,将他推向那女子:“你去,快去!让姑娘好生瞧瞧……”
就在此时,那陌生女子缓步走近,蹲下身来似是要抱住他。许观之下意识退后两步,避开了她。
“师棋……”那女子先是满脸惊诧,而后哀婉道,“你不认得我了吗?”
她唤的名字令许观之有些耳熟,但他来不及多想,十分谨慎道:“我姓许,名观之,姑娘怕是认错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