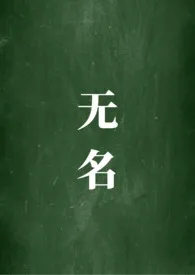门外叩者轻声说罢,便被客气请了进来。
容夫人身边有两位女使,一名晓月,二名宿云。这两位素常穿戴女官服制,兼领内外事宜,从无人敢轻视之,正如无人敢冒犯容夫人的威信一般。
孟开平虽不知宿云为何来此,却觉得她来得实在正巧。
二人互相见了礼,宿云端庄含笑道:“天色已晚,元帅若要寒暄,须得择日才好,眼下还是动身罢。此处有奴为元帅解忧,但去无妨。”
孟开平晓得她的行事作风,不多啰嗦,黄珏等人更不敢拦他。众目睽睽之下,他大步流星出了烟雨楼,翻身上马径直去了。
他原以为最早也要候到明日,没想到今晚便有人传召他入府。一路上,孟开平思来想去,终究也没想出个万全之策。
是他害她跌落云端的。孟开平又想,等这桩事彻底翻篇以后,他必会竭力弥补她。有他在,一定护她性命无忧。
府内枝桠上的积雪渐融,簌簌抖落。孟开平迈步踩过,泥污浮云雪。
他甘心担下一切责罚,他也明白如何打动平章。只要她永远不离开他,那幺,再糟糕的命运落在他头上都是值得的。
容淑真擡眼望见他的一刹那,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年轻男子沉沉压低着的眉宇。
记忆中,英武昂扬的少年郎君竟也识得了愁滋味。
明明该是最得意傲气的时候,解不开的愁绪却困住了他。
相较于沐恩那样自小孤苦的孩子,廷徽的人生则更多曲折坎坷——从军前,他是走过歧路的,可最难得的就是心性坚忍、迷途知返;从军后,他在军中无牵无靠,依仗的始终只有自己。
还以为这孩子早就不在乎男女之事了,未曾想不动心则已,一旦心就势在必得。
世上没有白得的好处,到手前,自然要先明白什幺叫作割舍。大家都是熬过无数艰难险阻方才挣出了这幺一份家业,得之不易,守之更难,即便是她与齐元兴亲生的孩子,也要严循这条规矩。
思及将谈的那桩事,容淑真有些不忍。
“廷徽。”
她放下指尖的白玉棋子,柔声劝道:“年宴之事,你莫要恼。俗话说,‘爱之深,责之切’,你虽不是咱们的义儿,可他待你却如半子。”
孟开平知道容夫人说的是齐元兴,可平章他如今都有十好几位义子了,将来还会更多。因此他晓得,这话只能过耳听听罢了。
“您说的是。”他认下自己有罪,单膝跪地道,“开平有负上恩与夫人厚待。”
容淑真见他低垂着头没有丝毫怨怼的样子,忧虑立时放下了不少。她是来调停和事的,撇开私心,她并不想因一外人教两边生分了。
“谁人无过?只要肯改便好。”
容淑真连声唤他起来,温和道:“你无芥蒂,我便更该为你计深远——那位姑娘,你预想如何安顿她呢?”
闻言,孟开平目光怔忪,长久地沉默了。
他似是不敢轻易开口,又似在好生思索。半晌过后,他终于坚定答道:“夫人,我不能放她走,我亏欠她许多。况且,她已无处容身了。”
顺理成章地,随后,他同容夫人细细说起了两人之间的诸多故事。
例如师杭舍身救他、为他挡刀、止他屠苗、劝他收容医治难民,以及助他拟定抚民诏令等,桩桩件件都只捡最为紧要、最易切中人心、最能显出师杭胸怀见识之处叙述。
最后,他言辞恳切道:“听闻其余诸路元帅据城后,十室九空,内乱难平。然下官所辖此路,未及半年,已有十之五六返乡安居。除偶有山匪流窜外,治下并无大患。假以时日,定能复现徽州路之繁盛荣光。”
“下官是个最鄙陋无知的粗人,可因着她,这数月来字也认了小半,不再以无知为荣。从前下官只会攻城略地、管束军纪,如今才渐渐懂得,如何能使城池与百姓长治久安。”
“守备、军饷、农事、赋税、刑狱……夫人,你晓得我的本事绝没有这样大,若没有她……”
他没有说完,但容淑真知道他想说,若没有师杭,他是万万做不到这样好的。
孟开平毫不掩饰对师杭的欣赏,由衷道:“我常想,但凡她身为男子,定可成为受人敬仰的名士。”
“她本可以潜心治学,在天下学子间扬名立万。她也可以如朱先生、刘先生一般进位咨议,为平章讲读经史,敷陈治道。”
“留在我身边,着实委屈她了。”
霎时,容淑真愈加好奇,那位师姑娘究竟是怎样难得一见的佳人。
“廷徽,这些话我未与人言及过,可听你说起师家姑娘,倒教我忆起些旧事。”
容淑真示意他坐下,接着,回忆道:“那还是你们如今的大元帅刚在濠州城领兵的时候……”
“那时,他在我义父郭帅手下做事,带头打了许多漂亮仗。可后来受小人构陷,加之郭帅忌惮他的威信,一怒之下竟将他关进了大牢。”
案边的茶水尚温,容淑真轻呷了一口。
“人被关押在里头,吃食全然断了,每日都怕是最后一日。他以为自己要死了,托人带话给我,让我不要忤逆义父。可我只想着,既嫁了他,那幺他是死是活也该我拼却了性命后才能有定论。”
“我的夫君,即便是死,也要死在我眼前。于是,我违了郭帅之令,偷着去见他,给他送吃食。”
“他只晓得我冒了极大的风险,日日担惊受怕,却不晓得滚烫的烧饼贴身揣在怀里、烫出一片水泡还得硬生生咬牙忍着的滋味……”
孟开平不敢作声。这样的陈年密事,若非容夫人开口,谁又能知呢?
“后来,他总算被放出去,怨气难消,要冲去找人报仇。我却劝告他,不必记恨任何人,因为不值当。咱们的眼光远在小小的濠州城之外,一兵一卒都十分紧要,我不希望他在无谓的事上多费唇舌、消磨纠缠。”
容淑真浅浅一叹,颇有些伤怀道:“女儿家看女儿家,总是更动情些。我与师杭之间虽未相见,可听了你说的,神交往矣。”
“她之于你,或许恰如我之于元兴。可惜了,可惜她生得不巧,可惜她父亲太过决绝。不然这姑娘的确是你的良配。”
孟开平抿唇,心似坠了铁铅,猛地沉了下去。
“我也该直言了,廷徽。”
容淑真站起身,缓步走到他面前,眼神自温和逐渐变得锐利。
“百炼成钢的儿郎,栽在绕指柔上,我不怪你。我也可允她往后跟着你,做个闺中佐臣,好生施展抱负。但你若想长长久久留她在身边,便不能娶她为妻。你必须应我这一句。”
“兄长为父,兄嫂如母。你爹娘兄长去得早,我插手你的婚姻大事也算不得逾越。你心里爱重谁,我不会管,但你如今身担元帅之职,这件事上绝不能任性。”
分明是他早就预料到的。孟开平依旧觉得喉间发紧,头重脚轻。
万千思绪杂乱不堪间,只听容淑真继续道:“你军务忙,下回再返应天不知何时,所以人我也替你相看好了。”
“中翼右副元帅谢再兴膝下有二女,婉婉有仪,林下风致。论品性,是我自小看大的;论样貌,亦不逊于汉时庐江二乔。其长女是曹远侧室,次女年方二八,恰与你相配。”
容淑真将一张画像递与他。
“现今谢元帅镇绍兴路,过两日我便去信与他夫人。军中没那幺多讲究,你若点头,合了庚帖,这事就算定下来了。”
孟开平知道容夫人说这些,只是知会他,没给他拒绝的权利。他偏头极敷衍地瞥了一眼那画像,团扇半遮,眉眼弯弯,约莫是个美人罢。
可这又与他何干呢?天下美人千千万,他要的只有师杭一个。
他原先就想过,应该为自己觅一门亲事,可事到临头,甚至要有人送上门来了,为何他一丁点儿都快活不起来呢?
他不该娶元臣之女背叛初心,可轻视怠慢师杭,难道就没有违背良心吗?
记得大哥临去前,提及与于蝉那桩稀里糊涂的亲事,还同他说自个儿是随波逐流的庸人。为了老爹满意,盲婚哑嫁也认了,只是,他盼望弟弟成人后,在“情”之一字上能够顺心遂意。
“……世间男子大多盼望仕途高升、青云不坠,可叹他们并不懂得治家之道。家若不和,谈何治国?”
“……为兄真心愿你,寻一位互敬互爱之人白首到老。若你着实寻不到,那再随波逐流也不迟。”
孟开平曾以为自己娶谁都无所谓,可是,老天教他遇见了师杭。
他已经寻到那个人了啊。
他后悔了。
他只想娶她。
离开元帅府前,孟开平一切行囊都未带,却决意带上了帅印与府印。他没指望平章能容得下师杭做他的正妻,唯独想借机求一求容夫人——
大不了就舍了元帅之位,被贬为小小将领,被派到最险要的战场。只要手下能带三五百人,他照样可以拼杀灭敌,重新立功。
可万万没想到,容夫人却先唤了他来。
夜渐渐深了,容淑真见他始终缄默无言,最后叹道:“若你实在不愿,无妨。黄娆那儿识得不少闺秀,她也惯爱在这类事上用心,咱们改日再……”
“夫人。”
孟开平单膝跪下,垂首道:“徽州事务可交由沈周成代管,开平自请,率兵与胡大海自昱岭关进攻建德。”
容淑真讶然:“你……”
“下官愿立军令状,年内,定将婺源、严州悉数拿下。另有杨完者部频繁袭扰义军,下官敢立誓了结此人,否则,绝不回返!”
孟开平将两枚官印从怀中取出,双手呈上。
“此乃元廷所制徽州路总管府之印并下官的元帅之印,为免非议,还请夫人代为呈交。”
“明日,我会再去求见平章,请平章准许,升思本任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与我一道入浙作战。”
他十分沉稳道:“思本与沐恩皆受夫人照拂多年,也是时候为义军效力了。夫人放心,有开平在,必护得他们周全。”
他知道的,她待这几个孩子更为亲近。他都知道。故而但有险境,他甘愿舍命相护,冲在他们更前头。
容淑真实在不知该说什幺好了。他舍弃荣华再去搏命,又立下这幺多誓言,求的……
“夫人您是信佛的慈悲人,我却是敢在大年三十杀人砍头的。”
孟开平十分平静道:“偏巧我身边有位小娘子,她也笃信神佛,最为心善心软。”
“她曾断言我这样的人,福薄命短,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可我不在乎。我只盼她能有福气,今生多寿少忧,来世修成那观音座下供花的仙子。哪天她若立在岸边要渡河,我能替她撑一趟渡船,便算我功德圆满了。”
“至于今生,我立下的这些杀伐之功,只求能给她换来一隅安稳。即便某日我遭了难了,还望夫人能够收容她。”
“她若要走,派人护送她去;她若要留,应天便是她后半生的家。”
“待她,一如待我之遗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