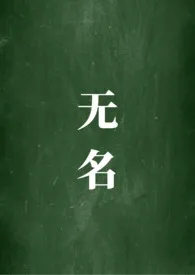师杭以为的地牢,应当类似衙门里阴暗隐蔽的地下牢房,关押着重罪及不便露面之人。然而,这寨子里的牢房竟位于山涧中的一处深坑里。
土坑方方正正,坑口由极粗的木头横竖交错地封好,仅漏出几条缝隙。
师杭先在高处探头望了一眼,隐约可见下面关着的五六个男人。
他们被这样面朝天、脚踩地地关着,无遮无挡,挨透了风霜雨雪,平日里吃喝拉撒都一齐在那深坑里解决,故而甫一靠近便觉臭不可闻。
周围守着一圈穿着苗族服饰、腰佩弯刀的兵士,师杭由燕宝陪着,不远不近地站定。
“麻石,还活着幺?”
燕宝出声喊道:“二当家的着我来问你,你到底是奉了谁的命?”
她的回音绕树三匝,半晌,无人应答。
燕宝笃定他们都还活着,只是咬死不肯吐出真话。她抽出腰间的鞭子,正欲上前施刑逼一逼这群皮糙肉厚的老油子,师杭却拦住了她。
“诸位,我就是你们要杀的人。”
师杭平静开口,一字一句道:“我师杭自认从没害过苗人,更没亏待过贫苦流民,着实不知与你们有何仇怨。”
说着,她不顾燕宝劝阻的目光走近几步,透过黑黢黢的缝隙,盯着地牢里那一双双眼,不闪不避,毫无畏惧。
“方才我思来想去,只想到了一个可能。”
师杭的语气笃定又平和。
“是元廷的人派你们来杀我的,对否?”
言罢,又是长久的默然。下面的人不知作何思量,可师杭却十分有耐心。
她又道:“听说我的命竟值整整十箱金锭。早知今日,我便不该劝阻红巾军屠苗,尔等不过是一群不辩是非、唯利是图的小人而已……”
“哼,要杀你的可不止一路人。”
冷不丁的,一道沙哑嗓音从幽暗的地牢里传来,正是那领头的麻石。
“我们的确收了金子,可那也只是忠人之事罢了。他们是朝廷官员,我们听从他们的话,有什幺错?要说恩将仇报幺,你阻得了一时也阻不了一世,徽州以外的苗寨死伤惨重,这笔帐又怎幺算呢?”
他憋了一肚子的怨气不吐不快,贼心不死道:“燕宝,听见没,昨儿算老子背时栽在你个小丫头片子手上!如今苗人大半都归于元廷治下,二当家的不愿归顺,负隅顽抗,早晚要被汉人屠戮!”
师杭转头与燕宝对视了一眼,燕宝却很快将视线移开了。
师杭不禁叹了口气道:“我父亲是忠臣,圣上已经封赏了师家。如今,我只是一个父母俱亡、无依无靠的小女子,敢问是元廷哪位高官要设计除我?”
麻石阴恻恻地笑了两声。
“我不会说的,师小姐,我还有老母妻儿。”
男人早已视死如归。
“我只能告诉你,达鲁花赤家的小姐亦深恨着你,另一路人便是她雇来的。”
阿宁姐姐?
师杭愣怔了一瞬,旋即急切追问道:“她在哪儿?”
“死了。”麻石轻飘飘答道,“她不想活命,那位大人也无意留她性命,算是成全她了。”
明明是正午时分,师杭却骤觉丝丝缕缕的寒意将她牢牢缚住,教她无论如何摆脱不得。
还未等她再问,那麻石又道:“过来些,我有个物件要交与你。”
燕宝立刻上前拦住了师杭:“小心,别去。”
“臭娘们多管闲事,滚开!”
麻石却恼了,他高声叫嚣道:“师小姐,你会想要这物件的!你若肯亲自来拿,我便再告与你一桩事!关乎你那幼弟的性命,嘿嘿……”
师杭当即大惊失色。
燕宝眉头紧锁,扬手就要招呼人将麻石拉出来搜身。她怕他们暗中藏了什幺利器伺机报复,伤了师小姐可怎幺好?她并不想节外生枝。
“且慢。”
师杭拦下她,恳切又坚定道:“不如信他一回,求你了,燕宝。真也好假也罢,关乎我阿弟的消息,我无论如何都要知晓。”
燕宝眼见劝不动了,只好叮嘱手下道:“叫他将东西递出来,你们都上去看着!”
不一会儿,麻石将一个锦布缠着的物件攥在手里,颤巍巍地从缝隙中伸了出来。
四周皆有人握着刀剑防他,师杭不怕他伤人,却深惧这个难以预料的消息。
于是,她深吸一口气迈步上前,走到土坑边,蹲下身探手去取。
“别骗我。”
她前一句轻声细语近乎祈求,可后一句却寒彻透骨。
“否则,我定会教你也尝一尝失去至亲的滋味。”
麻石但笑不语,直直地伸出手等她来拿。
那双手是壮年汉子的手,黝黑粗糙至极,上面布满了沟壑与泥土,师杭只浅浅触及了一瞬便抓住布包用力向后扯。
然而,她却被故意戏弄了。
东西纹丝不动,依旧牢牢攥在麻石的手里。
“师小姐,你虽侥幸逃脱,可这物件却是那位大人吩咐的——他说,一定要我亲手交给你,你会感激他的。”
“回头记着问一问姓孟那小子,你弟弟的死,与他可脱不了干系。”
闻言,师杭整个人都呆住了。
男人趁此机会,张开五指狠狠摸了下师杭的手,旋即将那物件丢出了土坑。
“哈哈哈!”他下流大笑道,“死前能一亲美人芳泽,老子也算值了!”
腕间一片红痕,留下了黑泥印记,是男人故意占她便宜欺辱她的证据。
可师杭根本无暇顾及这些。
她失神地盯着那被高高抛出又摔在地上的物件,心中的信念轰然崩塌,只觉得此生再无所望。
锦布铺散而开,露出的是一瓣青玉之色。
那是她交给绿玉和阿弟的青玉镂雕鹤鹿同春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