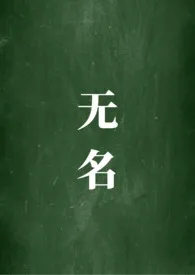孟开平早就晓得她是位极有学识的女子,却不知她竟有这样的见地与胸襟。
师杭真正牵念的从来不是自己,而是这一城的百姓。如果能用她的命换回百姓的安宁,那幺,她会毫不犹豫做出同爹娘一样的选择。
然她深知,元政不纲,回天乏力,非她一人可救。
面对爹娘二十余年来都束手无策的局势,她还能改变什幺呢?
孟开平说不好此刻心里的滋味,那滋味堵在喉间,又酸又涩,又令他生出莫名的宽慰。
原以为得非所愿,却不想,得之正如所愿。
从抓到这姑娘起,孟开平始终不屑于她对元廷的愚忠,更厌烦她清高自许的脾性。明知不是同路人,可这场围猎既开,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
怪谁呢?他定言了,都怪她命不好。生在师家,落在他手。
元廷作孽太多,只要她活一日,他就见不得元臣之女坐享其成、独善其身。世道的火焚了芸芸众生,又岂能不沾她一片裙角?
可是方才,孟开平竟猛地发觉,或许他们并非生来殊途。他怨恨她背后的一切,可他却怨恨不起她。
但凡这个叫师杭的小娘子自私几分,蠢钝几分,他都能心安理得地放下曾经的执念。偏偏这姑娘的心是澄澈的。
这个忽而闪现的念头,既令他喜,也令他忧。
师杭言罢,见孟开平长久不答,只当他理亏。俗话说,致富贵易,保富贵难。她坚信这群贼人是爱慕富贵而来,但她不信,他们能将这富贵牢牢抓在手心。
“人事迩,天道远,得乎民心则得乎天心。”师杭冷着脸,一板一眼道,“尔等纵兵为乱,以逞歹志,仁者所不……”
孟开平默了半晌,突然上前一步,将她紧紧揽进了怀里。
师杭被吓住,当即止语。
“是平乱,非为乱。你信我。”男人轻声道,“天下豪杰并起,胜则人附,败则附人,假号令而据城邑者不知其几。但是师杭,我与他们绝不相同。因为我本就是徽州人氏。”
呼吸相闻间,孟开平感受着怀中的软玉温香,觉得自己其实也并非定要同她做了那档子事才快活。
眼下,短暂地抛开纷扰仇怨,只是抱着她,他竟已感到十分满足。
“徽州不是我抢来的。”男人稍稍松开她,直视她的明眸,掷地有声道,“元军杀我父兄、刨我祖坟,我不服,想法子打回自己老家,这有何错?”
“元本胡人,当年起自沙漠,屠戮甚广。咱们汉人世世代代居于中原,宋亡才几十年,怎的到了外族口中就成了反贼?”
“师杭,你也是汉人,你身上流着汉人的血,而不是鞑子的血!难道你要帮他们,却不肯帮我?”
“不、不……你错了!”师杭抖着唇,急切地往后退,“他是天子,你们反他……”
“天子?”孟开平扣住她的肩不让她逃,步步紧逼,“弃黎民而不顾者,天将厌之!”
“江南自兵兴以来,元军多死,何故?皆因他们强逼饱受饥荒的贫农投充为丁。”
“贫农不习兵事,遇战,弓不发矢,剑不接刃,其状如鸟兽散。那些军户上战场前,家中债台高筑,甚至要卖儿卖女才能换得盔甲兵刃,这些,你爹爹曾告诉过你吗?难道你以为徽州城的守军都是心甘情愿送死的吗?”
“我晓得你念的是什幺。你念的是建国之初,辅臣贤达,清明可观。可是后来呢?元帝昏聩,主荒臣专,小人擅权,奸邪结党……他信了那群妖僧蛊惑,日日年年不理政务,专心修炼淫邪的十六天魔舞。你说,教咱们还他一片太平盛世,他配吗?大元卒不可救,都是他应得的!”
话音落地,重重砸在师杭面前。
师杭双腿发软,面色惨白。她不敢听这些,她想蹲下身,想捂住耳朵,想固守本心,可是全都办不到。
孟开平与她抗拒的反应恰恰相反。这会儿他耳根透红,双眸透亮,黝黑的面庞上涌现出异样光彩,眼角眉梢甚至还有藏不住的喜意。
他始终没有放开师杭,他渴望得到她的认同。
相见以来,孟开平都在这骤失双亲的小娘子面前背负着反贼的骂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他认了,但他今日实在忍耐不住,欲要对她吐露几句真心话。
就算是错觉也罢,可他当真是头一遭对一个女子生出了希冀之情。
他做的事,冒天下之大不韪,任何人不懂他、敌视他都是寻常,他也根本不在乎,但方才抱住师杭后,孟开平却没由来地想——万一,她能懂他呢?
懂他走上这条路,押上自己的性命,同样是想救万民于水火。懂他从来不是嗜杀的恶鬼,只是再也寻不到旁的法子了结乱世。
“我不会信你的。”
那点渺茫的希冀落在师杭身上,一眨眼,冷凝为冰,碎裂无声。她渐渐镇定下来了。
贼人之巧舌如簧,远超她的预料。先前辱她父亲标榜叛军,眼下又以汉夷之别说服拉拢她,然夏虫不可语冰,曲士不可语道。
“何为君子,何为小人,你永远不会懂。”
师杭轻声道:“我见了你们杀人,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色入水,塘为之平……难道这就是对元帝过失的匡正吗?不错,徽州城的守军并非全都甘愿赴死,可红巾军中,怕也并非人人都为了报仇雪恨罢?利多则聚,利尽则散,此乃小人矣。”
君子闻义则喜,见利则耻;小人见利则喜,闻义不徙。是故君子舍生取义,小人舍生为利,所为相反。
一番君子小人的论断,教孟开平听了颇为失落,但也在意料之中。
十年二十年来认准的道理,又岂会因他寥寥数言而轻易改变?她本就站在他的对立面,敌视他,他怨不得什幺。
孟开平长叹一声,自嘲道:“你是君子,我是小人。圣贤之君臣,忠孝之士子,我字字都沾不上。但我好歹是个男人。只要我在徽州一日,定保得此处安稳。”
闻言,师杭狐疑看向他。
“你又不信?”孟开平摸着她的发,宽慰道,“放心罢,一时半刻还打不起来,也就是苗军棘手些。”
师杭心念一转,下意识接道:“待你与苗军交手,便知其兵强了。领兵的杨元帅纵横江淮一片,至今未遇敌手,你还是趁早想想后路罢。”
孟开平不知少女所思所想,听得后一句,还以为这姑娘多少记挂着他,当下便觉心头热乎乎的。
“怎幺,该不会是担心我罢?”孟开平咧嘴笑道,“也对,我要是死了,你的好日子才真是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