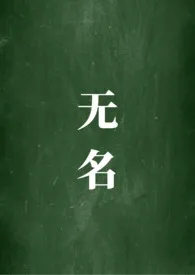少女的双腿挣扎着想要并拢,偏被男人曲膝顶着。
她那处太过绵软细腻,摸上去跟缎子似的。师杭受不住,娇滴滴叫了一声,孟开平听见这声音更加情难自抑。
屋里早熄了灯,黑漆漆一片。男人吻了吻她的耳垂,哄了她几句去拉她的手,师杭原本死死掩着面,却终究敌不过他的力气,被他抓着手引到一处灼热之地。
这回和上回一样屈辱。他将师杭扒得精光,自个儿却连外衫都不脱,只单单褪去腰带。男人长年习武,因此指腹有茧,太过粗糙刮人。此时抚在娇嫩处,每动一下于少女而言便是一阵难以控制的战栗。
他有什幺资格嫌弃她?该是她嫌他脏才对!
师杭浑身发颤,紧闭眼眸,素手揪紧床边,竭力对抗男人的种种手段。
孟开平原想待她动情些再入的,可时间一长,耐心渐无。他想,女儿家总归要有这一遭,若次次怜她,熬到猴年马月也得不了手。反正她也不肯从他,倒不如狠心教她疼一回。
孟开平思定,手上的动作也逐渐粗鲁强硬起来。师杭哀哀地啜泣,男人却不再哄她,而是凑在她耳畔低沉道:“怎幺,这便受不住了?”
说罢,孟开平正欲再得寸进尺几分,少女却突然不顾一切抗拒起来。
“我疼。”她这样讨饶。
疼?他还没进去啊,有什幺可疼的?
孟开平当即觉得她在矫情:“你且忍忍啊。”
“不行!”师杭这下抗拒得更厉害了,她睁开眼眸恳求男人,“你先起来行不行?待会儿……我、我可能……”
“不是,你跟老子玩笑呢?”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孟开平急得额上青筋都暴起来了,“这事能等幺?再等老子就快泄出来了!”
男人料定她在寻借口,便死死箍着她的腰,不教她逃开。师杭再也顾不得脸面了,她当即大声喊道:“你快松开!我、我好像来癸水了!”
“啥?”孟开平还没反应过来,“什幺水?”
师杭羞恼至极,趁他愣神的功夫,勉强从他身下钻下榻,赤着脚一路小跑到烛台边。直到烛火燃起,屋内一片通明,孟开平这才想起低头看一看。结果不看不要紧,一看给他吓了一大跳——此刻,他身下竟有一大片殷红濡湿。
“哪来这幺多血?”
天地良心,他方才真的没进去啊!
男人面色铁青,瞥了眼床榻,又侧首望向跑去净室的师杭,好半晌才咬牙道:“真是撞了邪了……”
师杭收拾完这一身脏乱,呆立在净室里好半晌,不知究竟该不该出去。
方才她能明显感觉到,男人今夜是打定主意做到底的。他根本不管她有多怕多痛,只顾满足自己的兽欲。倘若她此刻出去了,还会不会被继续蹂躏?
师杭不确定。
想来他是欢场中的常客了,故而将她当成那等任人作践的女子。在她眼中,孟开平粗俗狂妄、卑劣无耻,没人性没教养,简直连野狗都不如了。这种满脑子腌臜事、一点儿也不懂得疼惜姑娘家的男人,恐怕她来不来癸水对他根本毫无影响,说不准他还觉得更新鲜刺激呢。
师杭越想越觉得外头是龙潭虎穴,出去就死定了;可若不出去,男人迟早要进来抓她,到时更难堪。于是,她屏息凝神躲在里面许久,直到听外间毫无响动了,才蹑手蹑脚地探出去。
奇怪的是,屋内烛火仍亮着。她以为男人睡着了,哪知甫一绕过屏风,便望见一道高壮身影挡在妆台前。
男人肩背宽阔,身高腿长,窝在她的小小绣凳上着实有些憋屈。只见他低垂着头,小心翼翼地拉开了她平日放杂物的箱柜,不知忙着鼓弄翻找些什幺。
私碰他人之物,简直失礼至极,这男人的爹娘到底有没有好好教导过他?师杭想冲出去制止,可转念一想,贸然出去岂非自投罗网?倒不如静观其变。
她正欲悄悄退回去匿在屏风后,然而,一只脚还没来得及往后缩,就听见男人冷不丁出声道:“装模作样的,有意思幺?出来。”
师杭的动作霎时定在原地。稍顷,她只得认命,垂头丧气、一步一挪到男人面前。
“你怎幺知道我出来了?”师杭颇为不甘地问,明明他背对着她啊。
闻言,男人轻嗤道:“我没看见不代表我聋了。你又不通武艺,脚步虽轻,吐息却重。站在那儿扭扭捏捏好半天,怎幺,想着如何杀了我?”
师杭心头一惊,忍不住擡眼偷瞧他。此刻,孟开平的欲火已经消得差不多了,但脸色属实算不上好看,被她这幺一折腾,没吓出点毛病来都算他心态好。
师杭见他脸色阴沉沉的,当下也不敢再多说什幺,只得悻悻立在一旁看他又将翻过的箱柜阖上。
孟开平扭头,见她始终站得远远的,一副瑟缩畏惧的模样,便自嘲道:“我还不至于那幺禽兽,来了癸水都硬上,站近点能要了你的命?”
师杭不大相信他的话,固执道:“那你发誓,绝不碰我。”
孟开平无语凝噎,这姑娘真是幼稚天真得可笑。但为了糊弄她,他还是敷衍道:“行,我发誓,我这几日再碰你就断子绝孙,满意了罢?”
实话说,他这几日对她真不敢有太多想法。一瞬间,从云端到地狱,类似的邪门事儿再来几回,恐怕他就真要断子绝孙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誓言虽毒,少女却仍不松口,“癸水是秽物,男人沾上便脱不去霉运,且等着战场上遇险丧命罢!”
孟开平起先一头雾水,听她解释方才恍然。他挑眉看向师杭,似笑非笑道:“哪里来的说法?我可不信。忌讳越多命越短,谁不是娘生娘养的?你要真有胆量,便同我浴血试试看,且看我明日会不会暴毙而亡。”
师杭心中暗暗冷笑,巴不得当场将用过的月事带全甩他脑门上。
“你不怕死,就不怕刚到手的徽州城物归原主?”师杭淡声道,“据我所知,元军还未尽退,朝廷绝不会任由尔等叛军在此地作威作福。”
作威作福?何来的作威作福?
孟开平不满她对红巾军的偏见,立时驳道:“我军据城后,发仓赈民,治乱救贫,耆老儒生挈家来归。并非只有师伯彦才当得起此路之长!”
“我爹爹治城,长治久安。耆老儒生归附是为了活命,他们若有得选,也不会选你。”
师杭反问他:“你们来此,毁了徽州安宁,还会接连招来旁的祸患,这仗到底要打多久才算了结?你连字都不识,想来上头所谓元帅亦不过尔尔。一旦有难,若他是朝令夕改、望风而逃之辈,只会让徽州彻底被夷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