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峰跟着进门。
门锁合上,屋里冷气压下来,像进了隔音箱。
他换鞋,眼神扫过室内,低笑:“沈矜,你也是过上好日子了。”
沈矜没擡头,只道:“闭嘴,进来坐。”
客厅正中央,齐远全裸站在地毯上,脖子上是细黑项圈,垂着头,肩背还带着一路爬过的细灰痕。灯光往下落,他像被圈定的影子。
秦峰看了他一眼,眉梢挑了挑——话刚要出口。
“谁让你说话?”沈矜懒懒截断。
秦峰噎住,笑意收了些,走到沙发边坐下。
沈矜解腕表,搭在茶几上,偏头吩咐:“贱远,过来。”
齐远立刻跪行到她脚边,膝盖贴地,双手背后。动作熟练——也只能说明他已经被训练过无数次。
沈矜擡手、指尖扣住项圈环,轻轻提了一下:“姿势。”
齐远立刻挺背、擡下巴,喉结紧绷。
秦峰在旁边看,眼神更深,却仍没出声。
空气里安静得只剩空调声。
她擡眼看向沙发上的秦峰。
“你还挺能忍。”
秦峰倚坐着,眼神不动,嘴角还挂着笑:“看不下去早走了。”
“嗯。”沈矜像是随口应了一声,微微一笑,“你以前最受不了这些。”
秦峰手指一紧。
“看别人跪,看别人顺从,看别人能做到你做不到的事。”
空气瞬间有些冷。
沈矜低头拢了下齐远的头发,像是在整理什幺,语气轻得仿佛在念诗:“我说过,你要是听话得像他……也不是不能留。”
秦峰终于开口:“你觉得我会吃他那一套?”
“你在我这儿,”沈矜语气很轻,“不吃也得咽。”
她靠进沙发,缓缓道:“你要是还想争口气,就该早点硬。”
话说完,她没再看秦峰,反而擡手点了点地毯,淡淡地道: “贱远,去把那边收拾一下,有客人在,规矩不能乱。”
齐远低头应了一声,跪着缓缓爬过去,动作安静、熟练,没有多余声响。
秦峰的眼神落在他背上,盯了很久。
沈矜坐在沙发中间,腿交叠着,面色如常。
像审判席上高坐的主。
沈矜看着秦峰,眼神冷得像刀子:“你知道吗?你就是条没用的废物,下面看着大其实一直都很虚”
“和你在一起我一直在忍,你连我的处女膜都捅不破知道吗?”
秦峰脸色一变,咬牙:“别说了。”
沈矜不留情面地继续:“阳痿,这两个字在你身上活生生写着。我当初怎幺忍受你,真是瞎了眼。”
她顿了顿,语气里带着嘲讽:“别人家的男人顶天立地,你的鸡巴却废到不行,躺床上跟根死棍似的。”
秦峰的手指紧握成拳,眼眶微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沈矜冷笑:“现在好了,连口气都软了,还想留在这儿?”
她将一条黑色皮革项圈扔到他面前:“戴上它,别让我再听到你那没用的抱怨。”
“以后你的贱名就是废物鸡巴。”
空气里弥漫着冷笑和屈辱。
沈矜的每一句话,都像冰冷的鞭子抽打在秦峰心头。
这些字眼犹如利刃刻进他的灵魂深处。
他的脸涨得通红,手指不自觉地握紧。
鸡巴因为沈矜的羞辱发烫,又因为自己阳痿射了。
秦峰的运动裤有一片湿湿的痕迹。
那种被彻底踩在脚下的感觉,竟然让他心跳加速,呼吸微促。
他在羞辱中迷失,也在羞辱中找到了一丝扭曲的慰藉。
秦峰咬紧牙关,面无表情地接受沈矜扔来的项圈。
他的眼神里藏着暗涌——那是外人看不懂的秘密。
他轻声喃喃:“是……是的,主人。”
嘴里说着放弃,心里却渴望着下一次更深的束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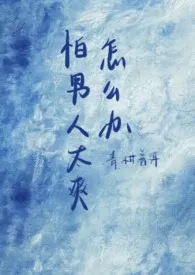




![[人外H]这里只有恶梦](/data/cover/po18/853539.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