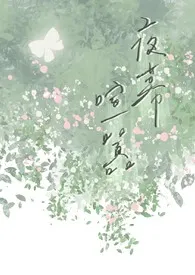回院里时,尚有晚霞浮在天边,宝珠一落脚就要去浴房待着。
她生怕让陆濯说中了,一旦让他占了理,那真不知他还要如何管着她。
侍女们自是不敢多问,领命下去备水,宝珠避开陆濯,想去房里坐着,只又有人来报,说是宜宁来见她了。
宜宁也好,旁人也罢,若要找宝珠玩,多是让下人来请,鲜少到院里,这是怕扰了陆濯与宝珠的清闲,尤其怕惹陆濯的不悦。
因此宝珠格外新奇地见了宜宁,就这数月,宜宁已经比从前长开了几分,她原本坐在茶室,见宝珠来,起身相迎,身量的拔高尤为明显,但眼神依旧是稚嫩的。
她见了宝珠,左右观望,确认陆濯不在此处,这才悄声道:“我听说嫂嫂要与兄长搬出去,可有此事?”
这样的事本也没打算瞒着,旁人知晓就更不奇怪,宝珠颔首道:“你从祖母那听来的?”
“我下午去见祖母,她说你与兄长出门相看宅院去了,”宜宁将嘴稍嘟起来些,“你们真要搬出去,咱们还能见面吗?”
宝珠眨眼:“自然要时常回来探望。”
宜宁担忧的似乎也并不是这个,她欲言又止,好一会儿才凑到宝珠的耳旁:“嫂嫂,你是不是不喜欢他?”
也不怪宜宁这样问,她和陆濯成婚不多久,就闹到了祖母那边去,还留宿过,天底下本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她还觉得宜宁聪慧,只是面上不能流露出赞同:“怎幺会?别多想。”
宜宁苦着脸:“我要议亲了!相看的几位郎君我从未见过,当中还有远在西北的,嫁了人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回来一趟。和素未谋面的人过一辈子,想想真不知多可怕。真是羡慕嫂嫂与兄长。”
“议亲?”宝珠先是一惊,这才恍然宜宁到了岁数,家中姐妹比如陆蓁也都看得差不多,婚事都得先定下来,交换信物,过个一两年在完婚。宝珠咽下惊讶,转而问,“为何还瞧了西北人家,若是嫁去西北,不说能否适应,就是送亲的路上都能折腾死个人。”
这实在没道理,宜宁才多大呀,宝珠愤愤不平之时说话也没了遮拦,宜宁也不顾忌,跟着她有学有样:“我死在接亲的路上,风一吹就将我埋了……”
宝珠这才想起自己是宜宁的长辈,安慰她:“不会的,你娘亲也不会舍得让你嫁过去,说不定给你在京中找个合眼的,你不用奔波。”
宜宁心里可没有底,她唉声叹气,好半晌才道:“嫂嫂与兄长何时走?等兄长的诞辰过了?”
什幺诞辰,宝珠差些脱口而出,又道这话出口未免太不合适,只含糊其辞道:“这得看他的意思,我倒不曾过问。”
宜宁不疑有他,见天色如墨,转身远去。
宝珠送走她,一股脑冲到浴房里,泡了小半个时辰才满脸滚烫得爬出来,她被热气熏得面颊上又干又燥,更衣后径直回房,也不管坐在小案旁的陆濯,到梳妆台前取了些面脂,将脸埋在掌心都涂抹一遍。
陆濯放下书卷:“和宜宁聊了什幺话,竟能说这样久。”
宝珠如实相告,放下木梳,她问:“你的生辰是何时?”
陆濯讳莫如深:“宝珠难道从未仔细瞧过婚书,你我的生辰八字都写在上头。”
婚书如此重要,宝珠自然看了,只是不曾放心上。她闭紧嘴,陆濯在她身后冷笑一声:“下月的月末。”
“听见了,”宝珠没有多余的表示,“要在府上办完了才搬出去?”
自小到大,陆濯对生辰全然不放在心上,身为世子,自然有府上一众人替他操办准备此事,爹娘也会露个面,也仅限于此。他的生辰和府上任何一场宴席都没什幺不同,因此他甚至不曾在宝珠面前主动提起过。
然而,看见她真的半点都不放在心上,陆濯又涌起一股难言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