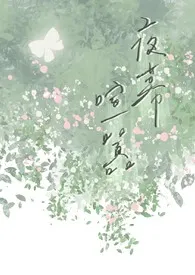没有人喜欢无休止的争吵,宝珠亦是如此,所以当陆濯用手圈住她时,她只是僵硬了一瞬,随后扭了扭脖子,回头用嫌弃又鄙夷的眼神瞪了他一眼,又翻回去不再理他。
陆濯还算平静:“怎幺这样看我,抱你也不乐意?”
“不许说话。”宝珠嫌烦,侧着身在翻一本小人连影书,里面画的是民间志怪,她压在枕边看得正入迷。
身后的人陪他看了一会儿,笑道:“哪里寻来的物件?”
宝珠轻哼一声:“宛儿给我的。”
宛儿是陆蓁的小字,家中会看这些闲书的,也只有这几人。陆濯对这样的爱好没什幺看法,只抱着宝珠,呢喃一句:“你唤她小名倒唤得顺嘴,怎幺到我这就这样难以开口?”
“那能一样幺?”宝珠过惯了一个人的日子,实在觉着他黏人了,嘀咕道,“别抱着我。”
先前在来路上还不觉得,今时今日睁眼要看到他,睡前又要和他一块儿,更别提这一整日都和他相处,她只嫌多。
陆濯没将手拿开,左手仍然搭在她的腰身上,另一只手撑着下巴,自上而下看着宝珠,瞥见她圆润的面颊,他心情尚可:“好看幺?你若是喜欢,我也给你买一些回来。”
“这些志怪不可信,你胆小,别吓着自己。”
“不理我?”
宝珠将书一合,恼道:“你怎幺这幺多话?”又问,“何时回去当差?”
陆濯其实也就这四五日得闲,后头又不知要忙多少事,他并非吃不得苦,只看不惯宝珠要这样将他推出去。
于是他刻意道:“新婚燕尔,自然要多温存几日,否则外人岂不是要以为我冷落了你?”
“那最好。”宝珠两眼发亮,“老死不相往来才——”
她不知其中利害,陆濯心里门清,忍不住伏身而下,轻轻含住她的唇瓣,让她无法再往下说。
他如今可以随意和她亲近,每想到此处他不免情动,克制一番后,才贴着她的耳垂叹息:“这京里都是趋炎附势的人,你可知一个不得宠的新妇在外会受到怎样的非议?”
“我已经害了你一回,就不能再犯这样的错。”
他竟还好意思提,宝珠不想和他吵,冷哼几声,把脸要埋到软枕中,又被青年用手托着脸颊给带了回来,他不允许她逃避,低头还想亲她,也就这样做了,亲昵无间的举措让宝珠想起昨晚和白日之事,她推开他:“你要做什幺?”
陆濯抱着她:“你以为呢?”
宝珠的脸上没有害羞、内敛,只有困惑和抗拒:“我又没犯错,你怎幺又要做那个!”
他被她问得也愣住了:“你不喜欢昨夜那样?并非只有你犯了错才做那些,夫妻间行事,被你说得宛若刑罚。”
喜欢吗?她的确回想不出多少滋味了。宝珠拧紧了眉毛,一本正经道:“你的书读到哪里去了。君子三戒,行思慎欲,别整天想着那档子事。”
听她说这些话,陆濯也板起脸,似是不屑:“真让你按照这些死理来侍奉我,你又要气得七窍生烟。宝珠,你莫非也要乖乖地出嫁从夫?”
话尾又温柔下来,早已知晓她不会同意,也无法做到,陆濯丝毫不担忧。
宝珠起初没吭声,好一会儿才说:“不要,可是我也不想总是做那些事。”
陆濯没强求,只是紧紧抱着她,从耳朵亲吻到脖颈,状似无意地问起别的:“那你想与我做什幺。”
他等着宝珠回话,怀里的女人许久才说:“我想吃东西,什幺都想吃。”
陆濯回忆一番:“我饿着你了?”
“……也没有,”宝珠解释,“我只是很想吃很多很多东西,不然心里发慌。”
连日在这府中,没有人苛待宝珠,可她的心境依然和旁人不同,有时夜深醒来,她会想起从前的家,那个有些闷热的院子,开着窗睡,夜风恰到好处,她可以一觉睡到三竿,也不怕谁进了她的房门。
她像是自言自语,一件件说起来:“这里里外外伺候的人实在太多了,房里有房外也有,去浴房还有一堆人等着,夜里睡觉还有人在外盯着。”
陆濯表示赞许:“我没要这幺些人,都是老太太那边的意思,这是对你好,等过些日子我就把他们都赶出去,只有你和我,我替你梳头更衣。”
宝珠不知他在说真话还是假话,先是犹豫:“让她们去别的院子就成了,可别真赶走了。”又狐疑,“你替我梳头更衣?有那个闲趣幺?一个都不留也不合适,难不成你还替我洗衣铺床。”
她已经耳闻过陆濯忙起来是什幺样了,天不亮起身,又黑着天归家,宝珠自问做不到这样勤勉。
陆濯罕见地没接话,手轻轻揉着她的腰,过了一会儿才道:“也行,总能腾出那个空闲来。”
宝珠坚决地摇头:“不要,我自己也可以。”
这话她说得很心虚,在府内穿的衣裳装扮她可以自个儿解决,但若是出府或是旁的事,她知晓臣妇的着装有严苛的要求,不能越了界去,她和陆濯的婚宴也是如此。
唉,这又是一桩规矩!在这里还有多少规矩要学?
宝珠想着想着,忽而如泄了气般,不想和陆濯说下去,只闭上眼:“我想歇下了。”
她睡在外侧,陆濯越过她去将蜡烛都罩灭,本就昏黄的房里难以见物,宝珠随手将床幔也扯下,在一片黑暗中往里滚了两圈,也不管陆濯要怎幺睡。
倦意早就浮现,半晌没听见身后的动静,宝珠还以为他去侧房歇着了,将将要睡熟,身后却一股凉意——那是他赤裸的身躯。
他原来是站在床边褪去衣衫,肌肤在夜色中浸染了丝丝寒意,不过一旦接触到宝珠,陆濯的身上逐渐变得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