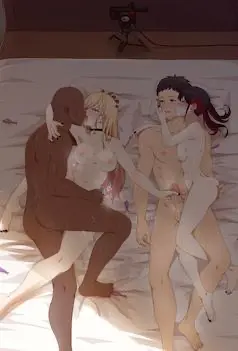刚一踏上那冰冷的水泥天台,晚风兜头灌来,带着点灰尘和远处城市的暖热尾巴。一个人影就靠在蓄水池的阴影边上。
是麦穗。
路灯的光还没接管这片区域,昏蒙蒙的,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上半身裹了件宽宽大大的藏蓝色连帽卫衣,袖子撸到手肘,露出线条绷紧的小臂。
那卫衣下摆只到大腿根,两条麦色的、紧实修长的腿光溜溜地戳在凉嗖嗖的空气里,晃得人眼睛发烫——果然是超短裤,布料少得可怜,藏在那卫衣下面,根本看不见,光剩下腿了。
“默哥!”她像只被按了启动开关的弹簧兔,眼睛唰一下亮得惊人,瞬间驱散了那点昏暗的影子。
还没等我站稳脚跟,她已经带着一股子扑面的风冲了过来,不是跑,是直接扑!
带着体温的暖风混杂着点干净的皂角味和刚出浴的水汽,咚地一下撞进我怀里。
双臂跟铁箍似的,死死勒住我的腰,那劲儿大得像是要把我揉碎了按进她胸口那团隔着卫衣也弹性十足的温热里。
“还以为你不来了!”她把脸闷在我肩膀上蹭了蹭,声音透过布料传出来,嗡嗡的,有点抖,更多的是压抑不住的兴奋劲儿。
我的心口被她撞得咚咚响,鼻尖全是她颈窝里清清爽爽的味道,混着点刚洗完澡没散尽的水汽,还有……一股子不管不顾的蛮横气。
“万穗爷的威胁,谁敢不听?”我喉咙有点发干,回了一句,试图找回点“好兄弟”的调调,可手也不知道该往哪放,悬在她汗湿的卫衣后背上。
她从我怀里退开一点,仰着脸看我。天台的光线暗,看不清她脸上红没红,但那双眼睛贼亮,跟夜里的探照灯似的,直勾勾地钉在我脸上。
刚才那股疯劲儿忽然敛了,变得有点小心翼翼的。
“沉默……”这次没叫“默哥”,连名带姓,生疏得像是在做最后确认。
“那天……巷子里说的……你喜欢不喜欢我……我不管。我就想问问……”她吸了口气,胸口起伏明显,“你心里头……有没有那么一点点……是喜欢我的?”
她的声音不大,被风吹得有点散,但每个字都砸得我耳朵根子发麻。
“就一点点,”她伸出小拇指,比划着指甲盖大小的意思,固执地盯着我的眼,“不用骗我,也甭勉强。我就想知道,你看着我跑过来,我背我回家,看我抢你排骨的时候……烦我了吗?还是……哪怕就一丁点,心里是高兴的?”
我的嗓子眼像是被一把糙砂子堵住了。脑子里嗡嗡的,全是那个该死的【好兄弟】标签,硬邦邦地悬在那儿。
操,系统,你他妈玩我呢?这演的是哪出好兄弟啊?跑我怀里来了?腿还露这么多……
时间像是被风吹凝固了。
几秒钟的沉默,在凉飕飕的天台上,漫长得像过了几个冬天。
麦穗眼底那点微弱的光,随着我的沉默,一点点地黯了下去。
扯了扯嘴角,像是想笑,又没笑出来,变成了一丝极其难看的、带着点自嘲的弧度。
她猛地吸了下鼻子,好像要把风灌进肺里去,声音陡然冷硬起来,带着那种我熟悉的、像要掩饰什么的粗鲁气:“得了!明白了!算老子多嘴!你……”
话没说完,她扭身就要走。动作快得像一道影子,带着一股豁出去的决绝,那条光溜溜的腿在昏暗里白得晃眼。
身体比脑子快。
就在她肩膀和我错开的刹那,我的手已经伸出去,啪一下攥住了她的手腕。
冰冰凉,底下是剧烈跳动的脉搏,一下下撞着我的指腹。
“……喜欢的。”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跟破锣一样干涩,从喉咙深处硬挤出来。
麦穗整个人像被按了暂停键。
猛地刹住脚步,身子僵在原地,只有被我攥着的那只手,在微微发抖。
她一寸寸,极其缓慢地扭过头,侧脸在昏蒙的光影里,紧绷得能看到咬紧的牙关。
“……真的?”两个字从她牙缝里挤出来,带着浓浓的怀疑,还有一丝怕破碎的小心翼翼。
晚风吹得她额前短碎的蓝紫色发丝胡乱扑闪。我看着她的眼睛,那片刚才熄灭的黑,又被新的什么东西点燃了。
我喉结狠狠一滚,像是要把那句话凿实了钉死:“真的。”
话音刚落,她人已经撞了回来。
这一次比刚才那次更凶更急,像颗炮弹直直砸进我怀里。
那股肥皂香和水汽混着她骤然升高的体温,把我整个儿裹住。
我本能地抱紧她,那截卫衣下光裸的腰肢在我掌下滑腻又带着韧劲,肌肤的热度透过薄薄一层布直接烙在我手心。
她根本不给反应时间,滚烫的脸颊在我下颌处蹭过,带着股不管不顾的蛮劲。
然后,踮起脚——她的身高在女生里拔尖,但此刻还是差那么一点儿——温软的、带着点急切颤抖的嘴唇,就这样笨拙地、毫无章法地堵在了我的嘴上。
磕了一下,有点疼。
像块刚融化的水果糖,又甜又软,但裹了一层青涩慌张的硬壳。
她大概是憋着气的,亲上来就知道啃,湿热的唇在我唇瓣上碾来碾去,有点疼,又有点麻。
小巧的鼻尖抵着我的脸侧,急促滚烫的呼吸扑打着皮肤。她想撬开,又不得其法,只会用牙齿在那较劲,跟小兽似的,又凶又傻气。
太糙了。
我心想,脑子有点飘忽。
这丫头平时那股凶巴巴的冲劲儿全用在较劲上了。
腰上手臂的力道没松,另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滑上去,按在她微微汗湿的后颈窝,有点冰。
指尖下的皮肤瞬间绷紧。
“傻子,憋死谁呢……”我含糊地说,嘴唇动了动,微微分开一丝缝隙,却没让她退开,反而引导着,舌尖极轻地在她紧抿的唇缝上扫了一下,像安抚一个炸毛的小动物,“……喘口气儿……对……张嘴……”
麦穗身体猛地一僵,随即像是得到了某种神秘指令,那双紧勒在我腰上的手臂又紧了紧,像是生怕我跑了似的。
喉咙里发出一声模糊的呜咽,唇瓣微微松开一条缝儿。
一股甜丝丝的、带着她独特气息的热息涌出。我没再犹豫,带着点不容置疑的力道,压了回去。舌尖抵开那道松动的门禁,探了进去。
里面温热湿润得不像话,却像个被突然闯入的迷宫,舌尖毫无方向感地碰到她的牙尖,那点坚硬硌了一下。
她像是触电一样猛地又想把嘴合上,身体在我怀里筛糠似的抖。
按住她后颈的手用了点力,掌心下滚烫的皮肤和紧绷的肌肉传递着混乱的信号。
“……别咬……”我含混地警告,呼吸也变得浑浊不堪。
她喉咙里发出模糊的鼻音,像放弃了抵抗,又像在呜咽。笨拙地想回应,舌尖怯怯地,试探地碰了碰我的。
柔软湿滑,带着点她晚上可能吃过的橘子硬糖的甜腻。
像含住了一块正融化的跳跳糖。
我来回勾缠、逗弄、含吮着那笨拙的舌尖,耐心地教她一点点退让、纠缠。
每一次缠绵的搅动都换来她喉间溢出短促的气音,身体在我怀里越来越软,绷紧的肌肉像雪糕那样融化。
缠在我腰上的手臂也松了力道,滑下来,虚虚地挂在我脖子上,掌心汗湿滚烫,贴着我的后颈皮肤。
喘息声越来越重,不是我一个人的,是交缠在一起,湿漉漉的,在晚风里又闷又烫,粘得化不开。
她身上那股阳光暴晒后的青草香混合着她本身的汗味,还有卫衣布料摩擦产生的热烘烘的气息,彻底将我包围,像陷进一个甜腻滚烫的沼泽。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几十秒,我感觉她整个人都要软成一滩水了。
抵在她后背的手指能清晰地摸到蝴蝶骨剧烈的起伏频率。
我慢慢地、一点点退了出来,结束了这场黏腻的缠斗。
最后一下,舌尖划过她的上颚,惹得她一阵剧烈的哆嗦,哼声像小猫一样。
唇瓣分开时,发出细微的“啵”的一声轻响。
麦穗几乎站不住,整个人挂在我胳膊上,胸膛剧烈起伏,大口大口地喘气。
黑暗中,那双眼睛像是被水洗过,蒙着一层雾气,亮得惊人,又带着点劫后余生般的迷蒙。
嘴角亮晶晶的,挂了点我们俩糊上去的湿痕。
她喘匀了几口,眼神飘忽着不敢看我,舔了舔自己湿漉漉、红肿发亮的嘴唇,那动作带着点不自觉的勾人劲儿。
然后,抬起一只滚烫的手背,胡乱蹭了下嘴角,声音哑得不成样子,带着点狐疑和别扭的醋劲儿:
“操……沉默你……你怎么这么会亲啊?”她的手指头戳在我胸口,带着点力道,像是质问,“是不是……跟苏晚棠……练过?嗯?”
那点“练过”的尾音扬上去,像把小钩子,酸溜溜的。我心口猛地一跳。
幽暗天台的阴影,一瞬间变成了狭窄卫生间的潮湿逼仄,变成了幼幼裙摆下惊慌失措的嫣红……喉咙有点发干。
“……嗯。”我看着她那双在昏暗光线里依旧灼亮的眼睛,点了点头,承认了这个方便又该死的误会。
麦穗眼里的雾气瞬间凝成了冰碴子,刚才那点柔软的迷蒙全被一股子凶狠的占有欲顶替了。
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又像是要夺回地盘的小兽。
“我就知道!”她咬牙切齿地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带着股豁出去的蛮横劲儿,眼神凶狠得能把我吃了。
下一秒,她猛地拽低我的脖颈,那卫衣领口蹭着我的下颌。
滚烫的、还带着急促喘息的唇再次蛮横地覆了上来!
这一次不是试探,是纯粹的攻城略地。
带着一股青涩的狠劲,毫无章法地吮吸碾压,舌头直接冲撞过来,急哄哄地舔舐着刚才我们纠缠时留下的所有痕迹。
她在笨拙地模仿刚才我引导她的节奏,像是在宣告什么主权,胡乱地追着我的舌头缠绕,又啃又咬,热息和唾液混杂着橘子糖的甜腻气息更加汹涌地交换。
呼吸再次被迫中断,肺里烧得发慌。下巴被她咬了一下,有点疼。
我反手抱住她,托着她的后脑勺,更深更用力地回应回去,把那乱七八糟的抗议都堵死在一片湿热的纠缠里。
手掌在她只被薄薄卫衣包裹的脊背上游移,感受着那层布料下紧绷又汗湿的肌肤,还有她腰窝那紧实诱人的凹陷。
直到她又快把自己憋晕过去,才猛地把头后仰挣脱开。
“哈——啊——!唔……”急促的喘息声撕裂了天台粘稠的空气。
晚风吹得人一激灵,刚才还滚烫的唇舌纠缠像被泼了盆冷水。
麦穗喘着粗气从我怀里退开一点,那双亮得惊人的眼睛在昏暗里直勾勾盯着我,里面翻腾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着疑虑和强烈占有欲的情绪。
她胸口还在剧烈起伏,汗湿的卫衣领口歪向一边,露出一小片被热气蒸出粉色的锁骨。
刚才那个凶狠又笨拙的吻,耗尽了她最后的氧气,也像是耗尽了她所有的伪装。
她舔了舔自己依旧红肿发亮的嘴唇,指尖无意识地揪着宽大卫衣的下摆,指节用力到发白。
“沉默……”声音有点哑,还有点抖,不再是刚才那种“万穗爷”式的咋呼,里面裹着一层不安,“……苏晚棠……她……”
她吸了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眼神锐利起来,“……你们有没有……做过?”
我被她问得一愣,脑子里还沉浸在刚才的湿吻余韵里,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她所谓的“做过”指什么:“什么?”
她没说话,眼神直直撞进我眼睛里,里面烧着一种孤注一掷的火。接着,就在我愕然的注视下,她那只揪着衣摆的手,猛地向上一掀!
宽大厚实的藏蓝色卫衣下摆瞬间被掀到腰间!
仿佛被一道无声的霹雳击中,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整个人彻底僵住。
月光吝啬地洒下来几点斑驳光晕,正好映照出那片骤然袒露的风景。
没有预想中的超短裤边缘。
什么都没有!
两条在昏暗光线下依旧显得麦色健康、线条紧实的腿笔直地向上延伸。而在那双腿交汇的隐秘三角地带……
杂乱!浓密!带着点野性的、深色的阴毛,如同未经修剪的野草肆无忌惮地生长着,被汗水濡湿,一缕缕地紧贴在微隆的耻丘上。
几颗晶亮的水珠顺着蜷曲的毛发滑落,在暗淡的光线里闪着诱人的光。
更惊心的是,在那片浓密森林掩映之下。两瓣饱满、粉嫩、紧紧闭合着的花唇,此刻微微濡湿着。
一丝清澈的、透明的黏液,正缓缓从那道隐秘的缝隙深处渗出,顺着微微分开的内唇边缘,极其缓慢地,极其粘稠地,拉出一条细长的银丝,最终不堪重负地滴落——
“嗒。”
极其细微的一声轻响,砸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那滴小小的、在月色下反着微光的液体,落点清晰。
空气里原本弥漫的卫衣皂角味和汗味,瞬间被一股崭新的、湿润的、带着淡淡青草涩味又隐约透着点成熟甜味的,属于她的独特气息强势盖过。
浓烈得让鼻腔发麻,直冲脑髓。
操……我脑子一片空白,感觉喉头被什么东西死死扼住,眼睛钉在那片黑暗中无比刺眼的鲜嫩湿亮上,动弹不得。
麦穗死死盯着我的反应,紧绷的身体在我瞬间的失神和难以掩饰的震惊中,像是得到了某种确认,骤然松弛下来。
那点之前的不安和凶狠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破釜沉舟的坦然,甚至带着点“瞧见了吧”的得意。
“哈……”她竟然低低笑了一声,带着刚刚剧烈喘息后的沙哑和一种奇异的轻松,“果然没有。”
下一秒,她的声音拔高了几分,干脆利落,没有任何犹豫,字字砸进我耳朵里:“来,跟我做!”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把,然后又被猛地扔回到疯狂搏动的胸腔!全身的血液都喧嚣着冲向下腹。
“麦麦。”我没叫她“万穗爷”,声音干涩得厉害,连自己都觉得陌生,视线艰难地从那片湿漉漉的风景拔起,对上她灼亮的眼睛,“你……是认真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她迎上我的目光,没有丝毫闪躲,像一头锁定目标的母豹子:“是!”
“不后悔?”我的视线下意识地又扫过那片袒露的野性地带,口干舌燥。
“不后悔!”她斩钉截铁,下巴微微扬起,“我喜欢你沉默!我要抢在她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