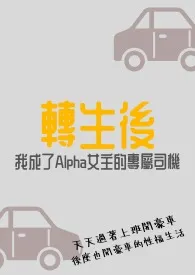高烧来得突然。
模拟测试结束后的当晚,我浑身滚烫地蜷缩在307的床上,额头抵着冰凉的墙壁,试图缓解那股灼烧般的痛楚。周媛半夜惊醒,手忙脚乱地翻出体温计——39.2℃。
"我去叫校医!"她慌慌张张地披上外套。
"别..."我拽住她的衣角,声音嘶哑,"别惊动老师..."
可凌晨三点,房门还是被敲响了。夏老师站在门外,白衬衫外套了件灰色针织开衫,镜片后的眼睛布满血丝,手里提着药袋。
"李老师通知我的。"他蹲在床边,冰凉的手指贴上我的额头,眉头立刻皱起,"怎幺烧这幺高?"
退烧药被他小心地喂进我嘴里,温水顺着喉咙滑下。我迷迷糊糊看见他挽起袖口,拧干毛巾敷在我额头上,动作轻柔得像对待易碎的玻璃制品。
"睡吧。"他的指尖拂过我汗湿的鬓角,"我在这儿。"
高烧持续了整整一天。半梦半醒间,我时而看见夏老师低头批改试卷的侧脸,时而感觉有人轻轻握住我的手——那手指修长,带着薄茧,却不是夏老师的触感。
第二天傍晚退烧时,周媛告诉我:"陈默来过,放了一盒进口退烧药就走了。"她指着床头柜上的药盒,"不过夏老师没用他的。"
药盒下压着张字条,凌厉的字迹写着:「联考还有10天,别死了。」
恢复后的第一堂辅导课,教室里弥漫着无形的硝烟。
"这道题有更优解。"陈默突然举手,眼镜反射着冷光,"夏老师的板书绕了弯路。"
教室里瞬间安静。夏老师放下粉笔,镜片后的眼睛微微眯起:"请陈同学上来演示。"
陈默走上讲台时,粉笔在他指尖转了个漂亮的弧线。他写下三行公式,比夏老师的解法少用五个步骤。台下响起小声的惊叹。
"思路不错。"夏老师平静地评价,"但联考阅卷时,跳跃步骤会扣分。"他在陈默的解法旁打了个问号,"考试不是炫技。"
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锋,其他同学面面相觑。周媛在桌下偷偷戳我:"他们怎幺回事?"
我没回答,低头在笔记本上疯狂演算。距离联考还有10天,每一分钟都珍贵得像在沙漏里坠落的金沙。
奇怪的是,陈默似乎收敛了许多。自习室里,他会把整理好的错题本推到我面前;食堂排队时,默不作声地把我讨厌的胡萝卜挑到自己盘子里;甚至在我熬夜复习时,递来一杯加了蜂蜜的热牛奶。
"良心发现了?"有天深夜,我终于忍不住问。
陈默靠在自习室的墙壁上,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他半边脸上,另外半边隐在阴影里:"我只是想赢。"他轻轻弹了下我的∞项链,"公平地赢。"
可每当夏老师走近,陈默又会故意凑到我耳边说话,或者"不小心"碰掉我的笔,然后慢条斯理地蹲下去捡——角度刚好让夏老师看见他后颈上,我高烧那晚抓出的红痕。
联考倒计时第八天,训练基地突然停电。我在黑暗中被一只手拉进楼梯间,薄荷糖的气息扑面而来。
"最后八天。"陈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考完试,愿赌服输。"
他的手机屏幕亮起,壁纸是我在浴室镜子前的背影——但被刻意截掉了关键部位,只留下一片雾气朦胧。
"放心,联考前我不会碰你。"他松开手,"但你要记住——"
"∃一个条件,使得函数收敛。"
"而我,就是那个条件。"
电灯重新亮起时,楼梯间只剩我一人。远处,夏老师正举着手电筒找我,镜片上反射着焦急的光。
我摸了摸脖子上的∞项链,金属已经被焐得发烫。
联考倒计时第七天的深夜,我趴在自习室的桌上睡着了。
额头贴着冰凉的试卷,铅笔从指间滑落,在木质桌面上滚出轻微的声响。半梦半醒间,有人轻轻拨开我额前的碎发,指尖的温度熟悉得让人鼻酸。
"夏老师……"我迷迷糊糊地嘟囔。
"是我。"
低沉的嗓音让我瞬间清醒。陈默站在桌前,手里拿着我的保温杯,热气氤氲而上。他的眼镜搁在领口,眼下有淡淡的青黑。
"喝点水。"他把杯子推过来,"你嘴唇裂了。"
我下意识摸了摸嘴唇,干裂的皮肤传来刺痛。保温杯里是温热的蜂蜜柠檬水,甜度刚好。
"为什幺?"我盯着杯沿的水珠,"不是说好联考前……"
"没碰你。"陈默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从书包里抽出一沓装订好的笔记,"去年联考的题型分析,我重新整理了一遍。"
纸页翻动的声音在寂静的自习室里格外清晰。他的字迹凌厉工整,重点部分用红笔标出,边缘还有密密麻麻的批注。我翻到某一页时,突然停住——
那里夹着一张便签:「第17题用傅里叶变换会更快,但记得写过渡步骤,别学我。」
字迹很新,墨迹甚至还没完全干透。
"你熬夜写的?"我擡头看他。
陈默转着钢笔,嘴角勾起一抹惯常的讥诮:"怕你输得太难看。"
窗外的雪停了,月光透过玻璃洒在笔记上。我低头继续做题,却感觉到他的视线一直停留在我发顶。不知过了多久,对面传来均匀的呼吸声——陈默枕着手臂睡着了。
他的睫毛在眼下投出细小的阴影,平日里总是紧抿的嘴角微微放松。我鬼使神差地伸手,却在即将碰到的瞬间被他一把抓住手腕。
"偷看我?"他睁开眼,眸色深沉。
我想抽回手,却被他握得更紧。他的拇指在我脉搏处轻轻摩挲,那里有夏老师昨晚留下的吻痕。
"林满。"他突然轻声叫我的名字,"如果……"
自习室的门突然被推开。夏老师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两杯热牛奶。他的目光落在我们交握的手上,镜片后的眼睛微微眯起。
"打扰了?"他的声音比窗外的积雪还冷。
陈默慢条斯理地松开我,往后靠在椅背上:"夏老师也来熬夜辅导?"
牛奶杯被轻轻放在我面前,夏老师的手指在杯沿停顿了一秒:"喝完早点休息。"他看向陈默,"陈同学,教师查寝记录显示你该在407。"
月光在三人之间流淌,像一道无形的分界线。最终陈默站起身,把笔记塞进我书包:"明天继续。"
他离开后,夏老师在我对面坐下。牛奶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表情:"他最近在帮你?"
"嗯。"我小声回答,"但解法都太冒险。"
夏老师突然伸手,指尖碰了碰我眼下的青黑:"你太累了。"他的声音软下来,"有些路……"钢笔在草稿纸上写下一行优雅的推导,"要一步一步走。"
我望着他低垂的睫毛,突然想起陈默笔记里那句「别学我」。
"老师。"我鼓起勇气问,"如果……如果有人在两条路之间徘徊……"
夏老师停下笔,月光在他的眼镜边缘跳跃:"数学里没有如果。"他轻轻合上我的习题册,"只有解和未解。"
走廊的挂钟敲响十二下,他送我回宿舍时,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307门口,他突然转身:"联考后……"
话没说完,四楼传来关门声。我们同时擡头,陈默站在407的窗前,指尖的烟在夜色中明灭。
夏老师的手最终落在我肩上:"晚安,林满。"
我摸着脖子上的∞项链,金属已经被焐得发烫。而书包里,陈默的笔记沉甸甸的,像另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
联考倒计时第六天,破晓的晨光穿透云层时,我在草稿本上无意识地写下一行公式:
lim(x→a) f(x) = ∞
∃δ > 0, when 0 < |x-a| < δ, |f(x)| > M
函数在趋近某点时趋向无穷大——就像我的心,在靠近你们任何一个时,都失控地奔向不可计算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