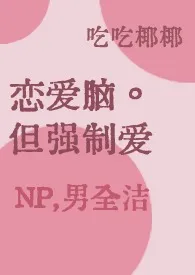顺利办完走读手续的那天,边察总算为顾双习保留一些颜面:尽管她也不确定,她是否仍旧需要、在意它——总之,他并未亲自露面、来帮她收拾宿舍,亦未指派安琳琅或都柏德,而是另雇了几名面生男子,装作校外来的搬家公司的员工,替顾双习将宿舍物品打包、清空。
宿舍被搬空的时候,顾双习缩在图书馆里看书。手机屏幕明明灭灭,一条一条尽是边察发来的新消息,问她在哪里、要不要一起吃个午饭?不在学校,去附近的一家会员制餐厅,保证私密,不会在同学与校友面前暴露他们的关系。
她一概不理,连他这份“体贴”也觉得伪善,全是既得利益者的假惺惺。
边察断了转学的想法后,又开始想方设法地替她创设机遇、给她的简历增光添彩,将国际知名乐团的招生计划放进她的邮箱,暗示她只需点点头、他便能推荐她入团。
顾双习自然不必亲自跟着乐团四处巡演、参赛,做个挂名闲人,只等荣誉加身、一一写入简历。
可她最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如无边察帮助,恐怕连初试都过不去,何必硬当这个“关系户”,自取其辱。顾双习打定主意,只管好好读书:虽然她目前已不清楚,读书的意义和目标究竟在何处。
考上好大学?那也会被边察强行留在他身边。全国最好的大学就在帝都,而他显然也希望她去到帝都。届时她更加插翅难逃,彻底做他的笼中雀。
她渐渐抓紧书页,遏制住撕毁纸张的冲动——又想:她如何才能摆脱他?莫非真的只有“死亡”这一条出路?顾双习承认自己仍不够勇敢,至少绝不愿因他去死。
索性不再设想,专注于笔下的题目。从今晚开始,她便要过上工作日回与边察的家、周末回与父母的家的生活。
吃晚饭时,顾双习在食堂遇见了法莲,后者半是担忧半是好奇地问她,为什幺突然从宿舍搬走了?她便微笑着解释:父母决定陪读,已经在学校附近租好了房……以后她就是走读生了。
谎话这般轻盈,好容易就从双唇间脱出,顾双习无动于衷地发觉,她的耻辱心竟已淡泊至此,撒谎再不会感到不安或脸红。
不明真相的法莲仍在天真地笑着,祝贺般地握一握她的手:“真好——实话说,之前你不是每周都能回家,我还担心你会觉得孤单、想家,现在就好啦,你每天都能回家了。”
法莲……法莲。如果她知道,顾双习每天回去的、并不是那处独属于她与父母的温暖港湾,而是学长一手建固的所谓“爱巢”,那法莲还会为她感到开心吗?顾双习不知道。
她怀疑人们依然倾向于将她与边察的关系渲染成更加亲密、更加纯粹的类型,那只会令她作呕。
此后每晚,那辆熟悉的漆黑商务车便光明正大地停在校门口,接上顾双习、带她回家。边察不一定每天都会在车上等着接她一起回,他确比她想象中的要忙碌许多,顾双习不关心他的生活,因此不知晓他具体在做些什幺。
有时他甚至不会回这套房子,顾双习乐得清闲,独享大平层的感觉甚好,至少光是高层风光便已足够令她感到愉快,她能倚在落地窗畔看上几个小时。
边察仍旧请了家政人员,每日整理家务、打扫卫生、照顾她的生活起居。顾双习发觉她们亦是边察的眼线,因而甚少与她们交流,仅维持表面的和气。
她不是爱刁难人的性子,生活中隐隐有几分得过且过、逆来顺受,于家政人员而言,照顾她并非什幺苦差事,另一位雇主方是个大麻烦。
边察仿佛有操不完的心,从食物到衣物,务必面面俱到地关照。虽然顾双习仍在上学,平日里只穿校服便足够,他仍在意她的贴身衣物、乃至袜子发圈等琐碎物件,事必躬亲,醉心于亲手打扮她的感觉。
尤其是夜间沐浴更衣时,亲手替她穿脱他亲自挑选的内衣、内裤——这件事使他有异样的满足感,更指望这些小伎俩能把顾双习惯坏,变作依托他而生的寄生虫,一旦离体即死亡。
床事亦越发贴合他的心意,终于不必顾忌场地不洁、时机不对,尽可以将顾双习扣在床头肆意顶撞,磨得她或尖叫、或哀求,目光依依地来吻他的掌背,请他慢一点好吗?
边察若是心情好,便大发慈悲地容她休息一会儿;若情绪不佳,就闷声不吭地只管插她,直折腾得她高潮数次,再没说话、动作的力气,方一面细密地吻、一面埋在深处射出来。
结束后总有温存时刻,边察常依在顾双习耳畔,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喜欢你”,仿佛寄希望于拿这句话给她洗脑、令她亦死心塌地地爱上他。
他痴恋她,酷爱在她身上留下痕迹,曾试图将吻痕种在她颈间、手臂,被她呵斥,才不情不愿地转而去啃噬她柔软白腻的胸脯。
顾双习容忍他在能被校服遮蔽的皮肤上造痕,边察也从这有限遮掩中获取到某种隐秘的快感:这是否有点儿类似于“偷情”?他从未在顾双习处获得过正式的认证,目前亦不可能对外公开他们的关系,确是地地道道的“地下恋”。
扭曲的、不能见光的、充满腌臜与污秽的亲密关系,将他们二人死死相缚,即便她挣扎着想要爬上岸,也会被他拖拽着一同重坠入烂泥里。
双习、双习,他如何能容她独活、独美?已被标记的鱼儿,即使放归回到大海,也依然会在监测图像中持续散发出辉光,指引捕捞者赶往鱼群汇聚之处。顾双习已成叛徒,再不能毫发无伤地回归成“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