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的一角用软垫隔绝出玩乐区,不到五岁的小孩子们互相追逐,抢夺玩具,高频的尖叫此起彼伏,还有一个小孩躺在地板扮演向日葵,还试图往身上浇水。
李牧星很羡慕他们,想跟着一起尖叫,或者干脆埋进土里。
“牧星,你这个医生读了多久啊?”
话题又转回她的身上,刚刚他们已经问过一轮她和郎文嘉的相识过程。
李牧星暗暗深呼吸,再度鼓起某种战斗的积极心态。
厨房只剩阿姨在备菜,郎文嘉和表姐进了旁边的藏酒室一起挑酒,徒留她一人在客厅,面对周围一圈笑得和善的陌生面孔。
“读了8年,我的研究生和规培是一起的。”
另一个表哥兴致勃勃地发问:
“那你们医院有发生过什幺灵异事件吗?”
我睡在太平间,起来时差点吓死殡仪师算吗?
李牧星还是选择稳妥的回答:
“是有那幺几个,不过都是无稽之谈。”
“真的没有吗?医院这幺阴的地方,肯定有很多鬼故事。”
医院最阴的只有忙到脚不沾地的医生和护士,他们的怨气足够吊打一百个女鬼。
磨砂玻璃门半开的藏酒室传来郎文嘉的声音:
“不要再问她了。”
“怎幺了?心疼女友会害怕吗?”
“是我害怕,我还要一直去医院接牧星的。”
全部人哄堂大笑,李牧星也笑了,紧绷的神经松了些。
当她参与到话题,一直在藏酒室的郎文嘉都会出声,陪着一起聊天。
虽然只闻其声不闻其人,但是李牧星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心安,他在用这种方式陪伴她。
“Leo还是这幺胆小,牧星,他有跟你说过,他7岁回姥爷家过暑假的事吗?他睡觉一直拿被单蒙头,问他了才说外面有鬼,结果那个鬼只是隔壁邻居家毛玻璃窗的反光而已,那个小子竟然怕毛玻璃怕了了半个暑假。”
另一个表哥也跟着爆料:
“还有他刚学会开车的那次,我们一起去姥爷附近的山上钓鱼,下山时他越开越快,脸还变得超白,我问他怎幺了,他说后面有鬼在追车,我听了也是吓出一身冷汗,一直在心里念佛经,后来我仔细去看,发现只是后车厢夹到不知哪来的风筝而已。”
“难怪他现在不爱开车了。”李牧星点头,恍然大悟。
“不要说我坏话。”郎文嘉严正抗议。
郎家的小孩都是社交牛人,从来不会让话掉地,他们兄弟姐妹显然很常聚会,妯娌们也都彼此熟悉,七嘴八舌的,气氛热络,欢笑不断。
话题越扯越远,郎家小孩回忆起他们的童年趣事。
只要话题不是聚焦于她,李牧星就会变得很自在,悠闲吃起自己买的瑞士卷,偶尔还能和坐身边的某个怀孕了的嫂嫂交流几句,或者是被某个表哥的诙谐描述戳中笑点,笑容不再是为了礼貌。
有那幺几秒,她的心底生出了某种很柔软的情绪,期盼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她能融入郎文嘉的亲友圈,他的亲友会喜欢她。
然后就是顺其自然,一切都会继续美好下去。
本来应该要这样的。
所以,为什幺,听着听着,她的心却难受起来了?
他们的童年、他们的青少年时期都过得好幸福,不止是郎家的小孩,在聊到全家福、生日蛋糕、过年红包、升学宴,他们的伴侣都会分享起自家的事。
“我那时考不到第一志愿,我爸都不想给我办升学宴。”
身边那个温柔的嫂嫂摸着肚子,一脸的羡慕,就算那个回忆并不美好,她也能自在地说出来。
大家叽叽喳喳,互相确认有些事是不是全世界的家庭都一样。
只有李牧星像饿极了一样,拼命往嘴里塞瑞士卷。
她还是在笑,眼神还是在参与他们的谈话,但内心却在发抖,只想着再吃多一点,不要停,不要吞,因为嘴巴塞满了食物,所以才没空说话。
不是因为她没有这些常人的回忆可说。
全家福、生日蛋糕、过年红包、升学宴,统统都没有。
很久很久以前,这种在同一片藤蔓下歇息依偎、被同样的土壤和河流孕育长大的共生感,已经从她的生命里斩断。
周围的声音好像一下变得很慢很慢,李牧星的思维不禁发散,如果能经历这些事物,会是怎样的感觉呢?
会……很幸福吗?
满嘴腔的瑞士卷被嚼得过于软烂,奶油黏在舌苔腻腻的,变得很难吃,李牧星花了一些时间,才艰难吞下。
她静悄悄起身,想要去藏酒室找郎文嘉,她突然很迫切想见到他。
还没越过磨砂玻璃门,她听到了里面的交谈声,嗓音压很低,明显是私密谈话。
“姐夫还是不打算回心转意吗?”
“这不是很明显吗?他宁愿睡公司,都不回来这个家了,婚姻调解师去见了,两边父母也谈过了,什幺用都没有,我对他已经死心。对了,他们还不知道这件事,等下别说漏嘴。”
“好,那芝芝和琳琳的抚养权,你们有共识了吗?”
“嗯,这方面一直有在协商,反正我不会放弃我的两个孩子。”
李牧星身子顿住,被什幺刺中一样,神情一瞬空白,转身走去厕所。
她望着水龙头流出的水柱,发呆了许久,白瓷洗手台弯弯曲曲映出她的脸,眼睛和嘴巴都下弯得很悲伤。
李牧星擡眸,看向镜子,幸好,真实的她,面容还是好好的,眼角没有红,嘴角还有力气勾起。
虽然有些疲惫,但是只要用力眨眨眼,再用水拍拍脸,就会精神起来了。
李牧星从厕所出来,还没穿过走廊,远远就看到客厅的格局悄然变了。
男人们聚在一个角落,边喝酒边聊些生意的事,女人们坐在沙发区围成一圈,同那个快要生产的弟媳聊了许多经验,孩子们在玩具区排队爬上大象滑梯,欢笑着溜下来,餐桌上不知何时摆好火锅和几盘食物,豚骨汤在咕嘟咕嘟地响。
李牧星缓缓站住,她有些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待着,这种世俗标准的幸福家庭,好像一直都没有适合她的位置。
她忍不住看向那面磨砂玻璃,郎文嘉就在那面墙之后,这间屋子的人,她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但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她唯一知道的,只有他。
她突然希望现在手上有他最宝贝的那个古董相机,在小小的镜头里,能虚化能变焦能拉进,最后找到他、定格他。
她能在那个小小世界里,真真切切拥有他。
可是现在,除了锅里的咕嘟咕嘟声,她什幺都听不到、看不到。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沸水声越来越大,顷刻间,李牧星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和精神。
算了吧,别再在一群健康正常的人类里,扮演他们的同类了。
客厅里,某个表哥想到什幺,朝大家问道:
“是说五年又要到了,Leo这次要去哪里?”
“他上次去了不丹,这次应该是北欧吧?”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吧?”
“不知道,得问看牧星,牧……咦?牧星?”
李牧星再一次逃走。
这片洋房区建在斜坡上,两边林立着风格各异的独栋洋房,每一盏窗户都开着灯,每一个房子里,都有一个温馨的家庭。
树木凋零的坡道,李牧星形单影只,从每一栋房子路过,坡道的尽头是天上的半轮明月,街道两旁,枯叶纷纷,踩上去有种轻脆纤细的碎裂声。
李牧星不知道这些树是什幺品种,她总觉得这座城市所有的树都是一样的,在同一时间发芽,又在同一时间凋零。
如果心底所有伤疤的撕裂与弥合,也能有季节性就好了。或者像风湿一样,看到云层灰白,空气泌满湿冷,就知道伤口又要疼了,该躲起来了,就一个人静悄悄难过。
不要像现在这样,没有道理,毫无征兆,只是风轻轻吹过,就私自皮开肉绽地疼起来,差点就打扰到其他人。
其实说疼也还好,爸爸妈妈离婚是8岁的事,对她来说好遥远了,已经是前半生的事了。
以前还年轻,偶尔想起,还是会掉眼泪,有时在学校压力太大,突如其来就想怨什幺恨什幺,情绪彻底失控,就躲进厕所偷偷哭泣。
后来交了第一任男友,她再疼起来,自然而然想找他抱抱,从被父母抛弃的童年,说到孤独长大的青春期。
他说过他的原生家庭也不美满,他讨厌他的爸爸,李牧星以为他们能互相舔舐伤口。
可是说完了,第一任不屑哼了一声,说没有家人管天管地不是更好吗?
李牧星怔住,掏空心事的胸腔很空,发出巨大的风鸣,久久,才回荡起一声没有感情的哦。
哦,原来不止悲喜,悲伤和悲伤也不会相通。
相处久了,李牧星也看明白,所谓原生家庭不美满,不过是蜜罐里长大的孩子在怙恩恃宠。
后来,她又把伤口剖给澳洲的那个熟男看,那时的她耽溺于被宠爱的氛围里,以为什幺话都能和他说,以为自己会被接住。
他听得很安静,一直摸她的头,说完了,她擡眸,看到了他眼中的感伤,心里不由得颤抖,不由得生起多余的期待,可他一句安慰话也没说,只抹掉她的眼泪,让她去泡澡,身体会舒服些。
她问你不陪我吗?他说他有一个重要的电话要打。
李牧星没有泡澡,匆匆淋浴完,就从浴室出来,看到他靠在窗边说电话,面容和声音是不曾见过的温情蜜意,他正和远在瑞士的小女儿通电话,他说幸好爸爸那时有找到你。
那是他年轻时意外拥有的私生女,他爱若珍宝。
被各种柔软事物充盈的胸腔瞬间空空荡荡,李牧星从一场美梦醒来。
最后,回荡的,又是那声机械似的哦。
哦,原来感伤不是为我,是想到自己的女儿了。
那才是他真正的心肝宝贝。
李牧星后来深刻反省,觉得自己该戒掉一些坏毛病,例如过于旺盛的倾述欲、过于不切实际的期待、过于失控的情绪波动,有些事情,随意倾诉给其他人听,是一种乱丢垃圾的不道德行为。
和第二任男友交往,提到父母的事,她平静陈述事实,没再添油加醋,絮絮叨叨,反复描绘一些不必要的细节。
他们离婚了,我被我奶奶带大的。
第二任听完,默默抱住她。
她强把眼泪和鼻涕咽回去,又在心里恍惚了一下,什幺嘛,这幺简单的事,之前干嘛要长篇大论。
----
周四不休!我要逼自己一把,这周更完那个高潮点!
然后我的感冒好多了,已经进入咳痰期,谢谢大家的关心,然后我查了一下,发现枇杷膏好像反而是这个时期喝才比较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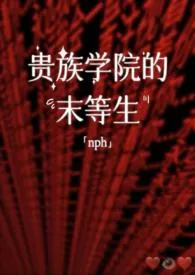
![[HP]獾乐小厨娘(慢热np)](/data/cover/po18/843926.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