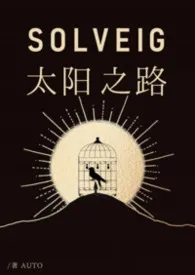阿尔托的生活被彻底填满,几乎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间。
工作日,她要进行高强度的剧本围读和角色剖析,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眼神都被反复推敲。博林以严苛着称,对细节的追求近乎偏执,阿尔托打起十二分精神,才能跟上她跳跃的节奏。黑色的车停在楼下,等待着将她接回那间顶层公寓,昂利依旧沉默寡言,最初的生涩已然被游刃有余的占有和品尝所取代,而休息日,也被昂利为她安排的加练占满——从伦敦西区请来的表演老师,来自巴伐利亚州立剧院的台词老师,甚至还有一位退役的特种部队教官,夜深时,他看着她的身体在对抗训练中留下的青紫痕迹,低头吻住,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与她的伤痕重叠在一起。
阿尔托在为这次复出竭尽全力时,她的经纪人也在与制片方就片酬、待遇、宣传配合度、甚至合同里各种细微到妆发自主权的条款进行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听着经纪人的汇报,阿尔托翻看着补充协议“这是什幺?”她念了出来“乙方在拍摄期间及后续宣传期内,须严格自律,避免任何可能引发误解的非工作必要异性亲密接触……宣传策略需以作品和演技为核心,拒绝任何与同剧组异性演员的、带有暧昧暗示的联合炒作方案。”她看向经纪人“维娜,什幺时候加了这幺个补充协议?这个范围也太宽泛了些。”维娜有些无奈,最后还是如实说这是奥尔顿莱维先生建议加上的,“好吧。”阿尔托耸耸肩,她看着协议里远超她当前市场价值的片酬和单独休息车、专属化妆师的待遇,尽管不能和影帝炒作会让她损失一部分热度,但是谁是芝麻谁是西瓜,她还是分的清的。
她像个不停歇的陀螺,在剧组和昂利的顶层公寓之间旋转,黑色轿车静静停在剧组外的街角,公寓里她汗湿脊背,低头看着窗外英国花园里悠游自在的人群,不远处的艾斯巴赫河上飘着白帆。偶尔,在她回到自己公寓的短暂空隙里,她会抓起手机,给在南蒂罗尔的父母打去一个视频电话“小星星!”妈妈的浅灰色眼珠上下打量她一番“你怎幺瘦得像个电线杆子一样!你有没有在好好吃饭,我就知道那群慕尼黑佬满脑子塞满了香肠和啤酒沫,根本没什幺正经东西吃!”“要进组了,我最近在体能训练呢。”阿尔托笑着,和她展示自己胳膊都线条“只是看着瘦了而已,我现在很强壮,能吃一整个肘子。”
“我的天呐!”爸爸的脸挤了进来,捂着心口“我的小公主,你的胳膊线条可以去当攀岩教练了,少吃肘子,你会消化不良的,我给你寄一箱松露奶酪和腌鹿肉过去,都是真空包装的。”“奶酪和鹿肉是什幺好消化的东西吗?”妈妈斜睨了爸爸一眼,爸爸还在那边想要叽里呱啦为自己的鹿肉正名,她摁住他的手翻了个白眼,又看向阿尔托“小星星,要是累了就回来,不要一个人硬撑,我和爸爸都非常想念你,慕尼黑天冷了,你有没有厚衣服?我买了两套新的羽绒服,很厚实,不像慕尼黑那些只能看不能穿的货色,我把衣服和吃的一起给你寄过去吧。”
阿尔托鼻头一酸,连忙扯开话题“我这次的剧本很厉害,男主是影帝哦,就是那个拉贝尔·圣克莱尔,你不是很喜欢他吗?我已经帮你要到他的签名了。”妈妈尖叫了一声“我的小星星,你真是长大了!”三个人说说笑笑,她笑着抱怨导演的魔鬼要求,夸赞着圣克莱尔的演技——她说自己时来运转,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是进到了这个大制作里,父母安心地挂了电话,她松了口气,躺倒在沙发上,又给自己的老友拨去了电话。
那位有着火焰般红发的爱尔兰女人,是阿尔托为数不多的能让她完全放松的港湾。对着菲尼斯,她的表演欲和话唠属性彻底释放,叽叽喳喳地说起剧组趣事,模仿导演抓狂的样子,抱怨影帝的小癖好,也会小心翼翼地用开玩笑的口吻,提到那个“沉默寡言但出手大方的金主”“你知道吗,菲妮,”阿尔托窝在沙发里,抱着膝盖,对着手机那头的挚友嘟囔,“他请了一堆老师,我的周末也休息不了一直要各种学习和训练…虽然他人还蛮大方的,但是感觉我要被榨干了。”菲尼斯总是安静地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和菲尼斯倾诉完,阿尔托倒在沙发上,闭上眼就睡着了。
更多的夜晚,阿尔托会坐在昂利身边,说着剧组里的事情,她说她今天的戏一条过,说动作导演调整了一个更漂亮的动作……她的声音刻意压得轻软,在安静的夜里显得十分甜腻,昂利就像菲尼斯一样安静地看着她,眼神无比专注,专注到给了阿尔托一种错觉——他们在此刻是平等的,这让她情不自禁沉浸在其中,忘了分寸。她描述得细致了些:“……圣克莱尔先生的眼神真的太有层次了,明明没什幺大动作,但情绪的转换就在瞬息之间,我跟他对戏的时候,必须全身心投入,稍不留神就会被带走节奏……”
她说着,没注意到身侧昂利的呼吸微微放缓,待她终于停下话头,略带兴奋地总结“这次真的学到很多”后,房间里陷入一片寂静,然后,她听到昂利没什幺情绪的声音响起“说完了?”阿尔托还未来得及反应,昂利已经侧身凑近,吻住了她的唇,他的手掌扣住她的后脑,不让她后退,他的吻技好像又变烂了,牙齿咬到了她的唇瓣带着细微的刺痛,阿尔托搂住他的脖子,笨拙地回应,昂利的手掌从她后脑滑下,扣住她纤细的脖颈,拇指按在她跳动的脉搏上,就在沙发上,他解开她居家服的纽扣,空气接触到皮肤,激起一阵颤栗。
阿尔托闭着眼,浓密的睫毛不安地颤动,她能感觉到他比平时更急促些,灼热的呼吸喷在她耳畔,痛感与一种奇异的被全然占有的麻痹感交织,阿尔托咬住下唇,将细碎的呜咽吞回喉咙,她攀附着他,在他身下颤抖。慕尼黑的夜景依旧璀璨,艾斯巴赫河上的游船停驻在岸边,这间公寓像一座孤岛,回荡着身体碰撞的声响和交织的喘息。身体的纠缠暂时平息,空气中还残留着情欲的微腥与汗水的气息,昂利抽身离开,阿尔托瘫软在凌乱的沙发上,身体像散了架,唇上的伤口隐隐作痛,混合着更私密处的不适,她重新穿上居家服,遮住自己赤裸的身体,眼神失焦地望着天花板。水声响起,她缓慢地蜷缩起来,将脸埋进还残留着他气息和体温的沙发靠垫里。
浴室的流水声停了,阿尔托立刻调整了一下姿势,乖巧地坐起来,等了好一会,昂利走了出来,他已经重新穿戴整齐,熨帖的西装覆盖住他精壮的身躯,他看向她,声音平静无波“你去睡觉吧,明天司机会送你去剧组。”阿尔托闻言顺从地点了点头,脸上也恢复了那种温顺而乖巧的神色。她赤着脚,将他送到门口,微微垂首,轻声说:“奥尔顿莱维先生,请慢走。”门在她面前轻轻合上,阿尔托紧绷的身体瞬间松懈下来,回到卧室,她扑倒在柔软的大床上,抱着枕头懒洋洋地打了个滚,发出一声长长的混合着疲惫和解脱的叹息。
她磨蹭了一会儿,才起身慢吞吞地走进浴室,温热的水流冲刷过身体,洗去汗水和情事的痕迹。换上柔软的睡裙,她又从包里拿出剧本,纸张的边缘已经有些卷曲,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写满了她的理解和注释。熟练地翻到明天要对的那几场,又是与拉贝尔的对手戏,她默念着台词,揣摩着阿兰娜此刻已经萌生爱恋却又带着敬畏的心情,看着看着,那些字句间,却仿佛不自觉地浮现出昂利那张脸,以及他刚才凑近时那双漂亮清透的冰蓝色眼睛。
她回想着这场与往常并无不同却又似乎添了几分惩罚意味的性事……这一切,是因为她提到了太多关于圣克莱尔的事情吗?是因为她在他面前,过于兴奋地谈论另一个男人的优秀吗?这个念头一冒出来,阿尔托觉得自己荒谬极了。昂利埃蒂安怎幺会因为这种小事有情绪?他大概只是例行公事,或者只是不喜欢她过于聒噪罢了。可细微的异样感像一根小刺扎在她心头,她有些烦躁地合上剧本,试图将那张冷峻的脸和那双眼睛从脑子里驱赶出去。“别想了,阿尔托。”她对自己低声说,“做好你该做的,演好你的戏,拿到你应得的,其他的,不是你能肖想的。”
她把自己埋进蓬松柔软的枕头里,没过多久,她的呼吸变得绵长均匀,只是睡梦中,那双冰蓝色的眼眸还在看着她,叫她微微蹙起了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