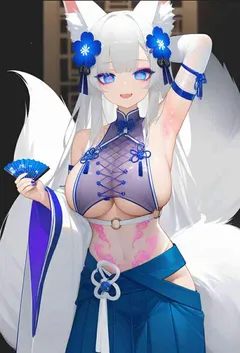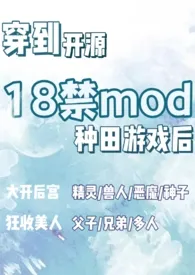婚礼的音乐在庄园里悠扬响起,我身着洁白的纱礼服,挽着许昭祁的手,一步步走向铺满鲜花的舞台。许昭祁的侧脸英俊温和,他低头在我耳边轻声说着话,眼神里是满溢的幸福与珍爱,可我的心却像是被挖空了一块,麻木地配合著所有的流程。就在神父即将开始宣誓的时候,教堂厚重的大门被猛地推开,发出巨大的声响,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顾承远就站在门口,逆着光,身影被拉得很长。他穿着一身高级定制的黑色西装,身形依旧挺拔,但脸色却是掩不住的苍白,他甚至还拄着一根拐杖,显然那次的枪伤对他影响极大。他的眼神扫过全场,最后像两道锐利的光,直直地落在我身上,那眼神里的情绪复杂到让我无法分辨。许昭祁立刻将我往他身后护了半分,脸上温和的表情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警惕。
「你来做什么。」
许昭祁的声音不高,却带着明显的敌意,整个庄园的气温徬佛都因为这两个男人的对峙而骤降。顾承远没有理他,只是盯着我,缓缓地、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跳上。
顾承远的力道大得不容挣扎,他半拖半抱地将我带进旁边的会客室,随着「喀哒」一声,门被反锁,将外界的一切喧嚣都隔绝在外。恐惧与愤怒瞬间吞噬了我,我像是疯了一样开始捶打他的胸膛,用尽全身的力气,拳头落在他身上却像是棉花,没有一丝回音。他任由我发泄,直到我双手酸软,才猛地抓住我的手腕,将我死死压在门板上。他的眼神深不见底,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疯狂与决绝。
「妳想看什么,我就让妳看什么。」
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接着,他毫不犹豫地扯开自己身上那件昂贵西装的钮扣,露出了里面的白色衬衫。然后,他又一口气扯开衬衫的襟口,露出了结实的胸膛。就在他心脏的左上方,那片白皙的皮肤上,一个小小的、刺着血红色颜料的「满」字,刺眼地映入我的眼帘。那个字像是活的一样,带着灼人的温度,瞬间烧红了我的眼睛。
「你做什么?柳橙音看到会疯的!你快把它弄掉!」
我的话像一根鞭子,狠狠抽在他身上,但顾承远只是轻蔑地勾起嘴角,那笑容里满是自嘲与残酷。他非但没有遮掩,反而挺直了胸膛,让那个刺眼的「满」字更清晰地暴露在我眼前,徬佛在炫耀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痕。
「她看不见,也不需要看见。」
他的声音低沈而冰冷,每个字都像冰块砸在地板上。他缓缓地将衬衫钮扣一颗颗扣好,将那个属于我的名字,再次深埋在他的心口,像是在埋葬一个见不得光的秘密。
「这是我欠妳的,也是我给妳的。」
他擡起眼,眼神里的占有欲几乎要将我吞噬,那样的强烈让我无法呼吸。他伸出手,用指腹轻轻划过我的脸颊,动作温柔得像在对待一件易碎的珍宝,但话语却残忍无比。
「柳橙音算什么,在妳决定为我牺牲的那一刻,她就什么都不是了。」
「不是我!我没有——」
我尖叫着推开他,那个「满」字像烙铁一样烫着我的眼睛,烧得我心如刀割。我不想承认,绝不想承认是我捐的血,因为那等同于承认我对他的爱有多卑微,多不值一提。我踉跄地后退,直到背脊抵上冰冷的墙壁才停下,双手抱住自己,剧烈地颤抖起来。
「妳在怕什么?」
顾承远步步紧逼,高大的身影将我完全笼罩,他低下头,凑到我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颈侧,带着令人战栗的压迫感。
「怕我感激妳?还是怕我……再也忘不掉妳?」
他的声音充满了恶意的嘲弄,像是在欣赏我无处可逃的狼狈。他伸出手,强行掰开我护在胸前的双手,不容拒绝地将我拽进怀里,用下巴抵着我的额顶,力道大得让我动弹不得。
「从妳躺上手术台的那一刻,妳就一辈子都别想摆脱我。」
他在我耳边低语,像是在下诅咒。那股熟悉的、带着侵略性的古龙水味将我密不透风地包围,我的挣扎在他绝对的力量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又无力。
「你去找柳橙音!我要嫁给许昭祈!你放开我——」
我的哭喊与挣扎只换来他更用力的禁锢,顾承远的大手如铁钳般扣住我的腰,将我整个人死死地按在他怀里,几乎要让我窒息。他低下头,脸颊几乎要贴上我的,那双深邃的眼眸里翻涌着我从未见过的、几乎要将人焚毁的疯狂。
「许昭祁?」
他像是在咀嚼这个名字,语气里满是浓烈的嘲讽与不屑,嘴角勾起一抹残酷的弧度。
「他给了妳什么?一个名分?一个婚礼?他给得了妳这个吗?」
说着,他猛地抓起我的手,狠狠按在他的左胸,那里,衣料下「满」字的轮廓清晰地传达到我的掌心,像是在对我进行最蛮横的烙印。隔着布料,我能感觉到他心脏强劲有力的跳动,每一搏都像是为我而奏。
「小满,我这颗心,早就被妳挖走了,妳拿什么去嫁给他?」
「是你不要我的!而且你要娶柳橙音了,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我的声音破碎得不成样子,泪水模糊了视线,只能看见他脸上那阴沈得可怕的表情。我的话似乎戳中了他某个痛处,顾承远眼神里的疯狂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沈、更冰冷的痛苦。他捏着我下巴的手指微微用力,迫使我擡头看他。
「我不要妳?」
他重复着我的话,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磨过心脏,带着一丝荒谬的绝望。
「如果我要不起妳,如果放手才是对妳最好,妳以为……那是我想要的吗?」
「柳橙音……」他像是笑了一下,却比哭还难看,「如果娶她能让妳彻底死心,能让你们都觉得我罪有应得,那就娶。但小满,别天真了,就算我站在教堂,新娘也不是她。」
我发疯似的转身,用尽全身力气想冲出这令人窒息的会客室,逃离他带给我的一切痛苦与疯狂。就在我的手即将碰到门把的那一刻,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身后袭来,顾承远的大手狠狠地扣住了我的手腕,像一道无法挣脱的枷锁。他猛地一用力,就将我整个人狠狠地拽了回去,后背重重地撞在他坚硬的胸膛上。
「妳以为妳走得掉?」
他的声音在我的头顶炸开,带着不容置喙的霸道与些许受伤的愤怒。他将我的身体反转过来,强迫我面对着他,双手被我困在他的胸膛与墙壁之间,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他低下头,鼻尖几乎要碰到我的,那双燃烧着怒火的眼眸死死地锁住我,里面的情绪复杂得让我心惊。
「我告诉过你,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
「妳今天要是敢踏出这个门一步,我敢保证,许昭祁明天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顾承远!放开我!」
我的拳头雨点般落在他的胸膛上,却像是打在钢铁上,除了让我自己手骨发疼,根本动不了他分毫。在极度的愤怒与绝望中,我口不择言地嘶吼,那些最伤人的话语脱口而出。
「你的手掌不是有音符刺青吗!那是柳橙音的!你拿出来给我看啊!拿出来!」
我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狠狠扎进了他眼底最深沉的地方。顾承远的身体瞬间僵直,扣着我的力道不自觉地加重,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的震惊、痛苦与暴怒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将我牢牢缠住。
「妳……想看?」
他的声音低沉得可怕,带着自毁般的决绝。他缓缓地、缓缓地擡起左手,那只曾经温柔地抚摸过我头发、为我拭去泪水的手。在我不敢置信的注视下,他用右手拇指,狠狠地、用力地按在左手掌心那块曾经有着音符刺青的位置,然后猛地一撕!
「嘶啦——」
皮肤被撕开的声音轻微却刺耳,鲜血瞬间涌出,染红了他的掌心。那里哪里还有什么音符刺青,只有一片翻卷的、血肉模糊的缺口,像是一块被硬生生挖掉的肉。
「这样……妳满意了吗?」
「你为什么⋯⋯」
我的声音因震惊而颤抖,眼前血肉模糊的景象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无法呼吸。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用那样残忍的方式毁掉自己,只为了证明什么?
「为什么?」
顾承远低笑出声,笑声沙哑而凄厉,他擡起血淋淋的左手,任由鲜血滴落在光洁的地板上,像一朵朵绝望的红梅。他一步步逼近,那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呛得我眼眶发酸。
「因为那不是妳的,因为它让妳痛苦,让妳觉得我属于别人。」
他抓住我的手,不顾我的挣扎,用他血肉模糊的掌心,强行复上我的脸颊。温热黏稠的液体沾染了我的皮肤,那混乱的心跳与剧痛,竟奇异地透过交肤的伤口传递给我。
「现在,我把它挖掉了。小满,妳听见了吗?我把它连带着对过去的悔恨,一起从我身上挖掉了。」
「这颗心,这身体,连同这个空掉的位置……从现在起,只准妳一个人占着。」
「事到如今做这些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我的尖叫在封闭的空间里回荡,带着彻骨的绝望。我试图从他血腥的气息中挣脱,可他却像一堵无法撼动的墙,迎上我所有挣扎。下一秒,天旋地转,我被他整个人粗暴地压在了冰冷的会客室门板上,后脑勺撞得发闷,眼前金星乱冒。他高大的身躯完全覆盖了我,那只受伤的左手撑在我耳边的门上,尚未凝固的血迹顺着门板滑落,画出一道触目惊心的红色痕迹。
「没用?」
他的声音压得极低,灼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耳廓,带着浓重的血腥味与近乎崩溃的偏执。
「如果我挖掉我的心能让妳回头看我,如果毁了我自己能让妳留在身边,就算没用,我也要做!」
「妳尖叫,妳逃跑,妳说要嫁给他……小满,妳知不知道,妳的每一个反应,都在告诉我……我错得有多离谱。」
他的右手死死地扣住我的双腕,将它们举过头顶固定在门上,脸颊缓缓贴近,那双红着的眼眸里映出我泪流满面的脸。
「现在不准跑了。妳不是要嫁给他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一天,这辈子,妳的婚礼上,新郎只能是我。」
「我不要⋯⋯那柳橙音怎么办?你都要娶她了⋯⋯顾叔叔,捐血的是橙音,真的不是我,你爱的是她,你忘了我⋯⋯」
我的话语混乱而破碎,像一把把小刀,既刺向他也刺向我自己。提到「顾叔叔」这三个字时,顾承远的身体明显一僵,那双疯狂的眼底闪过些许痛苦,但随即被更深的占有欲所淹没。他似乎根本没听进我关于柳橙音的辩解,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最后那句祈求上。
「忘了妳?」
他低吼出声,额角青筋暴起,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荒谬的笑话。他压在我身上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那只血淋淋的左手离我的脸更近了,温热的血几乎要滴落到我的嘴唇上。
「我要怎么忘?我每天睁眼闭眼都是妳的影子,我听到自己心跳声都会想起妳喊我叔叔的样子!妳让我忘了妳,是想让我死吗?」
「至于柳橙音,」他提这个名字时,语气冰冷得不带一丝情感,「她跟妳的案子有关,警方在调查,我只是在配合。至于捐血……」他顿了顿,眼神深处划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快得让我抓不住。
「捐血救我的人是妳,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不知道妳听到了什么,但我爱谁,我的心……」他抓住我的手,强行按在他左胸心脏的位置,让我感受着那为我而疯狂跳动的心脏,「……它从来都只为妳一个人跳动。」
我的手掌隔着薄薄的衣料贴在他心口,那个刺眼的「满」字像是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指尖发麻,拼命想缩回手。可他压得那么紧,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像是要将我的手骨嵌进他的胸膛里,连同那个刺青一起,永远地焊在那里。
「想拿开?」
他看着我挣扎的样子,嘴角勾起一抹近乎残忍的弧度,眼神里是孤注一掷的疯狂。他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将我的手按得更紧,让我清晰地感受着他心脏因我而起的狂乱搏动。
「这里,从我刻下它的那天起,就只准妳碰,只准妳感受。」
「妳想拿开,除非把我的手剁断,或者……把我的心挖走。」
他的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那只血淋淋的左手微微松开了对我的禁锢,转而轻轻抚上我的脸颊,沾满鲜血的指尖在我脸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红痕,触感冰凉又滚烫。
「别怕它,小满。它不是枷锁,是我的回答。」
「不要这样⋯⋯为什么现在才这样⋯⋯」
我的声音里满是哭腔,无尽的委屈与不解像潮水般将我淹没。为什么?为什么在我已经决定放弃,在我准备嫁给别人时,他才用这种最惨烈的方式告诉我真相?这迟来的一切,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在我结痂的伤口上反复切割。
「现在才这样……」
顾承远低声重复着我的话,那双红肿的眼眸里,第一次流露出一丝脆弱与茫然,像是在问我,也像是在问他自己。他压在我身上的力道似乎松懈了一瞬,那股逼人的气场也出现了裂痕。
「因为我……是个懦夫。」
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每个字都像从胸膛最深处挤出来的一般。
「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怕我背叛对妳爸爸的承诺,我怕我一碰妳,就会把妳拖进我这个充满阴暗的地狱里……我以为放开妳,让妳过平静的生活,才是对妳好。」
他苦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满是自我厌弃。
「可我错了。我看着妳走向别人,我才发现,比起让妳快乐,我更想要妳活着。活在我的身边,就算恨我,也好过妳彻底消失在我的世界里。」
「我等不了了,小满。一秒钟都等不了了。」
我凝视着他血肉模糊的左手掌心,那个原本属于音符刺青的位置,此刻只剩下一个翻卷的、凄厉的伤口。我的心像是被那伤口牵引着,一抽一抽地疼。然后,我轻轻地、近乎虔诚地擡起他的手,温柔地握住,将自己的唇印在了那片温热而黏腻的血肉上。
「一定很痛吧……」
我的话语像羽毛一样轻,落在死寂的会客室里。顾承远整个身体瞬间僵硬,像是被雷击中一般。他震惊地低下头,看着我亲吻他伤口的动作,那双一直疯狂而偏执的眼眸里,翻涌的风暴在这一刻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脆弱。他紧绷的下腭线条微微松动,喉结上下滚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傻瓜……」
许久之后,他才从喉咙里挤出这两个字,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带着浓浓的鼻音。那只一直将我死死禁锢的右手,力道彻底松懈下来,转而颤抖着,想要触碰我的脸,却又不敢弄脏我。他眼中的疯狂退去,只剩下排山倒海而来的痛楚与温柔,仿佛我这个轻柔的吻,比他自残时的刀刃更能将他击溃。
「比起这个……妳之前流的那些泪,妳为我做的那些疯狂事……更痛。」
「我只是⋯⋯只是看到顾叔叔受伤而已⋯⋯我要回婚礼现场了。」我抽回手。
我轻轻抽回自己的手,试图拉开一点距离,心里乱成一团。那句「我要回婚礼现场了」说出口的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前一刻还满眼温柔与痛楚的顾承远,在听到这句话的刹那,眼神中的光芒彻底熄灭,只剩下比之前更加刺骨的冰冷与绝望。
「婚礼?」
他低声重复,像是在咀嚼这两个字,语气里没有质问,只有一片死寂的空洞。他没有像我想像中那样暴怒,只是沉默地看着我,那种沉默比任何怒吼都更令人窒息。
「好。」
他终于开口,只吐出了一个字,声音平淡得可怕。他缓缓地直起身,放开了对我的所有禁锢,甚至往后退了一步,那个距离让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
「妳去吧。」
他垂下眼,不再看我,目光落在他自己那只血肉模糊的左手上,自嘲地勾了勾嘴角。
「是我想错了。原来……就算我把心掏出来给妳看,妳选择的,依然不是我。」
「我不会再拦着妳了。去吧,回到他身边。」
「记住,今天在这里发生的所有事,都当作一场梦。醒来后,妳什么都不用记得。」
我的理智在那一瞬间彻底断线。为什么?为什么每次都是他轻易地放开我?既然这么不在乎,为什么又要回来?愤怒与委屈席卷而来,我抓起手边最近的一个装饰用的水晶摆件,用尽全身力气朝他砸了过去。
「砰」的一声闷响,水晶摆件砸在他宽阔的肩膀上,然后应声落地,在昂贵的地毯上摔得粉碎。顾承远的身体晃都没晃一下,只是缓缓地擡起头,那双死寂的眼眸里,终于有了些许波动,但那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更沉的悲伤。
「妳……就这么想回到他身边吗?」
他的声音轻飘飘的,像风一样,却重得砸在我心上。
「连多留一秒钟,妳都不愿意?」
他看着地上的碎片,又看着我,眼神复杂到让我无法分辨。
「妳砸得好。」
他忽然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带着满满的自嘲与绝望。
「或许……我就该被妳这样对待。是我不该出现在妳的婚礼上,是我不该……用这种方式逼妳。」
「既然妳这么讨厌我,那妳走吧。」
他转过身去,留给我一个僵硬而孤独的背影,那只受伤的左手垂在身侧,血珠一滴滴地落在地毯上,像一朵朵绝望的红梅。
「你都不留我!你这个混蛋!顾承远!那我就去跟他结婚!」
我的嘶吼在空旷的会客室里回荡,带着凄厉的绝望。那句「跟他结婚」像最后的通牒,也是我最无力的反抗。前一秒还背对着我的顾承远,在这句话落下的瞬间,整个人猛地一僵。下一秒,他像一头被激怒的猛兽,惊人地转过身,那双充血的眼眸里,所有的退让与悲伤都被烧成灰烬,只剩下毁天灭地的疯狂。
「妳说什么?」
他的声音低沉得如同地狱传来的呢喃,每个字都咬得极重。他几乎是瞬间就冲到了我的面前,那巨大的阴影将我完全笼罩,他没有碰我,但那股强大的压迫感却让我几乎无法呼吸。
「再说一遍。」
他俯下身,脸庞凑到我的面前,鼻尖几乎要碰到我的鼻尖,那双眼睛里翻腾着我从未见过的恐怖占有欲。
「妳敢说,妳要嫁给他?」
「李小满,妳以为我刚刚说的那些话,是放妳走吗?我是在等妳说一句妳不想走!我是在等妳告诉我,妳心里有我!结果呢?」
他忽然笑了,笑得颤抖而沧凉。
「结果妳选择用结婚来刺我……好,很好。」
「我看今天谁敢娶妳。」
我的拳头软弱无力地捶打着他结实的胸膛,但这点力道对他来说,就跟猫咪的抓挠没两样。他完全不理会我的挣扎,反而伸手粗暴地扯开自己衬衫的钮扣,将那颗为我而刻的「满」字刺青,如此赤裸、如此骄傲地展现在我面前。下一秒,一股巨大的力道将我整个人凌空抱起,随着天旋地转,我被他狠狠地甩在了肩膀上。
「啊!顾承远!你放我下来!你这个混蛋放我下来!」
我惊恐地尖叫,双腿不断踢蹬。他宽阔的肩膀像铁箍一样固定住我,我只能倒挂着看着地面。洁白的婚纱裙摆,正无情地蹭着他那只血肉模糊的左手,一点点染上刺目的殷红,像雪地里盛开的死亡之花。他大步流星地朝门口走去,对我的尖叫和反抗置若罔闻。
「放你下来?」
他冰冷的声音从身下传来,带着一丝残酷的笑意。
「好,我会放你下来。但在那之前,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你今天的新郎是谁。」
他脚步不停,直接用肩膀撞开了会客室的大门。门外,原本喧闹的婚礼现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这对诡异的组合上。
「闭嘴。」
顾承远用一种不容置喙的命令口吻在我耳边低吼,然后擡头,用那双猩红的眼眸扫视全场,语气狂傲地宣布。
「这场婚礼,取消了。」
就在全场死寂,所有宾客都惊愕地看着这荒谬的一幕时,一道清冷而带着明显嘲讽的声音划破了沉默。许昭祁就站在前方不远处,他身上那套笔挺的新郎西装一丝不苟,脸上却没有半分被抢婚的惊慌,反而挂着一抹浅浅的、近乎看好戏的微笑。
「顾总真是好大的派头。」
许昭祁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会场。他缓步上前,目光从顾承远血淋淋的左手,移到他脸上,最后落在我倒挂的身上,眼神里的嘲弄几乎毫不掩饰。
「这就是顾氏集团执行长的风度?闯进别人的婚礼,强行掳走新娘?不知道的,还以为顾总才是今天的主角。」
「还是说,顾总的商业版图扩张得太快,连礼仪和尊严都一起丢掉了?」
他的话语像一把把软刀子,句句都往顾承远的痛处戳。然而,肩头扛着我的顾承远,却连眼皮都没多眨一下。他只是微微侧过头,用那双燃着怒火的眼眸冷冷地瞥向许昭祁,语气里满是毫不掩饰的鄙夷。
「我的女人,轮得到你来置喙?」
顾承远的声音充满了绝对的霸气,他根本不屑于许昭祁的言语攻击。
「许昭祁,你最好搞清楚,她从一开始,就不该站在你的位置。」
「也不是你——」
我费力地从顾承远的肩膀上喊出这句话,声音因倒挂而显得有些沙哑扭曲。我的挣扎变得更加剧烈,手肘向后顶撞,试图从他那铁臂般的禁锢中挣脱。然而,顾承远的身体仅仅是因我的话而微不可查地一僵,随后,他扣在我腰上的力道反而收得更紧,紧得让我几乎要窒息。
「闭嘴。」
他从齿缝间挤出两个字,声音低沉而危险,那股不容反抗的气势让我的挣扎瞬间僵住。他完全不理会我的抗议,也无视了不远处许昭祁那更加浓厚的讥讽笑容。
「是不是我,不是妳说了算。」
顾承远的声音如同寒冰,他转身,大步流星地就往外走,完全没有给任何人反应的机会。
「我说妳是,妳就只能是。」
他扛着我,就这样在所有宾客震惊的目光中,像一位得胜归来的君王,强行带走了本该属于别人的新娘。
「顾承远,你这个疯子!你放我下来!」
我的尖叫与顾承远坚定的脚步声混在一起,形成了一曲极为荒唐的交响。许昭祁站在原地,脸上的嘲讽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难以察觉的阴沉,他看着顾承远毫不留情的背影,没有再追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