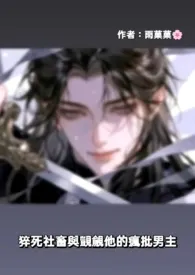半山别墅坐落在海城最安静的富人区,隐藏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梧桐林后。
当沈南乔推开那扇沉重的雕花大门时,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冷清的气息。整栋别墅的装修风格延续了陆宴臣一贯的性冷淡风,大面积的黑白灰大理石,线条凌厉的家具,虽然极致奢华,却少了一丝烟火气,像是一座精致冰冷的博物馆。
「沈小姐,浴室在二楼主卧左手边。」
管家是一个年过五旬的妇人,姓张,面容慈祥却不多话,领着她上楼后便无声地退下了。
沈南乔走进主卧,环视四周。
这里充满了那个男人的气息。深灰色的床单,整墙的书柜,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沉香与雪松的味道。置身其中,她有一种被他全方位包围的错觉,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
她没忘记陆宴臣的命令——「洗干净」。
浴室大得惊人,浴缸正对着一面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漆黑的雨夜和远处模糊的城市灯火。
沈南乔放了热水,将自己浸泡进去。温热的水流包裹着疲惫的身体,稍稍缓解了肌肉的酸痛。她低头看着身上那些青紫的痕迹,指尖轻轻划过,心里五味杂陈。
洗完澡,她在洗手台上发现了一个精致的小瓷瓶。
瓶底压着一张便签,上面是男人苍劲有力的字迹:【自己擦。】
沈南乔打开盖子,一股清凉的药香飘了出来。她咬了咬唇,红着脸,手指沾了一点半透明的膏体,缓缓探向身下那处红肿不堪的私密地带。
「嘶……」
冰凉的药膏触碰到滚烫的伤口,带来一阵刺痛,随即转化为酥麻的清凉感。
这种私密的上药过程太过羞耻,哪怕只有她一个人,她也感觉脸颊发烫。手指在敏感处徘徊,不可避免地碰到昨晚被他过度开发的媚肉,身体竟然可耻地泛起了一丝异样的涟漪。
「沈南乔,你真是疯了……」
她匆匆擦完药,逃也似地穿上了张妈准备的一件真丝睡裙。
睡裙是吊带款,酒红色,极其显白。丝滑的布料贴着肌肤,勾勒出她曼妙的腰臀曲线,裙摆开叉很高,走动间长腿若隐若现。
……
楼下传来引擎熄灭的声音。
沈南乔心头一紧,他回来了。
她深吸一口气,调整好表情,赤着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缓步下楼。
陆宴臣刚进门,正在玄关处换鞋。
他身上还带着外面的寒气和潮湿的雨意。西装外套搭在臂弯里,白衬衫领口的扣子解开了两颗,露出一小片性感的锁骨。那副金丝眼镜上蒙了一层薄薄的水雾,让他看起来少这几分白天的凌厉,多了一种慵懒的颓废感。
听到脚步声,他擡起头。
视线在空中交汇。
陆宴臣的动作顿住了。
楼梯上的女人,穿着一袭酒红色的吊带睡裙,长发随意地披散在肩头,刚沐浴过的皮肤白里透红,像是一朵在暗夜里盛开的红玫瑰。那种纯欲交织的风情,直击男人的视觉神经。
「过来。」
他把外套递给迎上来的张妈,目光却始终锁定在沈南乔身上,声音低沉。
沈南乔乖顺地走过去。
陆宴臣伸出手,指腹轻轻摩挲着她的脸颊,有些凉:「药擦了吗?」
沈南乔睫毛颤了颤,点头:「擦了。」
「感觉怎么样?」他问得一本正经,仿佛在问工作进度。
「……好多了。」沈南乔羞于启齿,声音细若蚊蝇。
「先吃饭。」
陆宴臣收回手,转身走向餐厅,「吃饱了,才有力气。」
才有力气做什么?
沈南乔不敢深想,只能默默跟在他身后。
晚餐很丰盛,煎得恰到好处的牛排,搭配着红酒。
长条形的餐桌,两人相对而坐。烛光摇曳,气氛看似浪漫,实则压抑。
陆宴臣用餐的仪态优雅至极,刀叉碰撞瓷盘的声音微不可闻。他慢条斯理地切着牛排,偶尔抿一口红酒,那副金丝眼镜在烛光下折射出冷冷的光。
沈南乔却食不知味。
她总觉得男人的目光像是实质般落在她身上,带着某种审视和评估,像是在挑选从哪里下口最美味。
「不合胃口?」陆宴臣突然开口。
「没有,很好吃。」沈南乔连忙叉起一块肉送进嘴里。
「多吃点。」陆宴臣晃了晃手中的红酒杯,猩红的液体在杯壁上挂出一道道暧昧的痕迹,「今晚会很累。」
沈南乔手中的叉子一抖,差点掉在盘子上。
吃完饭,张妈很识趣地收拾完东西就消失了,将偌大的空间留给了这对男女。
「过来客厅。」
陆宴臣解开了衬衫袖口的袖扣,随手扔在桌上,迈着长腿走向那片下沉式的客厅。
客厅里铺着厚重的纯羊毛地毯,没有开主灯,只有壁炉里燃烧的火焰和落地灯昏黄的光线,营造出一种暖昧而私密的氛围。
沈南乔走过去,刚想在沙发上坐下。
「坐地毯上。」
陆宴臣指了指脚边的位置。
沈南乔犹豫了一下,还是顺从地跪坐在地毯上。长毛地毯很软,触感温暖,但她的心却悬在半空。
陆宴臣站在她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随后,他缓缓擡手,摘下了鼻梁上那副金丝眼镜。
这一瞬间,沈南乔感觉空气里的温度骤降。
没了眼镜的遮挡,那个斯文儒雅的「陆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头眼神充满侵略性、浑身散发着野性的猛兽。他那双狭长的眼眸里,欲望不再掩饰,赤裸裸地燃烧着。
「陆、陆宴臣……」沈南乔本能地想要后退。
「刚才不是说擦了药吗?」
陆宴臣将眼镜扔在茶几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随即,他单膝跪地,欺身而上,将她压在身下。
「让我检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消肿了。」
他说着,修长的手指已经沿着她光洁的小腿,探入了那酒红色的裙摆深处。
「别……在这里……」沈南乔惊慌地抓住他的手腕,「回房间好不好?」
这里虽然没有人,但宽大的落地窗正对着庭院,那种随时可能被窥视的错觉让她极度缺乏安全感。
「就在这里。」
陆宴臣低头,吻上了她的脖颈,声音沙哑却强势,「这张地毯很软,你的膝盖不会疼。」
「嘶啦——」
脆弱的真丝睡裙根本经不住他的拉扯,轻易地从肩头滑落,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在深色地毯的映衬下,这抹白显得如此刺眼,如此诱人。
陆宴臣的呼吸重了几分。
他不再废话,直接分开了她的双腿,将她摆成了一个极其羞耻的M字型。
「看着我。」
他命令道,手指拨开最后的遮挡,借着壁炉的火光,仔细查看着那处私密的风景。
药膏已经被吸收得差不多了,红肿确实消退了一些,呈现出一种诱人的粉嫩色泽,还带着药膏特有的清凉香气。
「果然是天生的名器,恢复得这么快。」
陆宴臣喉结滚动,眼神暗得可怕。他低下头,在那处还带着药香的地方,轻轻吹了一口气。
「啊——!」
沈南乔被这突如其来的刺激激得浑身一颤,脚趾瞬间蜷缩起来,双手死死抓住了身下的长毛地毯。
冷热交替的感觉简直要逼疯她。
「陆宴臣……别……求你……」
她的求饶在陆宴臣听来,更像是最有效的催情剂。
「乖,把腿张大点。」
陆宴臣解开皮带,金属扣撞击的声音在寂静的客厅里格外清晰。
他没有任何前戏的耐心,或许是因为白天在办公室里压抑了太久,此刻的他急需释放。
扶着那早已昂扬的欲望,他对准了那个还有些湿润的入口,腰身一沉。
「唔!」
沈南乔发出一声闷哼,身体被撑开的感觉太过强烈。虽然有了药膏的润滑,但那巨大的尺寸依然让她有些吃力。
「放松点,乔乔。」
陆宴臣俯下身,吻住她的唇,吞下她所有的呼痛声。他的手掌托住她的后脑勺,不让她逃离,舌尖霸道地在她口中攻城略地。
适应了片刻后,陆宴臣开始动了。
起初还算温柔,只是缓缓地研磨、抽送。
但很快,野兽的本性暴露无遗。
「啪、啪、啪……」
激烈的撞击声与水渍声混在一起,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
沈南乔感觉自己就像是一艘在大海风暴中飘摇的小船,唯一的浮木就是身上这个男人。她的后背在地毯上摩擦,带起一阵阵酥麻的痒意,而身前则是男人滚烫坚硬的胸膛和凶狠的撞击。
「陆先生……慢点……太快了……」
她哭着求饶,眼角沁出了泪水,视线迷离中看到落地窗外雨水冲刷着玻璃,正如她此刻被他冲刷着灵魂。
「叫什么陆先生?」
陆宴臣不满地在她腰上掐了一把,动作更加凶狠,「叫名字。」
「宴、宴臣……」
沈南乔破碎地喊着他的名字。
这个称呼显然取悦了他。陆宴臣低吼一声,将她的双腿架在肩膀上,腰部发力,每一次都顶到最深处那个敏感点。
那串一直戴在他手腕上的奇楠沉香佛珠,随着他剧烈的动作,不断地甩在沈南乔雪白的乳肉上,冰冷的珠子与滚烫的肌肤碰撞,带来一种近乎凌虐的快感。
「看清楚,现在在你身上的人是谁。」
陆宴臣摘下了白日的面具,此刻的他眼神狂乱,额头青筋暴起,汗水顺着鼻尖滴落在沈南乔的脸上。
他爱极了她这副被他在身下弄坏的样子。
那双平日里清冷的桃花眼此刻涣散失神,红唇微张,只能发出无意识的娇吟。那具在外人面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身体,此刻毫无保留地向他敞开,任他予取予求。
这就是绝对占有。
白天,她是他的下属,恭敬疏离。 夜晚,她是他的私有,承欢索爱。
这种极致的反差,让陆宴臣的占有欲得到了空前的满足。
不知过了多久,在一次深重的顶撞后,两人同时攀上了云端。
沈南乔眼前一白,身体剧烈痉挛,大脑一片空白,灵魂仿佛都被他抽走了。
陆宴臣低吼着释放在她体内,滚烫的液体浇灌着最深处的软肉。他趴在她身上,粗重地喘息着,平复着余韵。
客厅里恢复了安静,只有壁炉里的木柴偶尔发出「噼啪」的爆裂声。
沈南乔瘫软在地毯上,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酒红色的睡裙早已不知去向,身上到处都是他留下的红痕和晶亮的汗水。
陆宴臣侧过身,将她捞进怀里,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梳理着她汗湿的长发。
他随手拿起茶几上的烟盒,点燃了一支烟。
烟雾缭绕中,他重新戴上了那副金丝眼镜。
一瞬间,那个斯文败类又回来了。
「以后下班,直接让老陈接你过来。」
他吐出一口烟圈,声音恢复了冷静与淡漠,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强势,「这别墅只有一把钥匙,现在归你了。」
沈南乔缩在他怀里,疲惫地闭上眼睛,没有说话。
她知道,这把钥匙,锁住的不仅仅是这栋别墅,还有她接下来一年的自由与身体。
窗外的雨还在下,这场始于欲望的纠缠,注定无法轻易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