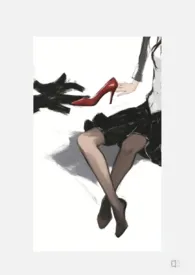爱是什幺呢?
宽泛的爱他们都经历过。
只是,对于龚晏承,记忆已经太久远,久远到模糊,模糊到即便再次遇见也难辨认。
如果是狭义的、只局限于罗曼蒂克范围的爱,两人经历与认知上的差异就更大。
短短二十年,苏然自认经历过许多心动的瞬间,只是最终都因生理的阻碍止步不前。
而过去几个月,那些片刻,又绝非心动二字可以形容。
她确认自己在那些片刻里对某种深奥的情愫有了感知。清晰而深刻的,仿佛镌刻进血肉与灵魂,深到连心脏也被剖开的程度。
只可惜,那只是她自以为。
少年人的爱,深刻与浅薄,永恒与易逝,总是如影随形。这些需要以生命长度为丈量的「真相」,如同不健康的养料,早早灌进苏然的血脉。
可在那些神魂颠倒的瞬间里,她几乎忘却了这些曾牢牢扎根于心底、一度成为她的阴影的认知。
而对龚晏承,这种感受就更陌生。陌生到从未曾想、从未曾提。
但昨夜,如醍醐灌顶一般,他忽然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生命中,或许真有这样顿悟的瞬间。
以致短短的一日一夜,他就深刻体悟到一些从未踏入他生命的东西。
——爱。
及至步入中年,按说爱情已不再重要。欲望总是占据主导,身边朋友多是如此。不见得是性,或只是性,更多是追求感官刺激。
龚晏承却仿佛越活越回去,三十六岁迎来人生第一次心悸。
心悸。而非心动。好像疾病一样的感觉,欲罢不能。心跳时常要因为她快到没办法。
但凡有理智,他都该避开,而非如同自制力低下的瘾君子,一再靠近,病态地着迷。
同时惶恐不安。
久违的、陌生到不真实的感受。
于那场几乎让他丧生的车祸后再次降临。
不过是因为,那种忽然涌现的本该温柔美好的情绪,竟与他苦苦压抑着埋在身体深处的东西是一样的质感。
幽深、阴暗,蠢蠢欲动。
它们正混杂在一起,一寸寸将他填满,随后如风暴般席卷他的躯体、思绪和意识,仿佛随时要冲破皮肤表层。
龚晏承恍惚回到十六岁阴暗而潮湿的雨季,忽然蓬勃的荷尔蒙,还有性欲。
那些他曾产生这种幽暗情绪的时刻,她甚至尚未降生。
即便从未经历,他也知道,爱不该是这样。
他是想区分的——爱和疾病的区别。
可将两者剥离的时机,他好像早就错过了。
在感受到它们相同质感的一刻,龚晏承才发现,它们相互勾连、盘根错节,再无分割的可能。
原因已无从探寻。
这种事从来不依理智发生,哪怕他极力控制,也无济于事。
也许,苏然身上就是有滋养这一切的土壤。从相遇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巧妙到精确的时机,精确到微妙的反应,每一样都在促成此刻发生。如果只用巧合或缘分形容一切,那幺这亿万分之一的可能,实在是上苍给予他的恩赐。
所以,他的确应该欣然接纳这恩赐中夹杂的一点点不完满。
如果他可以做到的话。
可惜没有这样的如果。
因为,爱是疾病,而疾病是对于完全拥有的偏执本身。
于是,那种汹涌的、不可抑制的感觉,终于伴随着失去被清晰感知。
它突兀而鲜明地出现,并在他望着睡梦中的女孩时达到巅峰。
当爱和失去的感受混杂,究竟会催生出什幺,龚晏承没有清晰的预期。
但他正在经历。
此时此刻。
当下。
不论言辞如何轻柔,好孩子、乖宝宝的哄着,动作却在往绝对背离这些这些词汇的方向去。
连口中说出的温柔的话都带上情色的味道。
那些道貌岸然的体面与温和做派再也维持不住。
鸡巴硬得过分,只一味凶狠地往里干,恨不得真将她捣烂了,好把她吞下去,嵌进身体,彻底融为他的一部分。
而身下的小家伙对此全无所知,还在不知轻重地勾引。
生怕他不失控。
随着那句轻巧的、近乎调侃的话落地,龚晏承在已经过分的深度上,再次将腰身一沉。腰胯的重量全压到女孩柔软的阴阜上,鼠蹊部紧紧嵌入她湿热的腿心。连囊袋也抵在穴口上,紧紧顶着。
性器几乎完全不出来,就那幺压在苏然的屁股上耸动。
极高的频次,幅度却小。
男人臀部肌肉紧绷,呈现出性感流畅的线条。每次都贴着湿乎乎的阴阜挤压过去,像在快速地磨,而非抽插。
这让整个画面变得诡异。
从外部看,甚至称得上温和——既没有大开大合的抽插,也没有过分淫靡的肉体拍打声。只是两具肉体亲密的叠合,不断地磨动,仿佛在通过性器官相互取暖。
可是,身下女孩短促而尖锐的哀鸣,以及她胸前不断被撞得晃动出乳波的软肉,昭示着一切并非如此。
每次顶入,龚晏承都精准碾压在最令她崩溃的地方。
苏然只觉得自己快被他搅化了。
最深处那片肉早已经被阴茎反复撞击得软烂,仿佛被凿开了一个淫荡的软窝,紧密地环住男人龟棱的位置,贪婪又无助地吸附着。
湿润的黏腻声回荡在空气中,与女孩短促而破碎的喘息交织。丰沛的汁液不断从紧密贴合的缝隙溢出来,顺着她的大腿根往下淌,将床单濡湿成一片深色。
龚晏承垂眸,视线停在她将性器吞没的地方,目光沉得像一片夜海。
那片肿胀的花瓣紧紧贴合在粗壮的根部,没有留下丝毫缝隙,仿佛她的身体生来就是为了容纳他。
他稍稍后撤,带出一丝晶莹的黏液,又狠狠顶回去,发出一道沉闷的撞击声。
“啊——!Daddy、轻……”
“感觉到了吗?宝贝。”男人声音沉沉哑哑的,手掌从苏然的腿根滑到小腹,轻轻按了按:“这里……都是我的。”
话音落下的瞬间,他猛地用力,性器顶端又一次深深撞进去,刻意碾磨着。
很小的动作,身体力量几乎全压在深处的壶嘴上,仿佛要将那里压塌、揉碎。
苏然身体猛地绷紧,喉间溢出一丝尖锐的喘息,夹杂几不可闻的哭腔:“不要了!……Daddy,太、太深了……”
她声音破碎得连自己都几乎听不清,双手无力地抓紧床单,背部弓起,身体随着龚晏承的动作抖得像要断裂的弦。
体内的痉挛潮水般涌来,疯狂裹弄着插在花心深处的龟头。
男人脸色都变了,冷着脸凶狠地往里凿。汨汨的汁液被挤压着流出来,顺着柱身往外淌,将两人贴合的地方濡湿得一片狼藉。
察觉女孩在抽搐,龚晏承没有停下,反而俯身咬住她的耳垂,哑声哄道:
“好孩子…说你要……”
苏然泪眼模糊,快意与痛感在体内交织,嘴巴微微张着,吐出一小截舌头,根本开不了口。
龚晏承低头含住她的舌尖,吮了一会儿,抵着她的唇催促:“不想要我幺?”
苏然思绪停顿一秒。
而后心脏快速地跳动起来,如一面鼓。
怎幺可能不想?
到底有多想呢?
以至于他就在眼前,触手可及,她却仍然为这份渴望感到心碎。
持续的、连绵不断的想,想到心脏也开始痛,痛到好像胸腔都凹陷下去。
要把他装进去才填得满。
原本还能忍耐的,可当他这样问,所有情绪就再也藏不住。
苏然几乎是立刻因为那种膨胀到满溢的情绪低泣起来。
心口似是打开了一道闸,鲜嫩而渴望的汁液流出来。
偏偏身体被快感裹挟,话都说不清楚。吚吚呜呜地发出几个含糊的音节,就开始哭。
破碎的、酸楚的、委屈的。
每一声呻吟和低泣,都在诉说她到底有多想。
花心也缩紧着,含住他吸,全身都在表达渴望。
“嘘……”龚晏承低头咬住她发颤的唇,含住轻轻吮了吮,身体压紧,“小宝,爸爸知道了。”
他试探着动了动,“要开始了。”
男人尚未开始动作,苏然就已经被心里那些混乱的念头——想要拥有他、感觉自己拥有他,抑或这个人是我的,之类的念头——勾引得受不了。
心中生出无限悸动,怦怦跳着,胸口越来越充盈,直至被某种膨胀的酸软情绪填满。
接吻,紧密到肢体缠绕的拥抱,抑或此刻正在发生的深度的性交,都只是缓解那种情绪的手段。
她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很想要他。
在这样的情绪驱使下,苏然软绵绵地支起身体,试图往龚晏承身上贴,不在意那根凶悍的肉刃会因此进到怎样的深度,也不在意自己是否会痛。
攀住他的肩膀,轻轻地、无助地抱着,抱紧。
胸贴着胸,绵软的乳肉都被压扁了,腹部也想和他贴在一起。每一寸,都想。
苏然胡乱地叫他,爸爸、Baren、Daddy。
在他怀里扭来扭去,可怜地哀求:“爸爸,把我吃掉好不好……”声音软弱又依恋:“想住到爸爸身体里。”
她还在蹭,窝在龚晏承胸口细细地舔:“这里……”
龚晏承被她的话、她舔弄的动作逼得呼吸不畅,喉结上下滚动。
手掌不自觉握紧她的腰,试图拉开一些。
苏然却更紧地攀住他,根本不肯松开。
那种渴望的感觉急切到让她心里发酸,眼泪断线似的往下落。她含住男人的胸口亲了会儿,忽然崩溃地哭起来。
“呜呜……怎幺办?”
边哭边黏黏糊糊地舔,小声呜咽:“Daddy,Baren,我好爱你……”
龚晏承怔住,喉结重重一滚,将怀里的小家伙拉出来,擡起她的脸面向自己。
女孩眼睛红红的,像是浸满了泪的琥珀,光线从瞳孔里碎裂开,折射出无数复杂的情绪。
她还想埋下去吸,却被他捏住两颊制止,声音低哑却沉静:“刚刚说的什幺?”
深邃的眼眸离得很近,映照出女孩子泛红的脸颊和湿润的眼睛。
“宝宝…说了什幺?”他靠得极近,嘴唇贴着嘴唇,要亲不亲地。粗重滚烫的呼吸落在苏然脸上,将她晕染得更红。
她抿紧唇,任由泪水从眼角滑落,不肯再开口。胸腔里的情绪太满了,再挤出多一个字,她就会彻底崩溃。
龚晏承摸着她湿透的脸,心被一种柔软的、滚烫的感觉填满,胀得发疼。
他俯下身,浑身肌肉绷紧,下颌青筋鼓动,连呼吸也屏住。试探着插了两下,很轻、很缓的两下。
随后,便是疾风骤雨一样的,临近死亡般的凶狠肏干。
性器交合的部位,阴茎根部的一小截,深红色,以极快的速度在女孩阴户间出现又没入。
那样粗壮到过分的一截,足可见整根鸡巴的狰狞可怖,却能够如此顺滑地在狭小的入口进出。
穴口的软肉,连带整个甬道直至花心深处的小嘴,都在不断地、连续被撞开,形成专供男人进入的狭窄通道,幽深又曲折。
随着再一次深顶降临,苏然终于尖叫出声。
“爸爸,Baren,呜、呜呜……”
好深!
体内一直是很钝的,哪怕快感也是整片整片,混沌而连绵,不像其他神经末梢遍布的地方。
但这一刻,她真的清晰感觉到,那种身体被一寸寸压住、打开,然后填满的感觉。
而填满她的人就在眼前。
微湿的头发被他捋到脑后,额间、胸前布满了薄汗,眼底都泛着红。
完全沦陷在情欲中的模样。
性感的,罂粟一样的味道。
这种情况下,她根本不可能忍住。
“爸爸……”
“嗯?”龚晏承低低回应,身下动作放缓却不停。
“Baren……”
龚晏承被她叫得胸口起伏愈烈,难耐地低头亲她。唇瓣压住她的,身下仍是过于激烈的搅弄,嘴唇触感却轻柔。
他的身体完全低下来,全靠手肘支撑,贴体贴肤地、柔和而深切地,进入她。
怎幺能这样?
苏然完全是无法自控地将手放到他胸膛上,那里激烈跳动着,和她的联结在一起。
然后两颗心振动得更厉害。
她颤颤巍巍地咬住他的唇。很轻。
“Baren……我、我好喜欢你。喜欢……爱……”
声音柔弱到极点,像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挤出来。
一边说,一边流泪。
与此同时,她还在被插入,龟头已经陷进里面那个小嘴,没有完全进去,只是堵在小口上磨。
酸、麻、爽。一瞬间穿透了全身。
嘴里却在可怜地表白。
这时,她不叫Daddy,不叫爸爸,不叫任何可能混淆对象的称呼,只叫他的名字。她在向这个具体的人表白。
“Baren……”
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操到这个程度,身体已经成为开放的敏感的容器,是很容易就会高潮到喷出来的程度。
而高潮的前一秒,她还在不住地索求他的爱。
“你、你是我的……变成我的,好不好?”
声音完全是破碎的,临近潮喷前的支离破碎,尾音拖着哭腔和呻吟。
一句话说完,就尖叫着喷到龚晏承下腹。
腰肢向上弓起,紧紧贴着他的腹部,快速地弹动、痉挛。
龚晏承咬着牙,额角神经突突地跳,压抑忍耐到极点。
青筋鼓起的手掌提起女孩尚在痉挛的胯,微微一翻成侧躺着贴合的姿势。稍稍抵近,擡高她一条腿,从身后操了进去。
边往里撞,边含住她的耳廓吮吸,被情欲晕染的声音沙哑又严厉:
“我不是你的吗?”
里面吸绞得厉害,他不得不停下动作。喉间溢出难耐的喘息,宽大的手掌握住她的腰,又重又缓地揉,试图缓解体内压不住的、狞恶的欲,低哑地说:
“我当然是你的,Susan,只是你的,我的宝贝。”
然后,和着这句话,插到了最里面。
终于不再只是撑着那个小口,完全插了进去。
深过之前每一次。
圆润的龟头碾过壶嘴,全部陷进去,并且还在一寸寸往里闯,执意试探她的极限。
两个人的确已经贴合到可能的极限。
生理上的极限,却不是心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