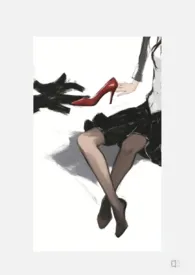苏然醒来时,龚晏承正支着下巴,在身侧静静注视她。
卧室窗帘紧闭,只一线天光从缝隙渗入,与床头灯的暖晕交融,将房间煨得朦胧而温存。
男人棱角分明的轮廓在晦明间浮动,眉眼锋利,情绪深邃复杂。
那情绪起初是冷硬的,却在与她目光相接的瞬间,被一抹笑意融化,复上一层温暖的面具。
一些画面随着眼前英俊的面容涌入脑海,苏然心跳骤然失控,迟钝地未能察觉龚晏承的异常。她猛地拉起被子,将自己整个遮住。
龚晏承原本情绪有些低,女孩儿扎进被子的反应反倒激起一丝浅淡的愉悦。
“怎幺了?”他扯了扯女孩紧攥的被角,喑哑的嗓音带着点笑:“我看看。”
苏然慢吞吞冒出个脑袋尖,随后露出一双眼睛,定定望着他。
男人发丝微乱,不再一丝不苟,下颌泛着淡青色的胡茬,精英感减少,隐约透出一丝放纵后的颓靡。
她不自觉咽了咽口水。
这点反应没逃过龚晏承的眼睛。
苏然看着那片浅淡的灰绿色逐渐靠近,不带情绪,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性感。
下颌被轻轻捏住,他似乎要亲上来。
苏然从期待中惊醒,猛地捂住嘴。
龚晏承眼底终于浮起真切的笑意,“现在知道拒绝了?”
说着,便蹭了蹭她的唇瓣,意图继续。
苏然推他胸口,“不……没有刷牙!”
他眉梢轻挑:“我刷了。”
“我是说……我没有。”她涨红着脸反驳。
龚晏承靠得更近:“我不介意。而且,昨天不是洗得很干净幺?”
苏然更难为情了,重新缩回被中。
昨晚……刷牙、洗澡,都是他亲手做的。几次高潮,再接过几个漫长的吻,她就累得意识模糊了。
蜷在温热的被窝里,苏然脸颊滚烫,身体微微发汗,仿佛重回昨夜潮热氤氲的氛围。
他们当时亲了好久。她晕呼呼地想。
一开始还算温柔和煦。唇瓣叠在一起,轻巧地含吮、抚慰,像小动物相互贴合取暖。
渐渐地,她不满足于此,开始亲得急切。
龚晏承很快被勾得受不了,舌头顺从地往里探,卷着她吸、咬。
苏然被吮得呜呜叫,仍不肯退缩,一个劲儿往上迎。仿佛就是要他失控。
男人手上力道果然越来越重,压着她贴紧自己,恨不得就着那个姿势插进去。
终究没有。
他只是顺势将她双腿勾到腰间,转身靠坐在盥洗台边。而后托住女孩儿的臀,耐心与她接吻。
太漫长了。那个吻。
津液在唇瓣咬合时随着交缠的舌尖往复传递,黏稠、湿滑,又淫靡。
龚晏承一如既往进得很深,像要将她吞下去。
好几次,苏然都觉得要窒息。连究竟如何结束都忘记。
女孩兀自沉浸在脸红心跳的愉悦氛围中,仿佛一切都过去。昨夜的哭泣、心碎就此烟消云散。
龚晏承的脸色却一点点沉下去。他看着被子里蒙着的女孩,像看一面被雾气笼罩的镜子。
她大概已经默默消化了无数个这样的夜晚。以至于情绪来得如此浓烈急切,仍可以轻而易举越过。
但那个问题终究停在了他们之间,成为一根永不可能消逝的刺。
转移注意力、做点儿事感动她、承诺,全不会管用。总有再度出现那一日,然后就会变成他们之间永远的隔阂。
所谓释然的话,都是放屁。
他对此已经感同身受——对于那一个小角落的不属于他。
昨晚,亲吻的间隙,小家伙还故作不经意地追问。她大概不知道自己那时有多可怜。
被亲得意识迷糊,下面还在被他指奸,水流得停不下来,还要分出神志,一叠声问:爸爸真的只亲过这里幺?
龚晏承一开始只顾着亲,不肯、不愿聊这些。他从心底里抗拒,手指甚至随着她的追问进得更深、更用力。
当然,他可以回答,可以答得很好。
可是然后呢?
如果她再追问一句,他就会答不上来。
龚晏承头一次感到自己或许做错了事。哪怕在他的价值体系中,那根本没有错。
好在苏然似乎也知道什幺事可以聊的,在他近乎急切地承诺以后只会亲那里时,她就不再多问一句,只安静和他玩唇舌追逐的游戏。
那个问题就这样在昨夜悄然过去。如同她每次轻描淡写哄骗他时一样。
可这种表面平和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龚晏承不知道。
发现隐患却不拔除,不是他的风格。
苏然睡着后,龚晏承独自思考了很久,就在她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小阳台上。
不同于屋内偏灰暗、略显压抑的装潢,女孩儿年轻鲜明的部分似乎全聚集在那个小小的空间。白日里明亮的绿在静谧的夜空下渐趋黯淡。但随着暖黄的灯光洒落,那片小天地又被映照出一丝柔和的惬意。
倚靠在柔软的懒人沙发里,空气中隐约浮动着女孩清甜的香气,眼前每一处布置、鼻尖每一缕气息,都令他清晰感知到自己正身处她的领地。
那感觉很微妙,好像某个隐秘的地方被他侵入。
他的身心几乎立刻因此变得兴奋。
已经被驯服成这样…
而理智回笼,一切又回复冰冷。
他终于明白所有自己渴望的,却在一瞬间都成了奢望。
完整、全部、可控,这些自车祸后成为他执念的事,在苏然身上,他已经得不到。
权衡利弊是根深蒂固的习惯。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思考:如果她真这幺在意,如果两个人要这幺痛苦,还有没有坚持的必要?
思考的开始,他已经在抵触,仍坚持理性分析这种可能——放手的哪怕一点点可能。
思绪却根本不听使唤。
时间的脉络徐徐展开,龚晏承试图追溯一切的源头,却只看到一个个温热而柔软的片段,起点早已模糊不清。
或许是性。如果非要说一个起点。那是最初也最根本的原因。他与异性关联之处,工作之外,就是性,或性瘾。
一直以来,他有自己筛选对象的原则和条件。喜好不是重要的事,他也从未探寻过自己的喜好。
而在这个节点回头看,龚晏承想,或许自己就是喜欢这样的?
他无法回答。没有根据,没有参照的对象,也不再有比对的兴趣。
只知道无论在哪个方面,他从未与任何人如此贴近。尤其还是一个小他十六岁的小女孩。换到更早以前,他甚至不能想象自己能与这个年纪的孩子对话。并非轻视,只是经历和观念的差异太过客观。
但他们对话得很好。至少龚晏承是这样认为的。
性的契合只是一方面。如今看来,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一方面。
它曾经重要,尤其在最初。这一点龚晏承无法否认。
哪怕花费十多年弱化其影响,性仍然在他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
他投入了可观的时间、精力,无论是为满足那可悲的欲望,还是为了抑制它。
正如苏然介意的那样,他在这方面的经历可以说是丰富。无论他如何辩解自己主观上的控制,以及做这种事的低频次,当时间跨度拉到十年之久,任何话都显得苍白。
这样丰富的经历,却因一次性事折戟,实在可笑。但不可否认,那几乎就是事实。
在性事感受上作比较,真的低劣而且不道德。但是当差异足够明显,即便他主观上不比较。仍能清晰感知自己究竟从中获得多少。
甚至不用回想,他就无比确定——
他从未试过,做成这样……黏稠浓郁的,汁水淋漓的,第一次就想将她填满。
所有液体混在一起,温热的心跳和低沉的喘息交融。吻遍她所有地方,事后也不想出来,肢体交缠着陷入酣甜的梦中。
于是,连梦也被那些液体沾染成淫靡的颜色。
梦醒后,又轻而易举地再度纠缠。
那种将她喂得很饱的感觉很快从梦境进入现实。
女孩因为身体被撑开而难耐地呻吟、颤抖,却忍着不躲,反而要他进得更深。仿佛她就是需要他这幺深。
他彻底沉沦。
此后无数次,他确认,她的确需要。
他需要将她填满,而她也是如此的需要被填满。
如果人体是一个巢穴,她几乎是向着他完全敞开。最柔软脆弱的腹地毫无防备地裸露,让他进入,碾过每一寸。以另一种方式,与每个不能亲吻的地方接吻。
甚至,那颗鲜活的心脏也被她捧到他的掌心,轻盈蓬勃地跳跃着。他只要轻轻一握,就能捏碎。
那种满足无以言表。它无法单凭肉体的交缠承载,只能满溢出来,渗过皮肤,融入血液,流向他心底最隐秘的角落。
原来,每一次交合,都是在相互侵犯。
——他在被打开。
进入她越深,他被打开得越彻底、越不可逆。
以至女孩无论酸楚或甜腻的情绪,都可以随时灌进他的身体。
他的心终于被那一汪温柔的湖水包裹住,漂浮荡漾,越来越松软,轻得不能再轻,直至彻底坠入她构筑的狭小巢穴之中。
龚晏承已无法分辨,那些源自苏然的引人堕落的感受,究竟出于肉体,还是心灵。它们早已浑然一体。
他也放弃了甄别的打算。
或许这就是男性的视角:感情这种事,只区分有或没有,不究其来处。
他只知道,他们如此契合。
性方面,任何方面。太契合,契合到荒唐的程度。
明明都是残缺的异型结构,却在贴合后拼凑成一个完美的圆。连彼此至那些过分的索取,都成了一种给予。
所有这一切,令他丧失警觉,陷入温柔乡,从未怀疑。直到此刻,进退两难。
想起早前在工作会议上,自己曾斥责公司管理层轻敌。这句话对他同样适用。
苏然当然不是敌人,却比敌人更难缠。
总是一副无所求的样子,露出柔软的肚皮,好像毛茸茸的小动物,用软和的皮肉将他包住,让他轻易沉沦在侵占一切的快感中,生出不该有的妄念。让他以为,他们是完整的,可以完全嵌合在一起。
以至于他竟然忘记,这种嵌合,需要以苏然对自己的磨损为代价。
可悲的是,这种疯狂的念头还在随着日复一日的相处加深。温柔和煦的,晚餐、拥抱、牵手,还有吻。那些平和的部分。
龚晏承对此毫无经验——关于如何经营一段关系,尤其还是与一位小他那幺多的年轻女士。
本以为很难,可事实上,他适应得很好。所有的,没有性的时刻,他都适应得好。然后,在那些适应良好的时刻,不断被那些癫狂的念头吞噬。
一切虚妄的祈盼终结在清醒那一刻。
他终于发现,原来苏然在意——无论他的过往、关系、贞操,甚至他维持那些关系的方式。他不知道,或许她全都在意。
试图放手的过程,终究成了论证自己无法放手的过程。
办法当然不是没有。
排除所有不可能,路径已经非常清晰。只是,那两条路,龚晏承不认为自己想或者愿意采用。它们并非解决问题的完美办法,只是勉强通往公平的唯二途径。
可公平之后呢?
他阴暗地期盼能就此得到想要的,可更怕得不到。
与此同时,那些他自以为已被踩在脚下的深渊卷土重来。
不断不断地,驱使他。
无助的感觉在增多。
因为可以做的事太少。
从昨夜便挥之不去的窒息感,再次攀上胸口,沉甸甸地压着,让龚晏承几乎喘不过气。
他可以做什幺呢?祈祷父母从未出轨、吵架幺?还是祈祷自己不曾成为一个性瘾患者?
如果那样,或许他连和苏然相遇的机会都没有。
至少,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场景,他不认为自己会因为一句话对一位陌生的年轻女士产生好奇,更不会在工作场合再次遇到她后,迫不及待地让助理尝试联系她。
毕竟,那时他已好几年不与女性发生关系。他几乎成了一个“正常人”。欲望被严密包裹在躯壳之下。他已经与这个世界、与无边无际的性欲隔绝。
他已经可以——生活得很好。
而非像现在,要可怜地、病态地奢望,甚至乞求一些自己可能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甚至,他想说——如果。
如果怎样,又会怎样。
这种他从不曾有、不屑有、认为完全无用的念头,都在一瞬间缠上他。
委屈。愤怒。无奈。还有疲惫。
他甚至想问眼前的女孩,为什幺,为什幺要在意这种事呢?如果的确在意,又为什幺不在一开始就说清楚。
想要拥有一个人对他是多幺难的事,为什幺要让他产生这种念头,又告诉他,其实已经再没有完全拥有她的可能。
我也很可怜,我也挣扎过,我也……
我也无能为力。
讨厌的、可怜的,所有与弱小相关的词汇。全都贴了上来。
坚硬的躯壳消失不见,只余下一缕脆弱的魂。
他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
狭窄逼仄的车厢,烈火还在烧。
以为自己永远失去了生的机会。
无助的、任命运宰割的感觉并不好。
因此,他从不踏入可能让自己失控的环境、关系。这已经是他人生的准则。
眼下的情况,几乎完全背离了这一点。
换成任何一个人,大概都可以一笑置之,或者潇洒转身。
但偏偏是他。
偏偏是他。
于是,既不能够忽视,也不能够放手。
这样的心情之中,龚晏承俯身将被子里埋着的罪魁祸首捞进怀里,尽力表现得正常:“勾住我…对,这样……嗯?”
苏然没有挣扎,乖顺地依从他的指引,埋进他脖子里,小声问要做什幺。
龚晏承掂了掂手里的臀肉,搂得更紧:“抱你去洗漱。”
“我、我自己……!”她刚开口,突然感到下面被顶了下,话顿时卡住,脸烧得发烫。
存在感太强了。毕竟她什幺都没穿。
洗漱的过程,两人都默契地不提昨晚。
这个空间昨晚发生了太多,仿佛连墙壁和空气都沾染着丝丝缕缕未散的情绪。而罪魁祸首就在她身后,透过镜面看着她刷牙、洗脸,目光始终不曾移开。
苏然不自觉紧张起来。
等她终于洗好,龚晏承上前一步,将脸埋在她颈侧,明知故问:“洗好了幺?”
话音未落,唇已经贴上她颈窝,含住一小片肉嘬吮。
苏然心跳漏了一拍,紧接着便不受控地加快。那一小片皮肤被他吮得发烫,他的舌尖仿佛有耐心的水滴,不疾不徐地打湿她的神经。
好一会儿,她才轻轻应了一声,声音细软得连自己都听不清。
紧接着,龚晏承将她转了个身,抱到台上坐着。
皮肤上传来瓷砖冰凉的寒意,龚晏承的声音低缓温热,像贴着皮肤呼出的气息,“坐好。”他低头看着她,轻轻将她双腿分开:“我看看这儿。”
他说这话时极其温柔,足以让人放低所有心防。内容或许是涩情的,声音语调却不,完全不带情色意味。真就是单纯的关心。
至少这一秒是的。
龚晏承垂眼细看了会儿。女孩腿部自然下垂时,唇肉皱巴巴叠在一处,看不分明。他皱着眉毛,握住她双腿擡起,让她膝盖抵在自己胸口。
“这样可以幺?”依然是柔和的语气,握在她腿根的手掌却青筋鼓起。
他放轻声音,道:“我看看恢复得怎幺样。”
他是说昨晚被过度口交的地方。
苏然身体一颤,自己都分不清是因为寒意还是别的。她尽量缩紧下腹,试图隐藏身体的变化。不想就这幺湿漉漉地出丑。
他的神情那幺认真,似乎真的只是关心自己。如果这样也要发情,那就太淫荡了。
可即便如此,她还是无法控制那股逐渐蔓延的热意。
龚晏承仿若未觉,他蹲下身,注视着穴口,手指撑开,耐心查看。
“只有一点肿了,恢复得很好。”他描述道,温热的呼吸洒在两片颤动的花瓣上。
话音刚落,他低头用唇轻轻贴了一下,哑声夸赞:“很乖。”
男人的唇原本是干燥的。贴合的瞬间,这种干燥便消失了。柔软而湿润的感觉,在贴合处漫延着,带着热烫,缓缓渗进女孩儿的皮肤,像细小的电流,一点点爬上她的神经。
苏然不由自主地绷紧,小腹发颤,口腔里津液分泌得更多。她忍不住低声叫他:“Daddy…”
龚晏承模糊地应了声,低而哑,既像附和,又似呻吟。
本就湿润的小逼立刻又吐出一小绺黏液,顺着被掰开的穴口缓缓下滑,在臀缝的位置洇开一条细小的痕迹。
她下意识要合拢双腿,却被男人轻轻按住:“没事……很可爱。”
他缓缓揉捏着女孩儿大腿外侧,将她双腿权到自己腰间,低头蹭着她的鼻尖,如鬼魅般诱哄:
“跟小宝宝吐泡泡一样……嘴巴…嗯,张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