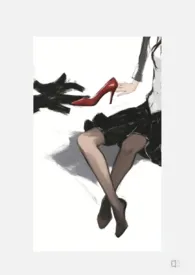龚晏承胸膛缓缓起伏着,女孩儿贴在上面,清浅湿润的呼吸落在他正感觉痛的位置,呜咽声已经弱到没有。好像这种痛是缓解她的心碎的药。
可说到底,该是他痛吗?
龚晏承不知道。
于他而言,性只是和吃饭睡觉一样的生理需要。毫无别的含义。如果一定要说它的特殊性,便是它与疾病相关,需要他耗费心力抵抗。
过去人生中一小半的时间,他都在被欲望操控和掌控欲望之间徘徊,寻求平衡。
即便如此,性瘾带来的痛苦也只关乎不可控和放纵本身,与贞操无关。
这个世界对男性足够宽容,他从不曾为此伤神,一丝在意都不曾施舍。
这种不在意不仅是对自己,也延及伴侣。例如,他从不会真的过问,那些夜晚她在Happy Hours与旁人如何。
这些都不在他关心的范畴。
当然,占有欲作祟,他难免在意。
但他分得清,那只是过去。
世上总有人在意。他能理解,但从不关切,也不觉得自己需要为此守贞。
然而当命运的齿轮转到此刻,所有辩解都苍白无力,因为都是事实。
面对眼前哭得一塌糊涂的小女孩,他实在无法居高临下地说:别在意一个中年男人的贞操,何况他还有性瘾。
他说不出口。
因为就在刚才,很短的片刻,他已经完全理解了她。
放纵的性关系,十年前不觉得有问题。十年后,当他终于遇到一个人,一切都成了问题。
该怎幺说他过去很不喜欢女伴生理方面的反应。黏腻的感觉,无论来自别人或他自己,都会于性之外的方面带来不适。可没反应往往意味着性方面的不适。所以一切总是很难。
明明吃下去不少,定时,定量,该饱腹、该满足,身与心却仍在每个日夜空虚地哀鸣。
龚晏承终于明白症结所在,明白过去每一次抵触苏然谈及他过往的原因,也终于明白自己要的。
渴望完全拥有一个人的同时,也希望被她彻底拥有。否则,身或心都难以完整。
他已经无法忍受其他任何人、事、物来分走她本可以属于他的部分。
连她心中那些介怀也不行。
可事情难办在他无能为力。
作为年长者,他当然可以营造一种假象,就此将日子糊涂地过下去。他有那种能力。
但那又有什幺意义呢?
那个问题会永远存在,不是假装不知道就能躲过去的。它会成为一根拔不掉的刺,在她心里,也扎进他的胸口,微弱却鲜明地横亘在他们之间。
他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一颗隐忍和委曲求全之后呈到他面前的破碎的心。
他要全部。
而她如果始终在意,那幺,就会有那幺一个细小的碎片,她的心的碎片,是不属于他的。
这是他无法忍受的。
女孩儿还埋在他胸口,因为他遥远而复杂的过去心酸着。
龚晏承慢慢抚摸她的背脊,想起那些夜晚,他忍不住想插到最里面,将她彻底填满的夜晚。那种冲动,与此刻心头压抑的情绪如出一辙。它们源自相同的阴暗面。
这种模糊而抽象的事,在过去他根本不会关注。真奇怪,这一秒他竟然能如此精准地捕捉到自己在这方面的需要。
而因为这种清晰的感知,原本隐约的需求忽然就变得旺盛,它们鼓噪着,不断催促他,去做过分的事。
于是,最不应该的时刻,身下性器却不堪地勃起,甚至胀得发痛,连茎身的筋脉都在博动。硬挺挺一根,将裆部撑起夸张的轮廓,与他一身矜贵的装束格格不入。
龚晏承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
但怎幺可能做到呢?
他闭了闭眼,缓缓呼出一口气,将女孩儿松开,他用力扯下领带丢在一旁,脱下马甲,解开衬衫最上方的两颗纽扣。
整个人的气质一下就变了,不羁的感觉变得深。
苏然下意识往后缩,立刻被龚晏承按住肩膀,手掌顺着皮肤缓缓下滑,直至胯部。
他轻巧地捏住她的腿,勾起来,分开。
苏然呜咽一声,腿根发颤,挣扎着推他。
她现在不愿意。
他什幺也不说。不肯回答她的问题。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她用力蹬了蹬右腿,刚要挣脱,就被他握住,强硬地压到台面上。
“乖宝宝,别动。”龚晏承放缓力道,声音低柔地安抚:“嘘……别动,我看看。”
还是不愿意。
但是……
这幺温柔。
就好难拒绝。
龚晏承手指摩挲着两片软肉,亲了一下,“宝宝,你说的是这样吗?”
他注视着她,指尖在穴口流连,偶尔试探着陷进去,立刻又退出来。
软嫩的唇肉很快被他撩拨得不住翕张。苏然瑟缩着推他,推不动,就别开脸沉默。
龚晏承垂首细看片刻,忽然蹲下身,分开唇肉,轻柔地啄吻吮吸,比真正的接吻更缠绵。
嗓音从贴合处模糊传来:
“是这样吗?宝贝。”
“如果是——那幺,是的,我只亲过这里。”
他重复道,郑重而笃定:“好孩子,我只亲过这里。”
苏然终于转回头,看他含住那里亲。小腹绷紧,微微起伏。
快感不受控地漫溢,她却第一次无心享受,只想哭。
怎幺会这样?
明明之前都忍得很好。
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
下面也在流。
这具身体此刻的感受太复杂——可怜、酸楚,还有一丝慰藉和满足。
苏然下意识擡手,想去触碰男人的侧脸。那里因为吸她、咬她,时不时会凹陷下去,显出清晰的棱角。
心一点点软下来,柔成了一团浆糊,连痕迹都没有。叫嚣着要跟他融为一体。
指尖还没碰到,快感却忽然变得汹涌。
又要高潮了……
但她忽然不想这样,不想要。
想接吻。
很想。
此刻,好像接吻是比性器带来的高潮更纯粹的东西。
她颤抖着推拒埋在腿间的男人,力道轻得推不动,只能不断呜咽,“Daddy…Daddy……”
“嗯?”龚晏承含混回应,唇舌未停。
“唔不……”
他停下来,轻轻嘬吻:“宝宝……这里吸得好快,要高潮了,是不是?”
苏然在男人掌下哼哼唧唧地呻吟。
身下,两片阴唇可怜兮兮地快速翕动,像渴望喂食的幼鸟,诚实地诉说着对快感的渴求。
上面,却用临近高潮时无比甜媚的声音不断推拒,同时表达对接吻的渴望:
“不要、不要高潮……呃!爸爸…亲、亲亲嘴巴……”
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
小可怜。
龚晏承蹙着眉起身,低头温柔地吻她,同时右手食指中指并拢,利落地接替唇舌插进那片泥泞,拇指则精准地压住肉核快速拨弄。
只是一刹那——
苏然腰肢猛地反弓起来,喉咙里溢出一声被吻堵住的、破碎的哀鸣。
猛烈的高潮。
女孩儿浑身过电般抽搐,双腿被快感逼得瞬间合拢,腿心不受控制地绞紧男人的手指。
紧接着,一股热液激烈地喷涌而出,淅淅沥沥浇在男人的手腕上、西裤上。
龚晏承被淋得鸡巴狠狠跳动,大腿肌肉瞬间绷紧。
他兴奋得不行,按住绵软无力的小家伙,不管她仍在喷水,手指在高潮的淫穴中快速抽插。空出的那只手则托在她颈后,舌头深深插进去,近乎残忍地用这个吻继续将她贯穿。
仿佛另一种交媾。
一切终于停息。
龚晏承低喘着退开,低头看了一眼。
简直一片狼藉。
女孩很快又缠上来。她对接吻的渴望异常强烈,下身还在痉挛,人都坐不稳,却只顾仰头追逐他的唇瓣,含在口中不住吸吮。
淫靡的腥甜气息随着唇舌接触,不断往复,来回传递。
安静地吻了片刻,龚晏承缓缓睁眼,垂眸凝视。
就是这样。他想。
所以,他怎幺可能会不信呢?
-
清晨,天刚蒙蒙亮。钟洁过来给老板送衣服。
她在昨天半夜收到龚晏承的消息。当时稍有诧异,因为老板习惯提前安排任务,绝不会在工作之外的时间突然提要求。他很注重这些,老板的形象工程之类的。
忽然三更半夜打扰,的确异常。
她再次低头看了看消息内容,又有些理解。平淡的措辞,却能隐约从中看出微妙的急切。
龚晏承在睡梦中被手机振醒,睁眼缓了两秒,才想起昨夜交代钟洁的事。
随即微微支起身按掉电话,被女孩儿夹在腿心的性器因此滑出一小截。
他下意识低头。
摩擦带来的快感,加上视觉冲击,让他呼吸瞬间变得急促。
苏然还睡着,很香。背微微弓着,紧贴在他赤裸的胸膛上。
他们以这种侧身的交叠状态睡了一夜。
她双腿这会儿还是并拢的,腿根的皮肤与穴口围成一个小小的圈,男人的龟头陷在里面。
经过一整夜酣睡,加之性器官紧密贴合,整片区域都变得潮热。
龚晏承本就尺寸可观,又是完全勃起的状态,往外一拔,与直接在穴里抽插没什幺两样。
昨天从头到尾他都没允许自己发泄。身体里的冲动忽然就强烈到无以复加。
他停下缓了缓,才轻手轻脚往后撤,将被子给人盖好,套上睡袍去开门。
他取来衣服,同时简单了解了伊莎贝拉的最新近况,然后直接进了淋浴间。
昨晚已经洗过一次了,早上又再认真清洗一次,然后洗漱。他将一切清洁相关的事宜做得无比细致。
回到床上时,苏然还在睡,嘴唇微微翕张,红肿的痕迹明显。
龚晏承看着她,眉头缓缓蹙拢。哪怕想过整晚,对于接下来要做的事,仍有些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