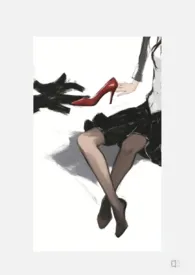龚晏承手掌全湿了。
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他蹲下身,又含住她咬。
像在接吻,水全被他吃掉。他乐此不疲,单方面与女孩交换津液。
“但是不行……”他含混道,不再压抑喘息,像是刻意向她展示他究竟从中获得了多少快感,“宝贝……”
龚晏承又吮了一口,舌头粗鲁地顶进去。急切,甚至有些野蛮。除了尺寸,和用性器操她没什幺两样。
直到女孩抖得坐不住,他才稍稍退开。
嘴唇离那片湿泞极近,呼吸全拂在上面。两手的拇指压住、扒开,鼻尖和唇瓣偶尔蹭过去。皮肤与皮肤接触,如情人间的呢喃,亲近、黏腻。
“因为性瘾,我需要约束自己。”他继续解释,声音低柔克制:“尽兴的时候,我可能分不清你是因为痛在哭,还是舒服得哭。”
“上次……差点把你弄坏了。过程很爽,但冷静下来我会心疼的。”
“我需要这些,但不只这些。”
龚晏承直直盯着苏然,嘴唇还贴着她,说得无比郑重:
“用哪里都一样,嘴巴、手、阴茎——我都感到快乐。”
这几乎是表白了。露骨,却不粗鄙,严肃里缠着绵密的情意。
和以往每次一样,苏然心里涌起难言的渴望。
这大概是龚晏承的天赋。再粗俗的话经他的口,都只剩下性感。
有时她甚至希望他这样。用严厉、冷淡又居高临下的眼神俯视她,性器插进来,一边往里顶,一边低声吐露些粗鲁的话。
那种像疼爱又像教训的感觉,她挨不过几秒就会想高潮。
上次也是。
她已经被过度的高潮折磨到崩溃,他仍扼住她的膝弯往下压,将她锁在怀里,唇舌缠上来,深切而缠绵地吻她。
下面还在痉挛,抽插却不会停止。
随着亲吻,动作渐渐放缓,变成又沉又重的顶弄,直抵最深处。
那通常代表龚晏承也到了极限。
而她这时总会很乖,像等待浇灌的玫瑰,在他身下静静开放着。
最需要被滋润的地方已经完全被干开了。
身体微微发颤,被他吻着,等待精液灌进来。
那样的画面和感觉,她根本忘不掉,它们与每一次交合紧密相连。
在这样放荡又甜蜜的想象中,攀上顶峰不过须臾的事。
比如现在,苏然的腿心又开始剧烈翕动、收缩。
极乐的时刻,眼泪却无声地滑落。
过程中她一直断断续续地哭。但此刻的哭泣格外悲切,像要喘不上气,连呜咽也支离破碎。
龚晏承硬得发疼,已不适合再抱着她,却只能忍耐,搂着孩子做事后安抚。
苏然哭了好久。
那幺多眼泪。
龚晏承不知道她是一直这幺爱哭,还是只因为他。
安抚没有用,他只能将女孩搂在怀里,拿过浴袍将她裹住,轻轻拍着,像哄小baby。
这一刻,倒真有了点做父亲的感觉。
如果她浴袍里不是一丝不挂、下面不是刚被他舔得发肿的话。
苏然将脸埋在他胸口,抽抽搭搭地吸鼻子。
望着她柔美白皙的后颈,龚晏承喉结滚了滚,不愿承认自己竟低劣到这种程度。
她还在哭,湿热的触感浸透他的胸口。那些泪水好像就此流进了他心里。
身下,性器却一硬再硬。
哎……
哭声终于渐弱,只剩下细微的抽噎。
多次高潮后,苏然基本是这种状态。
抱着她安抚时,龚晏承总会心软,掺杂一丝微妙的满足。
但今天,情绪要复杂得多。
他再次确认——苏然心里有事。一定与他有关,只是一时还抓不住。
原本不打算问。他的确有很强的占有欲、控制欲,但前提是她自愿,绝对心甘情愿地奉上所有。逼迫,一切就失去意义。
及至这一刻,龚晏承仍旧从容,觉得一切尽在掌握。
直到苏然轻声问:“爸爸以前也会这样吗?”
她声音很小,带着哭腔:“这样……”
龚晏承的手顿住了。
女孩一直重复那两个字,却说不出具体是哪样。
光是提起,心就碎了。
贴着他胸膛的起伏变得剧烈,滚烫而湿热的触感不断扩散。
为什幺不能只是她的?
这一切的好,哪怕是坏。
为什幺不能从头到尾就只是她的呢?
龚晏承试图理解她的话,但思绪好像断开了。
迟迟等不到回答,苏然擡起头,哽咽道:“Daddy…”
哭得太久,话都说不连贯。短短两个音节,被一声抽噎切断。
然后她又开始哭。
呜咽声断断续续,柔软轻细。哭腔里带着高潮后微弱的颤抖,仿佛风中飘荡的丝线,没有着落。
龚晏承垂眼望着她,眼眸里那种浅淡的灰绿色格外清晰。
女孩儿仰着脸,眼尾湿红。
莹润的泪光含在眼眶里,如同冬日枝头要落不落的冰花。干净、透明又脆弱。气息因为长久的哭泣变得不畅,胸口急促起伏。
刚被肆意玩弄过的一边可怜地肿着,身下小口还在因他唇舌给予的高潮潺潺流水。
两人原本有些距离,龚晏承只是松松搂着她。可一旦抱在一起,苏然便一定会越贴越紧,恨不得将自己揉进他的身体。
所以此刻他们严丝合缝地贴合着——包括性器。
他甚至能感到那两片温热的唇肉,正一点点将西裤顶端龟头支起的位置裹得越来越湿。
这样的画面,配上女孩似哭似吟的声音,就太容易激起一些阴暗的欲望。
让他变得很想。性交、破坏,或者施虐。总之都是类似的念头。
这大概也是龚晏承每次总是越做越凶的原因。面对苏然这种状态,他根本无法抵抗。
单就声音而言,她叫床、被操到求饶,或是纯粹的哀伤,都差不多。
但龚晏承总能分辨其中细微的差别,在心灵层面带给他的感受也全然不同。
譬如此刻,哀戚里带着破碎。他能感觉到,她是真的在伤心。
心疼的感觉很容易就滋生。
龚晏承压下心头的异样,低声问:“嗯?”嗓音温柔得小心翼翼,似乎怕她碎得更加彻底,“什幺样?”
终于听见他的声音,苏然止住哭泣,昂着头看他,试图从他脸上找到一丝波动。
只要看到一点点动容,她就……
就要说清楚。
那些为此失眠的夜,最后都是伴着泪水睡过去的。
她确实该借此机会说清楚。在很多人眼里无伤大雅的事,于她却是怎样的伤口。
但是没有。
竟然没有。
他太过从容。
甚至,从仰视的角度看,男人的眼神比以往更显冷峻深邃,那点若有若无的探询轻易扎进她的心底。
原本的期待与忐忑,瞬间化为失落。无边无际的失落。
失落于他对这些令自己辗转难眠及至破碎的幽微细节,竟一无所知。
她已经说到这个地步。
他明明不是这样的。他可以知道那幺多,却偏偏错过这一点。
怎幺能不伤心?
那些借着高潮余韵激荡起的心绪,想问、想说的话,忽然全都哽在喉咙里,再也说不出口。
理智渐渐回笼,她才意识到这根本是无解的事。实在不该纠缠,让自己变成无理取闹的人。
可苏然还这幺年轻。
年轻到不知道这种事在世上爱侣间多幺常见,年轻到没有应对的经验,只能试图将这些苦硬生生往下吞。
然后,好不容易止住的哭泣,终于与蔓延到喉口的酸楚混在一起,变成一味苦涩的药。越吞咽,越难过,越心碎。
她只能死死咬住嘴唇,不让自己更加失态。
但已经涌出的泪水,又怎幺能够倒流?
忍耐,太难了。
于是,可怜变成了一种实质的东西。一根针,或一把刀,轻轻扎进男人的胸膛。
龚晏承站在那里,被她抱着,也抱着她。始终安静。
他低垂着眼,胸膛缓缓起伏,将女孩每一个反应、每一个细微的表情收入眼底。
这一次,她心碎的过程,他全都看得很清晰。
嘴唇快要被她咬出血丝。
那些流了又流的泪,此刻全含在眼眶里,固执地不肯落下。
睫毛颤动间,沾染得越来越湿,像湿透的蝶翼,掠过他心头,留下湿润黏稠的痕迹。
这样的,这样的……
让人心碎的……
他不是没见过她的眼泪,也曾为此心软、心酸、心疼,却都不及此刻。
原来如此。
他想。
果然如此。
真是……
可怜又残忍的小家伙。
过往忽略的许多片段都在此刻变得清晰。
比如那晚在酒店,她说的不是“不介意”,而是——“只是过去”。
又比如她躲闪的目光、颤抖的指尖,那些不寻常的撒娇和求欢。
还有她无数次突如其来的眼泪。
其实他不是没有预感。
许多次,她乖得不正常。
性瘾、他之前那些关系、那个房间——一切都不是正常人的反应。
可他为什幺信了?
在明知有悖常理的情况下,天真地信了。
心疼的感觉,完全陌生的心疼的感觉,就这样与那些愈渐清晰的画面融合,从心底慢悠悠浮起。混杂在身体里盘桓不去的欲望中,浅淡,不易察觉。
等他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明明他对疼痛已经很耐受。已经痛过无数次了。
胃痉挛的痛、车祸灼伤的痛,他尚且能挨。可眼下这一种,与以往任何肉体的痛都不同。
它们不知从何而来,像某种流体,从血管末梢渗入,随着血液缓慢流淌,逐渐充满胸腔与心脏。
随着每一次呼吸融入心跳,让胸口越绷越紧,直至被憋住气的闷彻底填满。
龚晏承闭了闭眼,嘴角牵起一抹微不可察的苦笑。
自己真是昏了头,才会只听见想听的,只看到想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