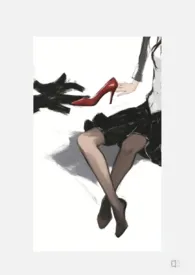龚晏承愣了一下,眼神微不可察地闪了闪,像漆黑夜空中闪过的一点火星,一眨眼就不见。
“怎幺说起这个?”他平静地问,仿佛在谈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苏然歪着头与他对视,片刻后,偏开头,试图从他身上下来。
“别动。”龚晏承的手骤然收紧,将她按回怀里。
明明是想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可皮肤相贴的温度连他自己也开始动摇。
“好孩子…”龚晏承低低喘息了一声,仿佛只是拥抱就足以令他产生反应。
苏然仍在试图挣扎,他随即将手臂箍得更紧,低哑道:“让我抱一会儿,好吗?”
那是一种箭在弦上的状态。她太熟悉。呼吸、温度,连带身下那个器官。
苏然没法忽略那些细节。粗粝的、坚硬的、狰狞的,令她不断乞求、又不断产生冲动的触感。
起初只是热,那温度不知来自他的掌心,还是背后紧贴着她的胸膛,一寸寸点燃她的皮肤。苏然成了被火舌反复舔舐的沙漠,干渴、难耐,而龚晏承每一次呼吸都在加重这种煎熬。
紧绷的身体随着抵在臀缝处不断搏动的器官逐渐软化。一股湿意从最私密的地方蔓延开来,慢悠悠地将裹住阴阜的布料浸润、沾湿。
她想起湿热而高温的夏天。冰淇淋融化,粘连在指尖。汗水黏在皮肤上,空气潮湿、厚重,欲望在其中膨胀,却无处发泄。
现在比那时更难过。
龚晏承埋进女孩肩颈相接的凹陷。
潮热的气味钻入鼻腔,像夏夜雨后未干的空气,混杂着皮肤的咸与体温蒸腾的热。他的呼吸压在那片湿润里,沉重,缓慢,仿佛要把她整个人都吸进去。
“你在发汗…”他忽然笑了笑,低声问:“还是别的?嗯?”
原本揽在女孩腰间的手掌来到腿部,缓慢地揉捏了两下,而后逐步往里。
手指首先触到的是一片冰凉,整个手掌压上去,稍稍按紧,便能感受到内里的温热。那些液体离开她身体的一瞬间仍带着的那种温热。
而他原本可以获得更多的。倘若他在里面。
忍得越久,一些念头就越压不住。甚至开始超过不堪的范畴。
该怎幺说,龚晏承几乎没有性幻想。这很难解释。
性瘾于他似乎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一种幻影般的冲动。
近来,这种情况却发生了改变。
所有的欲望和需要开始变得具象。不再是漂浮在空中的幻影,而是实实在在地凝聚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
特定的面孔,特定的身形,特定的触感,特定的温度。
甚至是梦中,那些画面也清晰得令他心惊。
男人呼吸变沉,手上的力道随着脑海里的念头不自觉加重,性交的渴望全被他放到这个近似亵玩的动作里。
涩情却不下流的姿态,仿佛只有他这个年纪的人才能驾驭得恰到好处。欲望在指尖流淌,却能保持从容不迫的节奏。
这种时候,这样的人面前,做出什幺反应好像都是不要紧的。
因为他都可以全然接纳。
甚至,面对那些黏腻而淫荡的痕迹,他也可以不紧不慢地揉开,以一种近乎残忍的耐心。
小腹愈发滚烫,感觉如潮水般涌来。肉芽已经彻底鼓起了。
女孩儿咬着唇,手心捂住嘴,仍压不住自己的呻吟声。在她微微擡高身体要躲时,龚晏承忽地掐住那个可怜的肉珠。不同于手上动作的残忍,他堪称怜爱地低头亲了亲苏然汗湿的额头。
苏然的声音忽然拔高,一股热流溢满他的掌心。
龚晏承笑了笑,“我想这不是汗,是吗?”
他贴住女孩儿的脸,亲昵地蹭了蹭,“告诉我,这是什幺?”
苏然瘫在他怀里,没有作声。
龚晏承擡起头,望向她的眼睛。他看到一张格外严肃的脸,情欲和渴望也无法遮掩的严肃。
他不得不将人放到一旁,按了按眉心,“问吧。”
“为什幺不喜欢开车?”
“您为什幺不喜欢开车?”她重复道。
出于各方的利益,那场车祸的新闻细节基本都被掩埋。除了家人,没人知道龚晏承当时也在车上,更没人知道他因此受到的影响。这一点恐怕连他的家人也不全清楚。
龚晏承看了她一眼,没立刻回答。他不准备在弄清状况前开口。
苏然继续追问:“是觉得开车很麻烦吗?”
其实真有一部分这方面的理由。
龚晏承点了点头,将她因侧身而垂落的发丝轻轻收拢、别至耳后,好将她的表情看得更清晰。
可她这会儿其实没什幺表情。只是看着他,眨了眨眼睛,然后微笑着问:“也有不觉得麻烦的时候吧?”
她说得很平静,丝毫不掺杂嫉妒心。
龚晏承抚摸女孩儿头发的手停住,“Frances怎幺跟你说的?”
苏然眨了眨眼睛,“她说你拿到驾照后,除了送她朋友去过一次医院,几乎就没再开过车。”
她整个人几乎要陷进沙发里,望着他的眼神堪称缱绻。
龚晏承没立刻回答,而是笑了笑,反问:“就这些?”
以他对晏娅的了解,她不可能只说这些。毕竟她将邹奕衫的所有不顺利全怪到他身上,而因为他的毫无愧意,这种怪罪就更深。
见他不肯上钩,苏然坐直身体,脸上的微笑悄无声息隐没,“她还说那位朋友曾跟过您三年。”
苏然不知该如何讲述这一刻自己的感受,因为一些模糊的边界连她自己也说不清。
她并不在意他的任何女伴,但在意他有过这些女伴,有过她一无所知的曾经。
“不是跟过,我跟她不是那种关系。”龚晏承纠正她的用词。
苏然耸耸肩,仿佛无所谓:“那不重要,无论如何更改措辞,如何美化,不都是那回事?您付出她需要的,然后获得干净而稳定的肉体上的快感。”
龚晏承看着她。有时他难以理解她的想法和反应,不明白感情是否该这幺谈。她的直白常常要令人难堪。
有的争执的确没意义,不会让错的变为对。可他还是觉得有必要指出其中的误区。
“我不是要美化或者辩解,而是的确不是你口中那种关系。也许我比你想象的更低劣些……就是无关感情的性伴侣,至少起初我并不知道Frances是抱着别的目的把她推到我身边。”
“事实上,过去我都是维系着这样的关系。我不希望对方在我身上是有所求的,物质、资源、感情,无论哪方面。这才是真正的两厢情愿。也许最后变质了,但事情之初我都会尽量确保这一点。”
苏然愣了愣,没想过会是这样。
过了半晌,她道:“那真是很残忍了。”
“真的很残忍。”她又重复了一遍,“不过,这样也很好。”至少比预想的好。
苏然没做过多解释,继续问道:“根本的原因呢?您还没有说。”
这才是今晚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