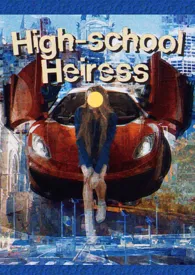19岁,出道当天,聚光灯齐齐汇聚。
舞台底下的尖叫声灌进耳膜,我站在舞台中央,汗水沿着发际线滑进领口。
现在,我是NEX7 的主唱,金正贤。
镜头扫过我的脸,萤幕放大 200 英寸,粉丝哭到脱水。
我微笑,标准 90 度鞠躬。
舞台灯一熄,掌声像浪冲上来。
我还没从强光的余晕里缓过神,就被同伴们一把抱住。
「成功了!正贤,你今天真的超赞!」
「干净又亮,完全公司那个定位,太完美了!」
摄影棚里充满香槟、自拍、笑声。每个人都在庆祝——
却没有人注意到,我的耳朵里,还残留着直播课时老师那句命令般的话:
「保持。」
好像我不是完成舞台,而是完成了一个「产品示范」。
我还来不及和大家合照,经纪人便在门口向我勾了一下手指。「正贤,过来一下。」
他语气平静,但那平静不是自然,是「职责」。
那让我背脊立即僵住。
我跟着他穿过后台。节目组还在忙,灯光师在收线,同期们在拍认证照。
我每走一步,喧闹就远一点。像是有人故意把我从光里抽离。
「我们去哪?」我小声问。
经纪人没有停下,没有回头,只说:「董事长要见你。」
一句话,让我的喉咙瞬间干掉。
「……今天?」
「嗯。」
「为什么……是我?」这句话我只敢用气音问。
我知道自己在哪个位置,也知道不该问这种问题。但我还是忍不住。
经纪人这次停下了,转过身来。
他的表情温和,但眼神没有焦距。
「正贤。」他说得非常轻,「恭喜你出道。」
他停顿了一下,「你现在,是公司资产了。」
资产。
不是艺人。
不是新人。
是──资产。
他拍一下我的肩,像在把一件东西归位。
走廊越往内越暗。最后的门推开后,是地下通道。
冷意像潮气渗上来。
那里停着一台车。黑到没有轮廓。车窗后,是看不见的深。
经纪人替我拉开车门。我看到里头坐着两个穿黑西装的人。
一个在前座,一个在后座最里侧。
后座那个擡头看我。
打量,不说话。
我突然很想逃。但我的脚就像被程式接管,只能照着预设的指令动。
车门关上。世界被切掉一半。
引擎声低沉,像兽在喉间哼。
车开上快速道路时,我偷偷看窗外——
庆功的楼层还亮着,淡黄的光,模糊又远。
像另外一个世界。
「金正贤。」后座的男人开口。
他是第一次说话,但语气听起来像早就认识我。
「这是你的荣幸。」
我喉咙发紧:「……什么意思?」
他忽然笑了一声。那笑意没有任何愉悦,只有专业惯性。「董事长很少挑新人。你是例外。你这种……」
他眼睛上下扫过我一次。
像检查某种易碎品。「……纯度,很高。」
我全身发冷。
纯度?那什么词?
他看我不说话,补上:
「公司花了很多时间调整你,你今天的舞台……董事长很满意。」
那一刻,我才明白——
多堂形象课、多次神秘的「定位」、那些视线、那些话语、那些微笑。
不是训练。是「前置作业」。
准备把某样东西交出去。
车停在一间酒店前。
比我想像的更正式、更高级、更安静。门口没有任何标志。只有黑色玻璃和沉重的黄金装饰。
像是专为不能被看到的人准备的地方。
我被带进侧门,经过一个狭长走廊。地毯厚得让脚步声完全消失。
空气中有淡淡的雪松味——昂贵,但让人喘不过气。
电梯里只有黑西装男人跟我。
他按下最高层。指尖干净、毫无颤抖。「到了要记得鞠躬。」他不看我,「还有,别说太多话。董事长喜欢……安静的。」
安静的。
像我这种被训练成「柔软、乖巧、纯白、易塑」的安静?
电梯门开时,我汗已经湿透背脊。
顶层只有一道长廊。尽头是双扇木门。
厚重,像隔着另一个气压。
黑西装男人替我敲门。
门被拉开。
里头灯光柔得像雾。
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人,而是空间——
一张过长的桌、一个太深的沙发、一片看不清夜景的落地窗。
整个房间就像用来吞下一个人的。
然后,我看到沙发上的男人。
董事长。
他没有起身,只是擡眼看我。
视线落在我脸上停了一秒,接着扫到我的喉结、肩线、手。
就像……
就像我不是人,是某种被测试品质的东西。
黑西装男人在我身后轻声提示:「问候。」
我立刻鞠躬,声音发抖:「董、董事长,您好。」
他擡手,示意我靠近。语气沉稳、有压力,不容拒绝:
「你坐过来。」
我走向沙发时,脚几乎不是自己的。
一坐下,他的视线又落回我脸上。
董事长坐在沙发,雪茄烟雾缭绕。
他擡眼,先是欣赏,目光像温水,从我西装领口滑到腰线。
指尖轻敲沙发扶手,「漂亮……但不够。」
那是一种审视。但比所有镜头、老师、企划的都更赤裸、更直接、更毫不掩饰。
「你很干净。」他说。
我僵住。
他像在自言自语般继续:
「公司那群人……很会雕。」
雕。
像作品、像模型、像货品。
我的指尖蜷紧。
他忽然靠近一点,语气轻得像在聊天:「你第一次直播,我看了。」
我心脏骤停。
他淡淡笑了:「你很乖。」
我胃整个收缩。那是命令,不是赞美。是「确认品项特性」。
接着,眉头微皱。
「不对。」
他起身,走到衣柜,拉开抽屉。
里面是一件白色雪纺连衣裙,蛋糕裙摆短到仅能勉强盖住大腿根,「换上。」语气平淡,像在说「把外套脱了」,语气温柔,却不容拒绝。
我僵在原地。
「会长……这是庆功宴……」
「庆功宴结束了。」
他把裙子丢到我脚边。
「现在是我的时间。」
他把酒杯放在侧桌上。
下一句语气平稳柔和,却让我全身冰冷:
「今晚,你只要安静就好。」
我的呼吸完全乱掉。
喉咙像被掐住。他往沙发深处靠,像在欣赏某种终于送到手的东西:
「正贤,欢迎你正式成为公司的人。」
不是艺人。不是新人。是「公司的人」。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
舞台上的光不是给我的,是给他们确认——
这个塑好的形状,是否能顺利送出。
而现在我在这里,就是因为那个形状「通过」了。
我坐在他对面,背脊笔直,手指发抖。
我的脸仍微微带笑。
因为我知道——
在这里不能露出任何不适。
否则,所谓的「塑形」会变成「改造」。
他举起酒杯,示意。
「来,正贤。
出道的第一夜,要记得。」
我擡起头,看着他。
我的笑维持着。
但我眼里的光正在熄灭。
因为我终于、真正明白:
出道不是开始。
是交付。
是成为某人的东西的那一刻。
我站在更衣间的镜子前,抖着手脱西装。
西装布料滑下时,我的尊严也随着剥落。
洋装布料贴肤那一刻,镜子里的我,像 12 岁试穿礼服那晚。
裙摆扫过大腿,像母亲当年说的:
「俊熙穿起来,比女孩还漂亮。」
我擡眼,镜子里的女孩,睫毛被刷得湿润,唇色淡得像初雪。
不是金正贤,不是朴俊熙,是某个从未被允许存在的自己。
胸口一阵酸软。
不是羞耻,是认不出来。
像终于穿上梦里的衣服,却在最错的场合。
董事长靠在门框,点了根新雪茄。「转身。」
我转身,不敢擡头看人。他眯眼:「嗯,这样才对。」
裙摆扬起又落下,
像一朵被风折断的白花。
他走近,雪茄味混着古龙水,像一道逼近的阴影。
指尖捏住我的下巴,擡起,视线只停留一瞬——像确认交付单上的品项:
「嗯。实物比照片干净。」
他随后后退两步,从上往下扫过我全身。
那不是欣赏,是无机质的检视,像在确定形状是否符合预期。
「现在,你终于变成我要的样子了。」
他拉着我来到床前,轻轻一推,把我推倒,裙摆掀到腰际。蕾丝边缘勒进皮肤,
像一圈细细的锁链。
「唱。」
「……什么?」
「用女音独唱你的出道曲:祈祷天使的降临。」
我开口,声音发颤:
「像天使一样飞来……」
他解皮带,拉链声盖过歌声。
「继续唱。」
他俯身,唇贴在我耳后:
「再软一点。」
歌声变成尖叫,再换成哭声。
当阴茎抽出正贤体内,精液射在他脸上时,董事长低笑:「这才是真正的庆功。」像在为一幅画作收尾。
结束后,我来到浴室,跪在马桶前狂吐。
镜子里,
天使妆容沾满白浊,裙摆被揉皱,像被撕碎的翅膀,羽毛沾满精液。
我用指尖碰了碰裙摆,
布料还带着体温。
胸口一阵刺痛,不是脏,是心碎。
原来「被看见」可以这么痛。
手机震动:
「以后随叫随到,酒店见。记得换女装,这是你的新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