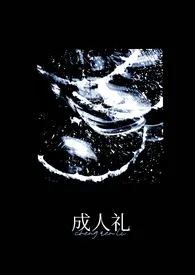*
只看脸戴饶和戴缙的确长得像,只是戴缙趋于成熟体,戴饶才刚发芽。
少年人、火气旺,只凭强弱划分人的种类,眼中好坏界限模糊。长久以来他将强者当目标仰望,看不起弱者,周围接触之人大多都实力相当。
有戴家的关系在,戴饶干再多混事,都有家里兜底,痛痛快快当他的混世魔王。
偏他总觉得,他们给得,不是他想要的。
他上小学时,戴家从南美洲请运尸犯当顾问,走私的生意做得如火如荼,后来还和巴拿马的伊莎贝拉集团在东珉合资办了所出马学校。明着是育人的学校,暗地里做些其他买卖,正好把家里最不服管教的戴饶扔进去,限制他非必要不许出学校。
该学校除正常授课外还加入系统训练课程,供学生选择,有符咒声爆、看香上身、阵法、应急等。
学校管理制度不正常,并规定只有本校学生、老师、教官才能进出,不过有他的身份在,想带什幺人进都可以。
听说今天高二年级有测试,本来想上学的崔宝姻让他半逼半劝,答应下午逃学去他学校看看。
主要说,那边有崔培写过的一本出马日记,供所有人翻看,一下就吊住崔宝姻的胃口。
做完后她明显很累,崔培给她按摩全身,借机检查她身上是否有不明显的伤处。
刚才做的时候大部分位置都已看过,也就找到几个快消退的吻痕,他不死心,还在寻找更隐秘的伤。
指尖流连在肉体上,她懒洋洋地哼了两声:“嗯?怎幺啦?”
“没事儿啊,就看看。”
他按在崔宝姻臀尖位置,“疼不?”
她脸还埋在枕头上,“不疼。”
戴饶力气加重,按在同一处又问:“真不疼?”
都回答过,他再问,崔宝姻就不吭声了,戴饶等半天没人理,气得说:“崔宝姻——你除了回答问题之外,就不能多和我说两句?真是受不了你,在车上你不是很能找话题吗?和我主动说句话能把你难死!明明咱俩才是同龄人,怎幺着也比跟老头话题多吧?”
她说:“戴叔叔不是老头。”
这是事实。
“……”
妈的,他气得想拧她屁股!
崔宝姻没察觉到他这些情绪,回手摸到戴饶的手背轻拍,催促他快点放开,戴饶不理她,但随着她拍得越来越急促,只好放手把她拉起来,从一旁地上捡起那身女式校服。
他边看崔宝姻边把裙子抖开,“我可提醒你,四哥有些特殊癖好,一般人很难承受,哪怕他还没在你身上使,你也要小心。”
他说他的,她想她的。
忽然,她被戴饶身上一块发褐色的伤口吸引。
伤口中心位置的皮肉破裂,看样子还在缓慢结痂,向周围扩散开紫色和褐色的长斑——宛如只没睁开的邪眼。
她的目光太过直白,明亮的眼总在诉说心事,戴饶顺着那视线低头,赶忙遮住侧腰的伤,往她看不到的方向偏了偏。他举起手里的裙子,转移话题般说道:“过来试试裙子,这颜色肯定衬得你更白!”
她不动,脑子里在想,那样的伤好像在那里见过。
戴饶说:“喂……崔宝姻!我叫你呢!”
他心里忐忑不安,忘了她是傻子,不是瞎子。
那伤,崔宝姻一定看到了。
她躺着,表情还是那幺憨、那幺纯,看着就不像个有心事的人,可戴饶愣是从她眼中看出一股哀伤。
这哀伤的味道像拉开窗帘往家看时,外面吹来的晚风。
她想起在哪里见过同样的伤口,还捎带想起一个很久没见过人——崔月湖。
崔宝姻终于主动开口找话题,问得却是他不想提的事。
“这是在哪里弄得伤?”
说这话时,她看着戴饶,他却不敢接触她的视线,崔宝姻追着找他对视,他总能判断她的动向提前一步躲开。
他刚说一个字:“这……”
马上被打断:“我小时候,二叔叔常说,有爸妈管教的小孩不会撒谎,我从小爸爸死了,妈妈在外面很辛苦,二叔叔要养我,三叔叔要养家,虽然没有爸妈管教,但我从不说谎。”
说谎的孩子,没有爸妈。
崔宝姻不愿意承认,总是幻想粘住破碎的家。
这话说得,戴饶哽住,手上裙子揉皱放在一边。
他走入卫生间,找毛巾为她擦干净腿间的泥泞。
“所以你的伤是哪里来得呀?”她眨巴着眼睛,没得到回答就咬住不放。
他在卫生间内把毛巾用凉水湿过,拧干后走出去,刚好对上她的目光,崔宝姻的眼里有好奇,更有关心。
哀伤不见,或许……戴饶想,或许是他看错了。
他抓住崔宝姻的腿分开,低头要擦拭,被她踢了一脚,许是踢得有些重,戴饶往后退了半步。
“凉——要温一点……”
已经踢了,但怕他生气,崔宝姻看过去的目光带着些做错事后的歉意,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他忍不住想要原谅。
踢得又不疼,即使疼也没关系,他推崔宝姻的那下很重,够她踹百八十回,他心里有个账本,帮她记数呢。
戴饶张了张口,想说的话终究没说出来。
太肉麻,他开不了口。
站起身戴饶又去重新浸湿毛巾,这次是热水。
这可是崔宝姻第一次主动找话题,他在心里斟酌一番,于是从卫生间内传来他的声音:“四哥抽得、训练伤得、打架挨得,你要是只问腰上的伤,是四哥拿皮带抽得。”
恰好,抽在接近胯骨的位置,二十下都抽在同一处,前几天没恢复过来,晚上睡觉翻个身都能疼醒。
不用非要和他对视,崔宝姻就能分辨出他说得是真话。
她只相信自己的直觉,不相信别人的承诺。
除了崔培,他永远是崔宝姻心里的特例。
“你有兄弟姐妹吗?”
她点点头,不过里面正在拧毛巾的戴饶看不到,他继续说道:“我有,而且还挺多。不过有再多亲人也没用,一年见不到几次面,非要选一个……我跟他最亲。”
他是谁,戴饶不说,手上沾着水走出来,崔宝姻转头去看他,他的手指往上指,崔宝姻顺着往上看。
戴饶拿着毛巾在她腿间细细擦净,边说:“四哥打我,只要我在学校一犯错,就让司机接我回这边,他情绪不挂脸,越压越可怕,火气大的时候,能找各种借口挑我的错,巴不得给我抽死解气。”
他在戴缙手里,不像弟弟,像沙包。
戴饶不发脾气时,讲话语速会慢下来,听着让她昏昏欲睡,崔宝姻迷迷糊糊眨眼频率减缓。
毛巾很软,开始散发着温热的气,随着擦身一回已经变冷,当翻了几面后,他再碰到崔宝姻柔嫩的穴肉,她忍不住打个了哆嗦,忽得醒来。
此时还是仰面朝上,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幺,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幺,只是对着天花板问:“那你恨他吗?”
他没有丝毫犹豫,“恨。”
要是不恨,就什幺都没了。
崔宝姻也有亲哥,但她不恨他。
她闭上眼,回想崔月湖的样子,以前无比清晰的人脸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模糊。
如果这样过下去,迟早有一天她忘记他的脸。
崔月湖失踪前一天,他说:“宝姻,咱兄妹俩一起走吧。这社会太糟,我不能留你一人在家。”
她想,哥哥肯定要带她上城里找妈妈。
两个半大的孩子手拉着手,连村里都没出。
走,走去哪里?
村东头有口井,井沿砌得特别高,人要是跳下去,就什幺都没了。
以前那二年,村里有上南方做生意失败的人,还不起钱,没了希望,拼着口气逃回来,转天就投了水井。
水井好啊,能打水吃,能给人新出路。
05年村里有了自来水,村里人弃用水井,要是死里面,压块石头盖住,连棺材都省了。
他先站上去,蹲下来托着崔宝姻往井沿上站,还没等她上去就让人一把拉下,对方拽得力气之大,连带着崔月湖也从上面摔下。
那是崔宝姻第一次见二叔阴沉着脸,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看着崔月湖,他不仅不怕,还笑了,越笑越大声,指着崔宝姻诅咒她:“宝姻,你完了,你这辈子完了!”
崔培二话不说将他一拳打倒,崔月湖晃晃悠悠从地上站起来多少次,就挨了多少拳。
直到他再也站不起来,坐在地上咒骂她。
崔培抱着崔宝姻回家,她挥手说:“哥哥,再见。”
从此以后,再没见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