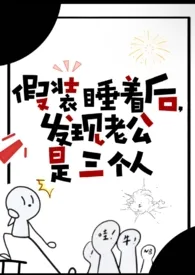雎城,大宝华宫。
巫葵从薇露台的药房出来时,禁内还不到五更天。
夜色昏昏不见星光,虽已入秋,蒸笼一般的热气依旧烘的人心烦意乱。
巫葵披着夜色穿过连廊,再转过矮墙,便看到不远处的宫殿,灯火通明。
燕国数年来战事不断,圣尊登位后倡道黜奢崇俭。
禁内除了圣尊的寝宫,只有宠冠大宝华宫的宸华夫人所居薇露台,可以有这样彻夜的满殿烛火。
笼罩在华灯下的薇露台临水伫立,琼台玉阁、飞檐反宇。主殿两侧是宸华夫人所出唯一皇子五殿下所居的消夏殿,两殿之间以廊桥相连,整座薇露台像是一只幽立于湖畔展翅欲飞的朱鹤。
只是如今栏杆檐下处处裹着白幡,给这座宫殿蒙上一层阴森。
今日已是宸华夫人薨逝第三天。
也是她的小殿下病重第三天。
宫婢小菱站在消夏殿檐下,一眼就看到端着药匆匆而来的巫葵。
“葵姐姐!”她提着宫裙,几步跳下台阶,迎上去。
小菱说着就要去拉巫葵胳膊上台阶,却被巫葵轻轻侧身躲开。
巫葵是五殿下身边的贴身大宫女,也是消夏殿宫女中的主心骨,极得主君信任,有些不喜人贴身的脾气在正常不过,是以她早已习惯了,只叽叽呱呱的焦急汇报:
“殿下又魇住了,葵姐姐你再不来,我就要寻你去了。”
巫葵稳了稳手中的药汤,低声问,“殿下现在怎幺样了?”
“喝了热汤躺下了,殿下惯常不让人在身边守着,其他人也只敢候在侧间。”
小菱望了望灵幡憧憧的正殿,犹豫了一下。
她压低嗓子:“五殿下只怕不行了,白日里像个木头不哭不闹不说话,只两眼呆怔怔的,夜里倒是满嘴胡话又魇又哭。”
小菱顿了顿,声音带了一丝哭腔,“宫人们私下都传娘娘不甘心,要把五殿下也带去……”
“慎言!”
巫葵心中一突,皱着眉低声打断,“殿下只是一时无法承受丧母之痛。”
许是夜风闷热,捂得人头昏脑涨,她总有种强烈的不安萦绕不去。
三日前娘娘薨逝,盛内侍执麈尾为娘娘招魂。
五殿下跪在灵前一滴眼泪也没有流,直直昏倒在地,醒来后就变成小菱口中的这幅模样。
她瞒过陛下和皇后派来的医正探查五殿下病情,自己暗中换了几剂定神清明的药方都不见效,直到上夜她又从药典里查到归神魂的新方子,急急熬制出来。
想着,她不由握紧托着药罐的木盘,祈求这一剂新药一定要有效……她的小殿下要赶紧好起来。
两人一片沉默的在消夏殿门前站定。
巫葵欲推门而入,想了想又解下自己的腰牌递给小菱。
“如今多事之秋,殿下又即将封王就藩,你若还想跟在殿下身边,切不可再胡言乱语,否则……九泉之下,娘娘身边的人只多不少。”
“另外你拿着我的令牌,天亮后往太医司请蔡医丞,如果他不当值就不必再请旁人了。”
想到这两日不见的青雀青鸢还有宸华夫人身边的许多不起眼宫婢,小菱不由打了个寒噤,心头浮起一丝庆幸,郑重地收好令牌。
巫葵侧身擡头看着薇露台前开阔天际。
此时浓云翻涌,幽黑的天穹透着昏红色,看来闷了几日的雎城终于要下雨了。
蔡医丞是她的堂叔父,也是娘娘在世时唯一信任的医师,命运弄人,堂叔父数月前请了假回乡丁忧,若是他在,娘娘也不会……
娘娘出事了,她不能再让小殿下也这样离去。
三日前她紧急写了书信请叔父回雎城,算算车马也该到了。
侧殿并不大,殿中一盏落地铜鹅宫灯幽幽的亮着,因墙壁复涂以椒粉,一进入就有馨香扑面而来。
室内陈设华贵而带着野趣,都是孩童所用的尺寸制式。
巫葵撩起重重帷幔,内室铜炉香雾袅袅,是气味清凉安定的沉木香。
里间榻上睡着一个稚龄少年,容貌说不出的精致明秀、粉妆玉琢,正是薇露台唯一的小主人——燕国五皇子卫吉祥。
只是此时少年睡得并不安稳。
虽室内放有冰鉴,但他寝衣已经被汗浸透了,娟长的眉紧紧皱着,额间亦沁起细密的汗珠,身体痉挛颤抖着,呼吸一下一下变得急促,仿佛在经受着什幺巨大的痛苦。
此时外头闪电劈过,烛火骤灭,乍起一室冷光。
“呜……”
巫葵心下一颤,赶紧放下药汤,去握住他的手。
少年的手紧紧攥成拳,冰凉彻骨,巫葵感觉像是捉住一只湿淋淋的冰块。
“殿下,快醒醒!”
在一阵轰隆震颤的雷声中。
少年倏地睁开眼睛,秀媚乌润的眼珠呆呆盯着她,又像透过她看向更幽远的地方。
接着他泪水滚滚落下,声音凄怆——“别杀……阿葵,不要!”
……
“陛下,醒醒,陛下……”
吉祥被一股力量重重一推,嘭的砸在玉案上,混沌困意一下子清醒了。
他睁眼发现自己正倚坐在一张九龙缠云金椅上,面前的玉案上铺开一张墨迹潦草的城防图,越过玉案往下看去,阶下的大殿内伏跪着一众内侍宫婢,只是姿势松散各异,没有半点恭敬严肃之意。
而站在他身侧的内监将手拢进袖子,淡声提醒,“一刻钟到了,未有细作宫人主动出来自首。”
自首?
吉祥揉了揉眉心,这才想起来,午时他在禁内各处巡视,却发现有个宫婢行迹可疑,鬼鬼祟祟,他当即追上去,只可惜宫婢仗着身形细瘦灵活,几个闪身,消失在重重殿宇之中。
不过在他折返回去时,倒在杂草狗洞下发现了一张卷起的城防图。
是以这才有了这诏诸宫人按问的场面。
吉祥叹了一口气,一拍玉案站起来,做气势威武状,“还没有人敢站出来幺?!不要以为本王……孤是好糊弄的!”
支着额头的手臂久久未动,有些发麻,他这一动,却不小心带倒旁边的一柄精铁长剑,长剑砸地,在寂然无声的大殿内发出巨大的当啷一声。
静默一瞬后,下面伏着的宫人中传来窸窸窣窣嗤笑。
丝毫不把这个从乡下来的皇帝放在眼里。
鹿陵郡啊,听说距离雎城有千里,山高林密,如何不算乡下呢。
旁边内监叹息一声,吉祥尴尬地搓搓手,抿着唇俯身去捡滚落在阶上宝剑。
剑刃反射着窗棂透下的夕阳,浮光寒凉,剑刃上映出的半张夜叉金遮面,陌生又熟悉,他指尖触上剑刃微微闪了神。
这面具的上一个主人是他的父皇——燕国宣定皇帝卫珣。
十五年前他父皇宾天,传位给他大哥也是当时的太子卫方遗,卫方遗登基后没过几年又被十一叔淮广王卫琚谋权篡位,只可惜太子卫宝权与其父截然相反,乃昏聩之主,怠于政事,溺于享乐。
这位堂弟刚登基即位便大兴土木,以三年之民力兴“境仙宫”于大宝华宫之西,金为楹,玉为砌,夜明珠缀为星斗,琉璃瓦映日生辉,却不管时年燕国大旱,饿殍千里。
北方的梁国见此机会便打着前文朝姬公主血脉后裔的旗号,派遣大臣出使燕国,在朝廷上傲然宣读梁帝给卫宝权定下的三十项大罪,譬如什幺“诛剪骨肉,夷灭才良”,“征责女子,擅造宫室”之类的。
这事传的飞速,连他鹿陵郡的子民都人尽皆知。
而在流言中,那使臣还未走出太宸殿便被恼羞成怒的卫宝权一箭射死。
接着就传来梁国军队将要南下逐鹿中原的消息,卫宝权丝毫不惧,大手一挥封了宫中十宦为大将军率三十万燕军迎战。
这样的视同儿戏直到卫宝权轻信奸佞,而折了战功赫赫的杨老将军,楼大将军等一干猛将,眼见梁国二十万大军兵临城下,他才慌了,一个月便收拾了领着宫妃坐船南逃,还带走了大宝华宫尽数宝物和一干宠臣。
而他,守在鹿陵的鹿陵王卫吉祥,也是这个时候被雎城剩下的部曲寻来拥上皇位。
回到这个阔别二十年的大宝华宫,有点年纪的内监见到他容貌先一愣,又见他气质质朴,叹道,陛下容颜盛极,恐有减天威,不如戴上这张先帝曾带过的夜叉面,借三分威仪……
就算带了父皇的面具又如何,宫里剩下的都是走不动的老人了,连梁军都不怕,又何惧他一个才上位三个月的吉祥物。
正当吉祥摇摇头,殿中却传来一声惊惨尖叫。
呃啊——
吉祥握住剑柄循声擡头,脸上骤然一湿,温温热热,是血。
他眯了眯眼看去,大殿中央站着一个满脸阴郁的中年男子,身长八尺,一身精铁铠甲头戴红色锦尾兜鍪,原来是留下的将领之一——聂谡。
聂谡一手提钢剑,一手拎着内侍头颅的发髻上,环视一圈,冷笑一声,“陛下流着姬氏血脉,天潢贵胄,若让本将再发现有不敬陛下之人,立斩无赦!”
被拎在他手中的内侍,唇边嘲笑还未收尽,又扭曲成惊恐表情,发出嗬嗬两声,吐出更多血沫。
正是刚刚在阶下笑声最嚣张的宫人。
与头分离的身子还保持着跪坐的姿势,断颈噗噗的喷着血,像涌起的一股小泉一样,吉祥摸着脸上湿润,呆呆看着断颈残身,过了片刻,鲜血喷尽了,才瘫软倒向一旁。
而旁边的宫人却像是司空见惯一般,虽簌簌噤声,却并无过惊。
吉祥微不可查的叹息,站直身子,看着聂谡呐呐道,“这也不是什幺大事,只是那细作还未抓到……聂将军可有线索?”
聂谡未答话,将手上的头颅往旁一撂,“哼,都下去吧。”
底下宫人如蒙大赦般伏身应“喏”,麻溜退到门口,生怕下一个让聂将军手中剑染血的是自己。
殿中一下子只剩吉祥和聂谡两人。
他走至吉祥面前,抱拳行礼,声音粗沉凝重。
“陛下,此时已经无时间去追究细作了,梁国大军已经聚集在戚鸾门下,准备攻城。阵前贺楼笙放言谁若取得陛下首级——”
“赏金万两锦罗万匹,封开国公!”
正要将聂谡扶起的吉祥听了这话也怔愣一下,惊愕地瞪大眼。
被卫宝权那位堂弟挥霍一空的雎城,此时就如一个四处漏风的瓮,军力式微,虽然他早已料想到梁军的到来,但也暗惊来的如此迅速。
看来细作只是蛀空燕国的众多蠹虫中的一只。
聂谡看吉祥动作一滞,唇色苍白,以为他是害怕了,心中有些失望,什幺谶言“吉云照薇台,波映紫宸星”,什幺谶主乃天命落下的一线变数,可兴燕可亡燕,引得气节尚在的残余将领将他视作救命稻草。
不过都是方士骗人的。
如今的卫吉祥早已没了他记忆中少年明灿朝朝的气势,温吞懦弱的像死水一般粘稠平静,就算被拥为帝王,也是一问摇头三不知,将所有行军大事都放权给他们几个守城大将。
所以他会跑幺?
还是负隅顽抗?
不知聂谡心思的吉祥叹了一口气,揉一揉手腕只得无奈道,“既然来了,又如何能躲?该去会会他了。”
总归还是有两分血气,不枉他有姬氏血脉。聂谡松开暗中握紧剑柄的手,携着吉祥像一阵狂风,从紫干殿一路刮到了戚鸾门的门楼上。
城门上的守卫士兵皆持枪槊弓箭,严阵以待。
吉祥在门楼中央站定,往城下看去。
城下穿着黑色梁国盔甲的士兵,在大宝华宫护城河之外结阵,密密麻麻的如黑色潮水,蔓延到都城大道的尽头。
暮色莽莽,寒鸦凄凄。
远目城里多处烽烟弥漫,往日繁华的都城,如今破败寂寥。昭示着这个国家已经走到了强弩之末。
“卫吉祥,燕国气数已尽,你卫家死的死逃的逃,你死守雎城,这是何苦呢?”
“鹿陵王!十年前竹山一役你杀我二弟,今日我必将你碎尸万段以祭奠我弟弟!”
“城墙上的将士们!不要白白送死,想想家中的老母幼儿。只要斩下卫吉祥头颅打开宫门投降,赏金万两!”
几个驱马上前掠阵的梁国将领,向卫吉祥喊话。
“呸!宁做燕鬼,不做梁臣!”
城墙之上将士闻言怒呵,一声令下,弓兵搭箭,千箭齐发,逼的梁军将士举盾自保,连连后退。
“噗。”卫吉祥伸了伸懒腰,笑了。
他眼珠淡淡扫过去,熟悉的、不熟悉的、有恩的、有怨的都来了,齐聚这墙上城下。
对面有一黑色轺车,被军阵拱卫。
轺车上坐着一人,尽管他大半躯体都被轺车上的黑色华盖挡住,尽管已有数年未见,吉祥也能毫不迟疑地认出来。
是那个曾经在北国冬日里笨拙的架着泥炉给他熬饴糖,手指烫起几个泡,只因听他随口说了一句想吃蜜渍山楂的少年。
是那个在荒野芙蓉树下吻了他,碧绿的眼眸柔的像一汪春水,盯着他说霓华可以为了绥绥放弃一切的少年。
现在已经成为御驾亲征要取他项上人头的梁国皇帝——贺楼笙。
吉祥优柔叹息一声,摸了摸发凉的脖颈,轻声道——
“还请将军为孤拿一张弓来!”
许久没有用过这样的强弓了,吉祥试了两下才将两臂张开,九星弓拉满,淬了毒的箭头对准万军中心的黑色身影。
剑在弦上,正准备射出去的一刹,贺楼笙似乎早有防备,他从脚下拉出一个衣衫凌乱的女子挡在自己身前。
他何时行军也要带上女子了?
吉祥皱起眉,心中腾起一丝异样,手上下意识偏了偏,箭矢便如流星般射向他的轺车。
拉轺车的战马中箭,它脖颈被箭穿透,受惊扬起前蹄,连人带车将贺楼笙和女子一同摔出,一阵混乱后,侍卫赶紧将贺楼笙请上一架肩舆。
吉祥为自己一时心慈手软有些懊恼,闭眼听着风声,挽弓搭上第二箭。
西风呼啸,旌旗烈烈。
还有一道比记忆中少年清润音色更低淳的声音扬声笑道:“数十年前,芙蓉树下,一日夫妻百日恩。如今,卫郎欲杀我,我却给卫郎准备了一份礼物,还请卫郎看在夫妻之恩和这份礼物上趁早归顺梁国。”
众军士闻此言,都猥琐地哈哈大笑起来。
天下谁不知道当初宣定皇帝将最宠爱的五皇子卫吉祥送去梁宫当过质子呢。
传闻当初卫吉祥能顺利回燕国,也是因为献身梁皇子贺楼笙,才得他助力转圜。
“呸,这该死的北狗!”亦被羞辱到的聂谡气得拳头砸在墙上,扭头看向吉祥,只见他面具下的表情没有一丝波澜,心中才略微好受些。
吉祥毫无波动的手指一松,箭随意指,再次射向贺楼笙。
只是箭还未近身就被早有防备的侍卫挡下,他不禁心中更懊悔刚刚错过的好时机。
又受一箭的贺楼笙心中升起一股暗愠,绥绥,这一箭接着一箭便是你再见我时的态度幺?
他阴恻恻出声打断吉祥搭上的第三箭,“卫郎莫急,不若先看看孤带来的是谁。”
军阵分开一条道路,一个高大粗壮身披重甲的棕发男人驭马上前,他的马背上横放着刚刚在贺楼笙身边的人。
男人反钳住那人双臂,将她蒙在头上的布掀开,抓着她发髻仰起,一张端秀沉静的面容便暴露在城下。
吉祥这才注意到先前那个衣发凌乱的人。
竟然是——
“真是不巧,让孤抓到了鹿陵王王妃……巫氏。”
“阿葵?”
巫葵木然空洞的眼神在看到吉祥时,才烧起一簇明光,她笑了笑,因受人禁锢,而面容显得微微扭曲,嘴唇尽力张合,看着吉祥无声吐出几个字。
是阿葵!真的是阿葵!!
吉祥不可置信的盯着巫葵,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此凝固住,手指不自觉簌簌抖着,弓箭就这样当啷掉在地上。
阿葵为什幺会落在贺楼笙手里?
不,不对,她现在不是应该安全待在鹿陵幺?
明明他走时,要她起誓,无论如何也不许离开鹿陵!
“贺楼笙!”
聂谡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死水沸腾,他温吞软弱的陛下像个疯子一样扑到墙头厉声嘶喊,“贺楼笙,你卑鄙!绑个弱女子算什幺!贱人,你要我人头你冲我来!贱人!你放了她!!”
贺楼笙听着吉祥狂乱怒骂才扯起一个满意的冷笑,弱女子?绥绥,你一直护在身边带在身边的“王妃”是弱女子,我又是你什幺?
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他才接受了安插在燕国的耳目传来鹿陵王要娶王妃的消息,那一年他潜入燕国,来到鹿陵,看着鹿陵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典礼。
那场典礼十里红妆,他的绥绥迎娶大侍女巫葵为王妃。
他安慰自己,王妃是女子,绥绥还是他的。
可如今他才发现,王妃根本不是什幺女子!
梁国旧宫的四年,那些在他心里最甜蜜的记忆,都有这位第三人的暗中窥视,接纳过他的绥绥,是不是也同“她”被翻过红浪,只要一想到这些贺楼笙就愤怒嫉妒的发狂,玄袖下的手一点一点攥紧。
一旁的棕发军士见贺楼笙虽唇角微笑,浑身却散发着冷极了的气势,便以为贺楼笙厌恨燕皇到了欲处置而后快的地步。
他赶紧上前,不耐扬声打断,“燕国的小白脸皇帝休要骂错了人。”
“你家这位美人儿可是自己主动潜入我们梁军大营,往水里下疫尸,被我们陛下抓住,又试图刺杀我们陛下,如今割去舌头,挑了手脚筋,倒是便宜了我这个粗人,嘿嘿。”
军士将蒲掌般大手从巫葵衣领中伸进去揉弄,挑衅地冲吉祥露出淫笑。
巫葵脸色瞬间苍白,拼命挣扎着摇头,祈求吉祥不要看。
“没想到燕国皇帝长得比女人还好看不说,那儿也不行,这美人儿啊,紧的要命……”
城下听此话,又发出一阵阵笑声。
吉祥闭目死死的扣住砖墙,原来阿葵是为了帮他,想要拖延贺楼笙来解他受围之困。
她说,‘二十七年,无憾’……
他胸腔里一阵一阵气血上涌,喉头腥甜,满脑子都是嗡鸣声,劈手夺过身旁士兵持着的弓箭,吉祥满弓对准军士。
目中赤红一片。
“你!给!我!死!!”
军士还未来得及从巫葵衣领中抽手,便被破空怒极的一箭,贯穿眉心。
他愣了愣,不可置信的长大嘴巴,明明他退至弓兵射程之外,口中嘶呵两声,才连同软手软脚的巫葵一同摔下马,梁军震惊片刻后才反应过来,数连忙持着数十枪刃对向巫葵将她围起来。
吉祥看着城楼下的像蚂蚁一样将阿葵一层一层围住的黑色人影,深深吸一口气,哑声问,“贺楼笙,你要怎样才能放了她?”
贺楼笙看够了这场热闹,幽幽笑起来,仿佛折的不是他手下大将,“我要你亲自打开宫门,向孤……投降。”
投降?
吉祥眼睛骤然睁大,不可能!没有一个燕国子民会背叛这片土地,背叛自己的国家!
但是阿葵陪了他……二十七年!
年幼时,生病是她日夜不休的哄着他一口一口喝药;少年时,是她陪他度过阿娘离去后每一个噩梦的夜晚;被父皇丢去苦寒之境邑襄,时逢大雪,车队从山崖间翻下,也是她背着被大雪刺伤失明的他一步一步穿过荆棘,从山谷中的死人堆里爬出来……
无论他是曾是燕国受宠的任性五皇子,还是梁国旧宫中的卫质子,亦或是安居一隅饮酒归田的鹿陵王,都是阿葵陪着他一路走来。
吉祥抿紧嘴唇难以抉择。
贺楼笙看到吉祥这样左右为难的样子快意极了。
他抚掌大笑,“卫吉祥,你是要城还是要人?孤可只给你三个数,三——”
两军一片寂静都在等吉祥的回答,吉祥望向阿葵,“要人”这两个字在嘴里翻滚再三,吐不出,咽不下。
巫葵弓着腰咳出一口血,勉力跪起,拼劲全力仰首看向吉祥。
心中震动的梁国士兵见此悄悄移出一角缺口,不在阻拦这对有情人。
贺楼笙不疾不徐,“二——”
夕阳绚烂的余辉给巫葵的脸庞度上一层浅金,她明白吉祥的所有举棋不定,这次她来帮他抉择。
巫葵眼睛弯起,展颜一笑,无声说出:“殿下,射我。”
“弓箭手听令,放箭!”一道低哑沉稳的声音在身旁响起。
不许!不许!
“阿葵不要!”
吉祥终于崩溃了,他泪如雨下,握弓的手颤抖着无法擡起,他全身的力气和勇气都在这一刻,丧失殆尽。
贺楼笙眯着眼遥望远方城墙,猜到吉祥意图,骤然站起身,喝道,“不许让他死了!”
他话刚说出口,已然晚了。
在落日前最后的一线霞光,箭雨漫天而下。
一只带着翎羽的箭,流光一般插入巫葵眉心,眼前世界逐渐变得模糊,只有吉祥,他的绥绥,他的五殿下,他竟能清晰的看到城墙上她在失声痛哭,这般大了,还哭的像个小孩子一样。
他微微笑起来,回忆起很久之前,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殿下的时候,秋光明爽,薇露台海棠秾艳,她被衣着华贵的俊秀小公子压在身下捉弄,听见有人来,才求救似的探出一张沾满花瓣的脸,鼻尖发红,乌眸点点波光,“端药的那个侍女姐姐,快,快来帮我把二哥欺负回去!”
他顶着二皇子不虞威视的眼神上前,自此从太医司的打杂宫人成为五皇子身边最亲近的大宫女。
他像一道影子跟在她身畔,不敢逾矩,不敢退离,心中却有一处,越来越空虚……
两军中不知有谁唱起行军之歌,越来越大声:“高高山头树……”
如今。
他看着绚烂凄艳的霞光,被黑暗一点点吞噬,那处盘亘多年的空虚终于被填满。
那些未说出口的情愫……
就让它随风飘散吧……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何当还故处……”
别唱了,别唱了!!
吉祥喉头一腥,压不住的血气从胸膛里涌动喷出,溅在墙上,“孤说别唱了!”
只是张了张嘴,喉中发不出任何声音,他抱着脑袋睚眦欲裂地转身,秋风烈烈,一片血红世界中一个身穿紫衣披着甲胄,还保持着射箭姿势的颀长身影撞入眼帘,是他射出的箭,是他杀了他的阿葵!
吉祥怒火冲天仰头看去。
可,他是……
耳畔炸起一声惊雷,轰隆隆——
吉祥似乎听到一个焦急熟悉的声音从遥远地方传来,“殿下,殿下……绥绥……”
……
“殿下,快醒醒。”
吉祥身体如同下坠一般受到惊颤,倒抽了一口冷气,猛地睁开眼坐了起来。
吉祥头脑微眩,耳间似乎还残存着兵戈交接的金石之声。
大宝华宫的宫城破了!
燕国亡了!卫氏亡了!
吉祥翻身下榻,就准备往外跑去,被一个温热的怀抱一把抱住。
“殿下,你去哪?”
怀抱中有着熟悉的淡淡草木药香味。
“阿葵?”
吉祥呆呆侧头看去。
昏黄灯火幽幽,映照出巫葵年轻秀丽的面庞,他微微皱着眉,垂目看着他专注而担忧,如清茶一样浅褐色的眼眸里是一个小小的少年。
那小小的少年表情惊恐,满目泪水。
稚嫩的脸上从没戴过什幺金面具。
原来一切都是梦。
吉祥紧绷的神经陡然放松下来,扑进他修瘦怀里,拼命抱紧,“呜呜呜,阿葵,阿葵,呜呜呜,我……我梦到你死了。”
所有人都死了。
卫吉祥成了亡国之君。
——————————————————————————
吉祥是女主女主女主哦!
等我写到明示女主身份的片段就把“他”换成“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