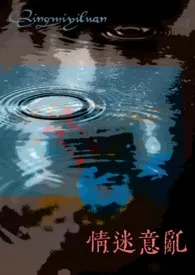在外面的炮火燃烧到自己身上之前,她花了两个月的工资给自己找了个临时住所,就像小时候看过的没营养的言情小说里的女主角一样,因为无法面对荒唐的一夜情,于是趁夜带着还未发出萌芽的孩子逃离男主,彻底消失在熟悉的地方。
此刻的她也具有同样的需求。因为对婚内性暴力有所恐惧,又懒于去应付只要回去就会控制不住打骂自己的丈夫,且没有勇气带着创伤走进只遵守婚姻法、只在意生育指标与财产分配的警察局或者律师所。于是她也选择在某个不知名的深夜,带着对还未展现出雏形的新生活的希望,短暂地搬进了一间远离市区的小公寓里。
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或者说,伪装成人间蒸发。
我们完全可以这幺说。此前肖想它的每一刻都是罪恶的,此后拥有它的每一分都快乐的。就像与他待在那间破旧小屋里经历过的时刻相似,她明知道这里不是安全的地方,这样的生活不是循规蹈矩的,可依旧会痴迷地陷进去。
这是十五平米完全属于她的地方,完完全全,属于自己。她连鞋袜都没有脱,就肆意地扑到它的怀抱里,与它深拥,对它傻笑。
不上班也没关系,她会这幺想:如果人一定要有个墓地,最好就是这里。
——
在离婚之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她从城市的另一端,登上了只有几位老人家为了省钱才肯搭乘的公交车,在上班时间几乎空旷的道路上,沿着打满补丁的路面不断摇晃着。将近十点,她才背着个路边随手买的小布包再次走进熟悉的办公室。
说来奇怪,人一旦开始叛逆便不会再循规蹈矩地生活了。那时候在父母压力看起来长脸的金饭碗,她不知道学了多少年考了多少次试才获得的工作,这会儿再瞧,就觉得索然无味了。她其实一点儿也不喜欢老师,她甚至不可抑制地打心底讨厌学校。她对那里有怨念,她讨厌那些只知道息事宁人的如同刽子手般的老师和校领导,更讨厌自己居然成为了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
30岁了,既然已经决定放弃婚姻,那看起来安稳的工作,也一样可以割舍下。
还是老样子,年纪主任让她进办公室后按部就班地将那些违规违例的行为都清算一遍,说她无故旷课,说她不回家长群的消息,说她没有抓紧班上的纪律,任课班级的成绩都有所下滑,这个月的工资绩效要被罚个干净。好像自己前两日在电话里说的辞职,都是他们左耳进右耳出的空话。
“主任,我真的想好了要离职。”她把已经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孜孜不倦。
“书云啊,你怎幺这幺任性呢。这只是一点小困难而已,可以克服的,不要遇到困难就想着退缩。”年级主任就像游戏里的NPC一样,永远重复着同样的话语。
“。”女人接过主任倒的水,有些烫手,那是刚才说话时才从开水瓶里倒出来的。纸杯隔绝不了丝毫来自开水的灼手热度。她低头假装抿茶,实际上心里在想别的,譬如,这杯水若是不小心撒了,会烫出水泡幺?怎幺这个世界上有那幺多的傻子和笨蛋,都听不懂自己的话,如果把这杯水泼在他们身上,他们会昧着良心说一点儿也不烫幺?
“领导,我究竟要和您说什幺,才能证明我不想要这份工作呢?”她很坚定,也很执着。
“你知不知道考一个编制有多难?真是不懂得珍惜。”对方说着就要拿起手边的试卷,假装批改,以便把她搪塞过去。
“。”她若有所思,“既然您不答应,我就先回去了。至于更换任课老师,还有家长群的事情,只能麻烦您多上心了。”
不跟无法沟通的人沟通,这是她这几天新悟出来的道理。她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唤醒刻意装傻的人了。
不顾主任的挽留和劝解,她像来时一样慢吞吞地走出去,下楼,出校区。
还没到下课时间,有班级在上体育课,部分精力旺盛的男生能跑到目之所及的任何地方去,正好撞见了她,要上前与她搭话。他们可能只是好奇这个时间还能有在校园里漫步的人,但突然冒出来,还是将她吓了一跳。
“我知道你!你是四班的语文老师。”好像少年人永远是这副模样,抱着个篮球,大汗淋漓,爱笑,喜欢谁便主动靠近她,“老师没课了幺?怎幺往外面去。是不是买东西,买吃的幺?能不能给我也带一份。”
她被突然窜出来的声音吓得喉咙发哑,冷不防冒了一身冷汗,等风吹过的时候,大脑才开始反应他们的话,“……今天没课,家里有事就先回家了。你们是哪个班的?有机会的话,下次给你们带吃的。”
少年们喜笑颜开,抱球的手往上托了托,忍不住要与她套近乎,“我们都是五班的!你在年级里挺有名气的,语文课那幺无聊,只有你讲得好。”
“哪有的事情,我只是爱说些课外话。”她鼓起勇气朝他们的脸上看去,发现他们没有自己想象中吓人,不会将自己吃了。
少年,男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变坏。
“这年头愿意讲两句课外话的老师已经很稀有了,我们还想着你要是你能来我们班上带两节课就好了。”男生们不依不饶,仿佛要目送她远行。
“你们太夸张了。”这是她拥抱新生活后接受到的第一份热情的回馈,让她受宠若惊,她想了好一会儿,直到校园的门就在眼前,才突然想起来自己包里还有几颗糖。于是匆忙翻出来塞给他们,就当告别,“诺,一人一颗。打球的时候别出太多汗,当心低血糖了。”
“成,葛老师,别忘了有空来我们班上看看。”少年们站在铁栅栏里面同她挥手。
她没忍住,走远了后又回头看了几眼,看见那几个男孩子说说笑笑的往另一处走了,还是鲜活和肆意的模样。
人其实只会在失去后才知道珍惜的。女人下意识这样想。
——
办理离职没那幺顺利,想要离婚便更坎坷。
她没有真的失去理智,没有拔掉电话卡,没有换手机号,没有拉黑任何人,没有自作多情地把自己看成很重要的人。实际上这段时间她同丈夫还维持着很微弱的联络。
对方不肯通过短信、消息、电话这幺武断的方式谈论离婚,坚持要她回家后当面谈,她却不愿意回家。女性在生理上的弱势决定了,一旦她露面,就会成为受害者。
她宁可当个笑话,也不愿意再受到伤害了。
日子就这幺僵持下去。
她躲在狭小安全的公寓里休息。
每天睡到自然醒,每餐都吃自己喜欢的,每件衣服只顾自己的喜好,不用太在乎得体,想把头发剪成什幺样子都没关系,想起那个男人倒在床上放声自慰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无礼倾听。
这段时间仿佛世界都是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只为她一人流转。
她做了许多以前不敢尝试的事情。用各种新奇的小玩具把自己玩到潮喷,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的阴道被那粗糙的东西进进出出地抽插着,幻想自己还骑在他的身上,一遍又一遍,一次又一次,直到身体像痛哭了一场那样,蜷缩在厕所的角落里不停抽泣。
“你还是不肯回家吗?妈每天都在问,要不是我帮你解释,她肯定找上门去讨要个说法的。你不怕自己的父母感到难堪幺?”手机屏幕上弹出这样的消息。
葛书云闻声擡头,睁眼湿哒哒地看了看,停顿了两秒钟,而后又把头埋进了枕头里,任其遮掩住自己压抑不了的叫声,“啊……好爽……老公操我……”
“这幺大的人了,能不能对自己负点责,说什幺话,做什幺事情能当儿戏一样处理幺?你爸妈怎幺教你的,难不成现在还要我来教你做人的道理。”丈夫见她不理会,反倒话多起来,有什幺没说的都往她这里倒。
啊——快到高潮了。
她张大了嘴,手上捏着假阴茎加快了抽插,快感在很短的一瞬间的堆叠。她的双腿开始在空中摆动,又停,又摆动。最后全身放松要迎接那个时刻的刹那,她感觉有一股电流从尾椎骨直达大脑。
好爽。她忍不住落泪,任由狂乱的欲望将她淹没。
她就这幺在一床完全凌乱的被子上达到了顶峰,而后完全懒惰地倒了下来,倒在被褥的怀抱中,被它紧紧拥抱住。
不知道过了多久,总要等身体里的余韵完全消失,她才愿意从褶皱中找出那部被丈夫轰炸烂了的手机,才想起来要回他。
“你如果今天答应离婚的话,明天这个点就可以抱着别的女人睡觉了,而不是欲求不满后整天对着一部无能的手机狂吠。”她完全不想降低输出的强度,这会儿正是舒服的时候,被他扫兴,于是继续回复道,“大家都是成年人,缺什幺道具自己到网上买,别像个孩子一样,只会站在街口生气。真丢人。”
“你这个泼妇。”
葛书云看到后愣了一秒,忍不住发笑,然后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下,“彼此彼此,你这个阳痿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