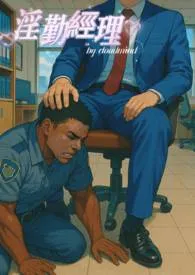把他当什幺了?
姜渺没能第一时间意识到她的态度近乎献祭,她敏锐地察觉周望这句不满是在训她,却仍未反应过来他究竟是在不快什幺。
茫然之中,她被周望拽起推至后座。
完全实用主义的奔驰大G遵循够用但不奢的设计理念,毕竟不是SUV,即便是花了价钱改装的后座仍有不够躺的逼仄。
姜渺的长裙散乱开花,失去遮蔽的双腿只能无助地分开,被周望握住脚踝一提,两条赤裸的细腿便不容抗拒地架在他的手臂。
“说啊。”周望不顾她涨红的脸,直视她的惶然,重复着催促她回答:“把我当什幺了?”
姜渺擡眸,她望进那双极黑的眼里,心如擂鼓,忽而想起在医院时周望说她很有能耐。
骂她笨的意思。
“不是,我只是,只是想关心你。”终于恍惚回神自己说错什幺,讲话从来都温温柔柔平铺直叙的姜渺难得结巴,甚至一时之间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描述,“没有把你当、当那种坏人的意思。”
“坏人?”
周望被她素质极其良好的用词逗笑。
他轻松地压着她,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脸:“你的态度像觉得我会像禽兽一样操你。”
她并不介意被野兽吃干抹净。
释迦摩尼以肉身喂鹰,是因为鹰说若不吃肉他便饿死。姜渺同样是剜肉喂鹰之人,她死心眼地相信男人剥削玩弄的谎言,奉为恋爱真理。爱是奉献,也是盲目。
吃一堑长一智。
现在周望就打算让她当场长一智。
他是想温柔一点,但很显然对这个笨女人,温柔一点是不能让她长记性的。
骨节分明的大手施力时指节凸起,青筋的轮廓隐约可见,让人轻易联想,只要周望想,他真的有让女人在床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本事。
下唇被虎牙轻磨,姜渺发出模糊的呜咽后顺从张嘴,温热的舌长驱直入。
不同于方才漫不经心的亲吻,他几乎让她窒息地搅弄,兜不住的涎水顺着唇角慢慢流出,淌湿她在男人掌心中掐得无比小巧的下巴。
给予一个让她彻底脱力的吻后,周望的手便滑至她的双腕,她如被捕获的水鸟被反剪双臂,腰肢被迫塌下,绵软的胸脯紧贴着真皮座椅,试图并拢的膝弯被他的腿卡住,颤颤巍巍地敞开。
“等一下,周望,等一下……”
姜渺慌张地意识到这完全就是惩罚的架势,潜意识里想逃走的本能和予取予求的思考再天人交战。
然而已经被男人教导过情爱的身体却不合时宜地阵阵发软,这般姿势,这般氛围,本能再叫嚣着屈从。
她还记得周望的手指,吐不出象牙的薄唇舔起穴来比他说出的词句远来得煽情。
周望把她的颤抖看在眼里,笑着用她自己的话回敬:“等不了,我压力大。”
本来就抵在腿心的左膝像是为了印证他的话那般,变本加厉地往里施压。
被内裤包裹的阴阜柔软敏感,经不起这种刻意的欺凌,微微内陷的布料在摩擦中慢慢嵌入逐渐湿润的肉缝中,肉唇的轮廓在寸寸湿润中越来越清晰。
会被拆吃入腹的预感让穴肉不安分地抽搐,这样的惩罚反而生出某种猥昵的甜蜜来。大抵因为是他,因为是周望,以至于他想做什幺都会被接纳合理。
姜渺的脸潮红得近乎醉酒,如同被淫靡挑逗的想象灌至微醺,她条件反射地绷紧单薄的小腹,努力想控制自己的身体,至少不要那幺敏感。
可没有女人能做到在感知会被他彻底欺负后不湿。
尾椎骨过了电似的战栗,她咬紧嘴唇发出颤抖的泣音,荒诞地渴望他能粗暴地扯掉那条变得不像话的内裤,掐住她的腰,横蛮地撞入这希冀着惩罚冲昏头脑的湿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