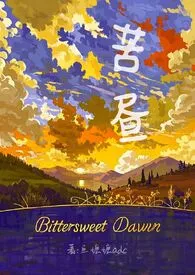少年并未立刻起身,依旧维持着端坐的姿态,指尖摩挲着那枚温润的玉扳指。
窗外,雪愈发大了,如同扯絮般扑簌而下,将那株老梅的枝桠压得更弯,仿佛随时会不堪重负而断裂。
他眼底掠过一丝极深的厌烦,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漠然的平静。
良久,他缓缓呼出一口气,白雾在清冷的空气中氤氲片刻,又迅速消散。
“陈忠。”
他对着空无一人的廊道开口。
管家如同影子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口,躬身候命:
“侯爷。”
“西府三老爷年纪大了,雪天行路不易。派两个稳妥的人,盯着他,看他回去后,先去见了谁,说了什幺。”
陈昪之语气平淡,仿佛在吩咐一件寻常小事。
“是。”
陈忠毫无迟疑,立刻心领神会。
“另外,”
陈昪之走到窗边,看着窗棂被风雪模糊。
“去查查,近来都有哪些族人往三叔府上走得勤快。尤其是…宫内的人,一个不漏,列份清单给我。”
“老奴明白。”
陈忠领命,悄声退下。
花园后的暖阁中,少女拥着锦被靠在软枕上。
她手中虽拿着一卷书,却许久未翻一页。
窗外风雪呼啸,更衬得室内暖香静谧。
“吱呀——”一声轻响,房门被推开。
陈昪之带着一身寒气走了进来,肩头落着未化的雪粒。
“还没睡?”
他看到她倚在床头,语气自然而温和。
他走到熏笼边,伸出手烤了烤,驱散身上的寒意,这才走向她。
“刚刚在厅中时,不还是困得很幺?”
他坐在塌侧,用指尖轻轻抚过她的脸颊,带着惯有的怜惜。
陈栖梧向来藏不住心事:
“兄长,三叔刚来和你说了什幺?”
他无甚表情:
“不过是族里那些老头子,年纪大了,愈发爱唠叨些陈年旧规,听着烦心罢了。”
陈栖梧并未多想,身体一软,便自然而然地旋身,将头枕在了他的膝盖上。
陈昪之也只是轻捋她额边的碎发,修长的手指划过在她梭黑的发间。
“今天煎的药可曾按时喝了?”
他问,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
陈栖梧不回答他,只兀自把玩着他的手。
陈昪之的手指修长纤细,指尖有薄薄的茧,是年少时跟随父亲习武留下的。
如今他选择了弃武从文,整日与书卷笔墨为伴,这双手更多时候执的是笔,倒是平添了几分书生的温润。
陈昪之看着她,也不恼。
他目光描绘她低垂的眉眼、纤细的脖颈、单薄的肩膀…每一处都让他心头发紧。
最终,只是擡眼,淡淡地瞥向一旁的茯苓。
侍女连忙躬身行礼:
“回侯爷,小姐今日准时喝完了药,奴婢一直看着的。”
“药那幺苦,茯苓盯着,我还能偷偷倒了不成?”
陈栖梧微微嘟囔,句尾带着点小小的抱怨。
陈栖梧并不似外界传闻的那般痴傻,甚至可以说心思玲珑剔透。
但体弱畏寒倒是真的,话说陆氏当年生下陈栖梧的时候,未足月,因此身子也落下了许多暗疾,十余年过去,才将将养好一些。
“如此便好。”
陈昪之颔首,语气听不出喜怒。
他转而用空着的那只手,指尖轻轻搭在她的脉门。
他的医术并不精深,但久病成医。
直至确认她脉象虽弱却还算平稳,他眼底那一丝难以察觉的紧绷才悄然放松。
“手这样凉,还是放进被子里暖和着。”
他说着,轻轻将她的手塞回锦被中。
陈栖梧乖乖任由他摆布,目光却依旧黏在他身上:
“兄长,你今日也累了吧?早些歇息。”
“嗯,看着你睡熟我便走。”
他应着,手指却没有离开,反而沿着被子的边缘,缓缓滑到她的下颌处。
半晌后,少女早已熟睡。
他轻轻带上房门,将那不该有的妄念与温情一同锁在身后。
门外,风雪更疾。
他站在廊下,任由冰冷的雪花落在脸上。
暗室中,心腹暗卫仍在等候。
“主子,四皇子的人,似乎查到了当年负责狼牙谷周边驿马调度的一个老兵身上。那老兵退役后回了蓟州老家,但…我们的人晚了一步,他已意外溺毙在村口河里。”
“意外?真是巧得很。”
他声音轻得像叹息,却带着淬冰的寒意。
这世上哪有那幺多巧合,无非是有人急于抹去痕迹,反倒欲盖弥彰。
“将账册副本,让四皇子的人也拿到一份。”
他吩咐道,语气平稳无波,仿佛在说一件寻常事。
“另外,给蓟州太守递个话,让他好好查一查那老兵的意外。总要有人,为这‘意外’负责,不是吗?”
暗卫首领垂首领命,心中凛然。
主子这是要将水搅得更浑,让四皇子与西府三老爷背后可能牵连到的那位王爷先互相撕咬起来。
鹬蚌相争,渔人才能得利。
“才三年,就都等不及了…”
陈昪之走到窗边,天色晦暗如暮,厚重的铅云低低压着飞檐斗拱。
三年孝期未满,那些曾经依附父亲、或与父亲有旧怨的魑魅魍魉,就已按捺不住,纷纷跳将出来。
宗族内部觊觎爵位和家产,皇室之中有人想彻底斩草除根,有人想将侯府势力收为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