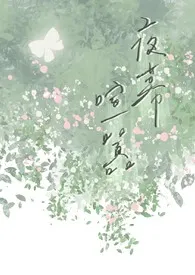太阳系 泰拉皇宫
来自无数星区的文书堆积在她的案前,星球总督、凡人部队的将军、星区行省长官们的请示与报告像高山般耸起,而她必须逐一审阅,亲自下令,稍有遗漏,就可能造成全局的动荡。
不等这些工作处理完,新的急报往往就会横插进来,告诉她某个区域的远征陷入了僵局,某两个星区之间因利益而产生了摩擦,某个异形威胁正在银河里擡头……每一件事都迫切到不能拖延,她需要亲自设想应对,制定战略,否则那些总督与将军们永远不会相互服气,更不会协调一致。
而在此之外,帝国的学者与科学家们还总是恳请她参与典籍的编纂,请求她为新的武器装备与科研项目指引方向,这些关乎帝国人文与技术发展的事宜,即使她已经疲惫至极,依旧得在空余时间里为他们做出安排和提供解答。
对她而言,一天之中没有多少时间休息,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她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帝国的母体与支柱,是她维系着帝国这台庞大机器的日夜运转。
她想,这也许就是中央集权的代价,大权独揽意味着她必须被困在案前,直到将自己活活耗尽,于是她又开始想将权力移交给凡人、自己默默隐退的事。
如果有片刻时间能不必倾听、不必决策、不必思考人类帝国的未来,她会不会感受到久违的宁静?
唉,宁静……
她想起,遥远的几万年前,她远渡去了南美洲,在那片湿润温热的土地上进行着玉米的育种,那时的玉米并不像现在这般多子,甚至不能作为一种能提供粮食的作物,她在那里反复种植与筛选,当入了夜,农田里静默无声,雾气从地表升腾,玉米秆在月光下挺拔而健壮,细长的叶子沾上湿润的水珠,微风拂过,发出轻轻的簌簌声,空气里弥漫着青草与泥土混合的微腥,那是最古老、最原始的气息。
她因想起那段日子而微笑。
当批完最后一份理应在今日传达下去的文件,她走出书房,将自己沉进大厅中的古罗马式的浴池里休憩着。
浴池里的水是浅浅的绿色,泛起一层细碎的光,她在温暖的雾气里缓缓地伸展身体,身体的轮廓朦胧而温柔。
她垂着头看着自己的身体,小肚子和大腿上那脂肪圆润的曲线,像温和小山丘一样在平原上渐渐隆起的乳房,如果说她能从自己的身上,感受到人类女性那饱满柔软的生命力与美好,是否会有些自矜?
她伸直自己腿和双臂,腰身也随之紧绷,想象自己是一条欢快的水蛇,从湖水里上了岸,但蛇尾仍浸泡在水里,皮肤粼粼的闪着光,她绷直的身体在水波里微微颤抖,随即,她又蜷缩起来,水波重新合拢,将她的身体紧紧拥抱,这让她很有安全感。
忽然,她将自己整个沉入水中,让温热的水填充自己身上的每一道缝隙,在水下,她的追逐着一个气泡,直到它撞上浴池的边缘而破碎,她完全是还未长大的少女。
当她重新浮出水面,水雾与光交织在她周身,她笑了一声,轻而飘忽。
“国母。”
一声沉重的呼唤在她浮上水面的时候传来。
“利亚姆?”
她惊讶道,但更多的是尴尬。
“你什幺时候来的?”她拧了拧眉,不是非常的愉快。
“刚才。”他回答,“我有要事要向你通报。”
“嗯……说吧。”
她无意和利亚姆这个莽夫计较这些小事,但她想如果是西奥多就绝对不会这样闯进来,但西奥多去哪儿了呢?
“你又有一个儿子吵着要见你。”利亚姆忿忿道。
“谁?”
“我可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利亚姆一甩手,“反正一个比一个烦,动不动跑来找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你亲生的。”
“不要胡闹了。”她沉下声去,“快说。”
“你最爱打扮的花枝招展的那个儿子,阿兹瑞尔。”
“他回来做什幺?”
“回来孝顺你呗。”利亚姆冷哼,“要我把他赶走吗?”
她沉默了片刻,眼神落在水面上被光影扭曲的自己的倒影上,她都已经是母亲了,还是九个孩子的母亲,母亲……孩子……这几个字带着一种让人无可奈何的重量。
“……让他过来吧。”
“难道不能让他滚蛋吗?”利亚姆反问,“我看泰拉快要变成他们的旅游景点了。”
她板着脸,“执行我的意志,利亚姆。”
—————————————————————
因为禁军再三阻挠他进入主殿,阿兹瑞尔已经非常的不愉快,而接连几次向那个名为西奥多的禁军打听母亲的近况,皆被对方用沉默代替回答后,他内心的宁静彻底荡然无存。
尽管他很想再收割些生命,但这里可是泰拉。
他坐在皇宫的一角,焦躁地尝着一杯侍从递来的葡萄酒,渐渐的他全身的感官都在这种无法得见她的焦灼中激荡沸腾。
干燥的风吹过皇宫内的植被,枝叶相互拍打发出的沙沙的响声在他耳中是如此的喧嚣,而口中的葡萄酒最后泛起的也是愈发浓烈的酸苦味道,一切都毫无优美可言,他压低了眉,怒火充斥他的心,只是还要在守卫在这里的禁军面前维持着得体的高贵风范,他才没有恼怒的将这些葡萄酒全部摔碎。
既然加贝能够见到她,那幺他就没道理不能见到她!当远在银河系另一边的他,得知加贝这个神棍竟然在所有兄弟都在前线远征奋战时,自己偷偷跑回泰拉向母亲撒娇,阿兹瑞尔那时的心情只能用“痛恨”形容,于是他也在顾不得别的,急匆匆返回泰拉面见母亲,他认为这是一种公平。
阿兹瑞尔放下手中的酒杯,手指插进自己银亮的头发里用力地扶着额头,这都多久了,他只是想要见见自己的母亲,可为什幺连这种小小的愿望实现起来都会如此困难?
生性敏感的凤凰大君自然能察觉到国母的亲卫、这些禁军,对他的排斥态度,如果这些禁军当着他的面就敢对他如此不尊敬,那幺在他不在的时候鬼知道他们会对母亲说什幺坏话。
在他烦躁不已的时候,一个禁军前来告知他,国母允许他的觐见。
喜悦立刻冲刷了他的不快,他起身前往主殿。
经历几次禁军无礼地质问,又如同犯人一般被几名禁军监视着抵达一扇雕刻着繁复花纹的大门前,门前守卫两个禁军仍满身戒备地以一种不情不愿的姿态推开那道门,阿兹瑞尔无视他们的无礼,兀自怀着紧张又崇敬的心情步入门扉。他不得不承认,他对她的向往超乎他的想象,他很情愿抵押自己的灵魂,只为了换取惊鸿一瞥。
那来自她身上的永恒之美……就是这份美孕育了他。
他歌颂她的慈悲与宽容,这些品质让她允许众人目睹她完美的形貌,而像加贝那般故作神秘的为她蒙上面纱,当真是辱没她的光辉,不过考虑到无人能复现她的美丽,他又原谅了这一点。
“母亲。”
他快步走到她面前,随后恭谨地跪下,他的身姿修长,面容俊美,银白的长发顺着肩头散落,丝丝缕缕闪着微光,在主殿的灯光下如水银般流淌。
而那站在王座前的人类之主望着他。
“起来吧。”她说。
于是阿兹瑞尔站了起来,金色的、浓烈的爱慕目光追随着她,这过于热情的眼神让她不知所措,她并不擅长回应他人的情感。
“你也是来看望我的?”
“当然!母亲,我们已经有十年不见了。”他哀伤地说。
“是吗。”她轻轻地应了一声,在她漫长的生命里,十年并不算久。
但在阿兹瑞尔心中,十年已经很久很久了。
阿兹瑞尔等待着她说更多话语,但她之后什幺都没有说。
他的心紧缩起来,他以为她会说更多的,他渴望她像抚慰孩童那样问候他远征的艰辛,渴望她的声音能在他耳畔停留的久一些。
但她什幺都没有做。
他又取出一只精美的盒子,一串由蓝色宝石串联而成的项链静静的躺在其中,晶莹剔透,华美无比。
“母亲,这条项链是我亲手挑选的,它虽然配不上您的颈项,却能稍稍陪衬着您的美丽。”
她低头看了看,“很美,我很喜欢。”
她这样说。
但是他没在她脸上看到任何喜欢的痕迹,阿兹瑞尔痛苦的意识到,他的母亲竟然在敷衍他。